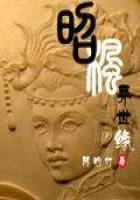宣旨官走了进来,阮启宸退到一旁跪下。
“皇上念二皇子身体不便,不必大礼听旨。”宣旨官道。
风元潞轻声说了声谢父皇体恤,宣旨官打开了圣旨,“皇上有诏,二皇子救驾及时,且孤身追凶,受了重伤。皇上感其为子之孝心,为臣之忠心,实为国之表率,特准恢复太子身份,赐金蝉两只。因皇上身体抱恙,准太子伤好后参与辅政。”
风元潞躺在床上一脸虚弱,完全不是刚才那紫电青霜的样子,“谢皇上!”
一旁的紫冲摸出几两银子塞在宣旨官手里。风元潞咳嗽了一声问道:“父皇身体怎样了?”
宣旨官看了看屋里几人,小心道:“……还需将养,圣上……龙体欠安,心情总是不太好。”
“转告父皇,待儿臣能站起来了就进宫侍疾。”
宣旨官离开,阮启宸站起来,看到倚着床榻,把玩那两只金蝉的风元潞,突然笑了,“殿下这相机而动的本事,草民实在佩服。一手苦肉计使得好,真真儿是一箭双雕。”
话音未落,只听哐的一声,含心刀带着鞘钉在阮启宸面前的木案上,在阮启宸的腰腹前摇晃着。阮启宸惊跳了一下,却还是失魂般轻轻地说:“殿下——你对她有真心吗?她为你献出一身精华,不但没得到你一丝庇护,却被伤魂还坠落山涯。”
风元潞眸中寒露一沉,问道:“为我?……你知道她是如何失去舞魂的?”
阮启宸愣住,“她没有告诉你吗?不是为你做簋凉杀吗?!”
!……
卧房内,一个倚在床上,一个站在床前,都静静地不说话,似乎都在自己的问题里失去了方向,阮启宸首先打破沉默,“不是殿下中了簋凉,那是谁?她能为谁?”
“你知道做那个东西的后果,还让她做?你不是医者吗?”风元潞的声音有些轻蔑,也有些恼怒。
“我那时已经不想害她了,但大皇子催了,而且……她已经下定决心了,说做完簋凉杀就回家过寻常日子。”
风元潞手中的金蝉越转越快,好像他此时的思绪。风元潞觉的自己很矛盾。爱上她是因为她的温暖与全心全意,那是自己的人生中从未见过的光华。可是现在自己却因为她这一点而愤恨不安,她如何能一再为旁人全心全意,他不准!
“她说那人要大婚了,还帮过她良多?”风元潞脸中已经出现了一张妖魅的脸,手中金蝉不再旋转,已经快被捏成两块金疙瘩。风元潞起身,在屋中踱步,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将来再不准她如此,不管用什么办法,她只能对自己全心全意,不计得失!现在得行动了!
哐当一声,两只金疙瘩被扔在桌上,风元潞看向阮启宸,一字字道:“阮公子,你做本殿下的府医,助本殿下抵抗生煞反噬。”
阮启宸浑身一震,面色大惊,这句话可比刚才所知道的惊人太多:只有驭煞之人才会担心生煞反噬!
风元潞盯着面色苍白的阮启宸,“本殿下既然这么要求,自然是知道你可以。”
“……,殿下已经恢复太子身份,又有谋略武功,为何要做这种……?”
风元潞转身走到含心刀前,伸出食指弹了弹剑身,“实力不济或不相上下才谈谋略武功,但也未必斗得过实力,……本殿下要那个最有把握的。”
阮启宸摇头道:“可是生煞,……那是自杀!”
风元潞却无情拆穿了他的伪装,“你知道有人试过,很有威力。”
阮启宸沉默半晌,“殿下既然对草民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于此一道我仅有一次病案,所掌握的医魂术只有血窑那一星半点,完全不及倪祈和禾焰,也不及师傅。”
“所以……这是阮公子名扬杏林的机会!想来阮公子若是安心体医之术,不会在禾焰做了大全引之后就出山了。”阮启宸眼睛里冒出一点火花,却又熄灭了。
风元潞看着恢复平静的阮启宸,马上想到他是为何做了皇兄在煊学的钉子,于是再次相机而动。“原来皇兄向我要参花是为了你师傅,那一株参花够用么?”
阮启宸的头猛地抬了起来,终于张开了嘴,“若殿下执意如此,在下虽无把握,但可以尽力一试。”
……
风启三十五年四月十五,风都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二皇子终于送走流年霉运,迎来好运了。因护驾有功,二皇子恢复了太子身份。又因为皇帝身子不便,二皇子一恢复太子身份,就开始了参政议事。除此之外,皇帝还再次赐婚,一赐就是两妃,都是朝廷重臣的嫡女,就连煊学医门小全引阮启宸都成了太子府的府医。至少从明面上看,太子的势力终于开始有了直逼三皇子的架势。
冷清了两年的太子府修缮一新,热闹起来。不过少有人知道,新修缮的太子府后院桑林中新添了一间紫玉暗室,还是护钱庄的老庄主冷烈亲自督工的。这紫玉暗室半掩入地,白日屋顶紧闭,完全隔绝阳光。夜间屋顶旋开,人隔着紫玉可暴露在月色星光下。风元潞恢复太子之位没多长时间,几乎夜夜都在紫玉暗室中渡过,陪他一起的就是新入的府医阮启宸。两三个月后,后院桑林却无人敢去,因为即便是日间,也能让路过的人有阴森之感,无端地脑后生风,感觉再也不会快乐。
这会儿已经是朝阳东升,整个风都都被朝阳镀了一层金光,但紫玉暗室内依旧黑暗压抑。暗室内有一方紫玉桌,上而摆着那柄离了鞘的含心刀。风元潞正盘膝于桌前,双手笼于丹田,星目紧闭,那蹙起的眉端昭示着他挣扎在恶梦般的感觉中,他额头上的汗已经滴落,如墨的头发已被儒湿。他指间莹绕的一缕忽明忽暗的灰气。即便只是一缕,一旁的阮启宸仍能感觉到一股活着的死气,这感觉很怪异。
风元潞突然睁开了星目,那缕灰气嗖的一下消失在含心刀内,风元潞慢慢站了起来。阮启宸急急上前,在风元潞腕间一按,马上抬手在乳突、心经、肺经处刺入几针。风元潞摇晃了一下,站稳后深吸一口气,望着含心刀道:“照这个速度,本殿下什么时候能引煞入身?”
阮启宸死按住手下突突猛跳的心门大穴,另一只手将伤敕膏敷了上去,又在下方快速刺了一针,忙活完了,才回道:“殿下的身体已经非比寻常人了,少则也得近一年,多则……,”
“那就一年后初成!”风元潞的声音不大,却霍霍如铁。
两人一前一后由暗道回书房。阮启宸上前扭动书架上的琅琊彩凤,书架转动,暗道消失后,行礼离开。早饭后,风元溢走了进来,在他面前坐下,“刺客的事儿已经抹平了,父皇没有怀疑,老三那边儿也没落下什么把柄,很干净。不过——,你若扣下她,无论是兵器图还是抓刺客,更是大功。”
风元潞抬起头,“再说一次……,”
风元溢截过话头,“不动她,我知道。但父皇不会放过她,我今儿在刺客这事儿上装了糊涂,但秘务司的差不能不当,她身上有兵器图。”
“这种事儿皇兄从来都在行。至于兵器图,要或不要根本没那么重要!”风元潞冷声道。
风元溢狭长的眉眼挑开,“不重要!就因为你……是生煞之主么?”见风元潞星眸一动,风元溢一挥手,“冷烈与暗香楼的红玉打的火热,在美酒和女人身上,他不是个管得住自己的,我让红玉将他看住了,不会再有旁人知道。”
风元潞下意识的撇了一眼含心刀,默认了。
风元溢凝神看了他一会儿,终于确定这不是冷烈吹牛,神色一变,“原来含心刀真是煞术,但你……可以拒绝的,为什么接!?”
风元潞星目微动,却依旧不言不语。
风元溢有些急了,“我查了麦离,前任含心之主,她失踪了,若她真如冷烈所言,为何会消失!”
风元潞在长久的沉默之后,终于开口了,“皇兄,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时运来了?”
“我在说驭煞之事!”
“我说的就是驭煞之事。你觉的我应势受了一剑才行了大运?是也不是,我的时运其实是与驭煞紧密相关的。从我接受含心之邀,成为生煞之主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这感觉难以描述,玄妙之极,简单说,就是未来有一番不可估量的伟业在等我,十分确定!在倪玥刺杀父皇那晚,我十分清醒我要做什么,受那一剑我丝毫没犹豫,那不是赌,我十分确定我不会死。不光如此,我还会否极泰来。尽管不知道如何来,但我就是相信会来。自从修习趋月术,这感觉更强了,我的运气、实力在与煞力在一同增长!这种滋味——若是能形容,那就是——赢的滋味!至于父皇的态度,……,你了解,以他的为人,全天下为他死都理所当然,如何会为我追杀刺客受伤而感动?他之所以恢复我太子之位,是因为他知道我已经是生煞之主!顺手推舟的事儿自然要做,何况我如何,他根本知道拦不住了!因他同冷烈一样,对驭煞之事是痴迷且畏惧。”风元潞娓娓道来,字字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