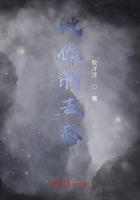外面的天很明媚,小阳春里的温暖直直射进七门里这座议事厅里,射在地面石砖上,斑驳成好看的点点,晕得人心暖暖,有一种困腻的感觉。可这困腻因豪华而生,这满院的豪奢皆因她老师而得。
面前七门各家主的正襟危坐,各有一家之主的威严及自省。包括年龄最小的第一笙,其身弥漫的气度也远非一般商流可比。
可章儿呢?当年清廉之名盛天下的章鲁,一身才情引人趋鹜的溹岭才俊,他的女儿,瞒世六年,隐面自居,不敢对人说父辈从前,不敢言家族荣耀。
世间,何所谓公平?何处有公平?
顾谙深深吸了口气,慢慢平复心中对七门里先入为主的愤恨及怀疑,继续问道:“倘真有难,该求助同门才对。”
第一笙直视向顾谙,做实了心中的怀疑。顾谙今日登门当真是别有用心。
当年,当年事旁人不知,顾相会不知?朝廷会不知?顾谙会不清楚?
当年她独自一人押着万石粮食出了北芷,夜宿砚城东北的风鸦涧。风鸦涧,传闻此涧无水无树,只有风和乌鸦,此涧高十几丈,一条羊肠窄道可行,下山后再行十里便可入砚城。可比从爻山进城节省一天的时间。砚城北城外爻山有匪,往来要交过路费,第一笙既不愿交钱又心存侥幸才冒险走了风鸦涧。毕竟临行前她请了天师占卜,天师说风和可行,其时家中老父重病卧床,第一笙心中挂念,才兵行险招。
天刚蒙蒙亮,她便催着运粮车上路,费力攀上涧顶,她才见识羊肠窄道之窄,粮车根本过不去,除非有力大者使粮车空两轮而驶方可行。第一笙当时就知道自己决策错误,既恨随行不规劝,又恼自己贪功。前进不可,后退再行明显误了交粮日期,赔偿金会让第一门损名又伤财。就在此际,狂风起,涧顶无遮拦之物,众人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只得舍了运粮车抱团抗风,紧跟着天降大雨,瓢泼而下的大雨浇在粮袋上,瞬间浇透众人的心。第一笙无奈之下,只得命人顺原路下山求救。报信人未回,却来了南杞国人。彼时,南杞国王妃拜流声刹的七空大师,得大师点拨,沿天女河顺流而下至砚城,清早徒步登涧求生机,得遇第一笙。在得知第一笙是与自己母族做生意后,南杞王后手令缓了她交付粮食的时间,又令族内以原价收了她的粮食。这一场机缘使第一笙拜了南杞王后。王后许是得了大师口中的“生机”,所以对第一笙爱护有加。相较南杞王后的关照,京北七门对她此次的险行,非但无半点安慰,反而皆是指责——指责她判断失误,失了京北七门声誉,被同行笑话;与南国瓜葛不清,被别有用心者诟病,与家门不利------
她蹒跚而回,面对满堂指责,她不明白。她冒险所做的这趟生意里,第一门只得七分之一利,她为了这七分之一利,险失了命。坐守家门得利的叔叔们怎么就不能给她一声安慰?连一句“好不好”的话都吝惜给她?商人重利,重利的商人啊!
第一笙抬头看向顾谙,道:“当时我已出城,天降大雨,回七门里求助明显不可能。”
“原来这么回事,我还道是七门里重利轻情,不愿意出手相助。”顾谙道,“第一家主若不兵行险招,也不会与南杞王后相识,也得不来与严氏长久合作的机会。七门里在第一家主手中可是壮大了很多。可见这世上的事、这世上的缘果真奇妙。”
第一笙接道:“我是市井之人,只懂行商重利。奇妙玄幻之事,从来都当作传说看待。大小姐学识渊博,您说奇妙应真是奇妙吧!”
顾谙嘴角上的笑依旧挂着,只是挂得久了,自己心里都生了嫌。察言观色的第三家主起身征询午膳的安排。
顾谙暖了脸色,道:“听闻第三家主对此次相师堂的堂会很费了一番心思,我总要用心赏玩赏玩,这聚宴就免了吧。”
第一笙闻见顾谙笑里的疏离,思量着她的别有用心。
“第一家主。”顾谙突又道:“我门内有位梁上君,前几日与人玩笑,冒犯了家主------”
第一笙嘴角微不可查地一动,明白顾谙欲言又止的手段为何了。
“既是玩笑,又何必在意?”第七家主道,“小辈家家的游戏,七门里岂是小器之人?”
顾谙未置一言,仍旧望着第一笙。第一笙将问题抛了回去,道:“顾少堂主以为此事该怎么处理?”
顾谙心里一笑,第一笙称她少堂主,心里是生了气。
“让小少爷受惊,这罪过不轻。只是我有急事须外出一段,这样吧,待归返,在下设宴,当面道歉,杀罚随意,可否?”
第七家主喝斥道:“一笙!荃儿不是没事吗?你要懂得适可而止。”
第一笙咬着牙,面上冷冷的,却没有言语。
“如此,便说定了。”顾谙起身,对众位一拱手,“今日不多留,找一天风和日丽的,请各位聚,答谢七门里对相师堂及天女峰的襄助------”顾谙说到最后,手势在第三门主及第七门主处均停顿了一下。及至出门时,顾谙依旧对二位门主格外关注。
七门里外,阳光不炙不烈。
高墙大院的争权夺势,张扬的那么明显。她有些不明白,这么一群散沙商人,当年竟能害她老师满族遭劫?
“小姐?”章儿注意到顾谙一脸的凝思问道。
“这是一群重利且自私的家伙,如今更连表面的齐心都不愿假装。当年到底发生了何事,使溹岭章家那样的名门望族一夜如大厦倾?”
“小姐------”
“怎么了?”
“是他!”
顾谙转头,看见南宫轶在熙攘的人群里走出。一身淡蓝丝绸的长衫,绣着零零落落的梅,缀着些许的墨色,衬出一丝淡淡的雅致,又透着一缕微微的香。束腰带自然下垂,其上坠着的玉佩和着春日的暖阳,格外温润。男子在人群中站定,双眸含笑,亲切地看着她。顾谙感觉自己身处在一片水泽之中,清澈之凉穿过她的长发,从她的手上滑过,带着丝丝牵挂越过高山大河,扶摇直上入九霄。顾谙不自觉地笑了,笑自己这种奇怪的感觉。
南宫轶没想到自己随心而行的路上会遇到她,会遂心所愿的遇到她。她浅笑的眉眼怔了他的心。那略带青涩的面上染上少许的阳光,透着红色,熏得他的心也跟着漾了漾。烟罗软纱的长裙,旖旎丰姿。一颦一笑里的自然,让本已停了脚步的南宫轶不自觉地又迈步近前。“男人啊!男人啊!”南宫轶的内心一直在自嘲着,自嘲自己亦如其他男子一般,在面对绝色美人时不能免俗的心动、心痒。
有轻风吹来,吹乱了南宫轶的心。
他知道,自己想见她。方才在歇马河畔闻到荼蘼花香时,他便似生了魔障,一路追随气味而来。他从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闻香寻人的奇能。
南宫轶走到顾谙面前站定,不言语,任嘴角跑出的笑渲染他兴奋的心情。他不知这种感觉是什么,是情之所起的意动?还是棋逢敌手的渴盼?他不知,他只知自己可以再进一步,能够再进一步,敢再进一步。有多少年了,自从母亲死后------是了,有十五年了,他有十五年没有离女孩子这样近了。她的笑,让他生了勇气、生了欲望,他想离她更近些。
顾谙不知面前的南宫轶内心澎湃且复杂的情绪,她脑子里想的是照夜公子带回的消息,面前这位南国的太子有疾,从未召侍。这有疾,是身?还是心?从未召侍,是因为惧、不屑?还是因为其好男风?貌似听闻这位太子爷品性端正,从未有过这类传闻。自己该如何下手去试探?正想间,南宫轶开口说话了。
他说:“你劫了我的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