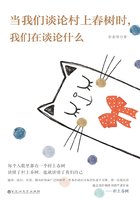八年前的饥荒,这是禁忌,这是皇帝心中的痛。在这朝堂之上,谁敢提及?这李山雨倒好,上朝第一天就敢皇帝的伤疤给捅了。
“不知李非良为何忽然提起这事?是在指责我们不作为吗?”任千秋一蹙眉,当年的事他们的确做得不好,但也轮不到李山雨这个毛还没有长齐的小屁孩。他身旁的王谦眼睛忽然动了一下,若有所思。
“对呀!我是在指责你们呀!”李山雨淡淡一笑,众大臣变了脸色,充满了愤怒。
“指责?你有什么资格?”任千秋冷笑。
“凭我是在八年前活下来的受害者。”
此话一出,朝堂之中忽然寂静起来,所有的大臣都猛的把眼睛盯在她的身上。
眼前这位娘子看着也就十四五岁左右,八年前不过是一个六七岁的幼童,她怎么可能活得下来?
“看你们的表情似乎不相信,不过我也不在乎,反正你们也不会在乎,反正死的不是你们的亲人你们的朋友。像今日的水灾已经发生了五天,死伤几万人,而现在让你们出些钱也不愿意。我一直在想,大咏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八年前也没有做何大工程,也无战争……那救济灾民的钱去哪了?”李山雨的声音很平淡,但是她说得每一句话都如一击击重锤砸向每一个大臣的心中。他们大部分没有内疚,也没有懊悔,只有害怕。他们低着头,偷瞄着皇帝的表情,皇帝摸着自己的胡子,看着李山雨,心中多了几分悸动。
“八年前赈灾的钱被贪污了,而贪污之人已经被凌迟处死,而他的家眷也一同处死。十三位主犯,牵扯两万五千三百四十一人。”皇帝开口了,这个案子他直到现在都还记得,主犯的名字也行模糊了,但人数记得很清楚。这件事在朝堂中都成禁忌,百姓更是不可多说,李山雨自然不知道。
“陛下倒是很干脆,不知道这次陛下能否像八年前那么干脆。”李山雨并没有像其它的大臣一样称赞皇帝圣明,只是冷淡回答。
“李非良这是何意?”王谦一直眯着的眼睛忽然睁开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们不知道吗?昨日这长安城关于泽安城水灾的事情已经传开了……”李山雨眼睛一转,有些疑惑。“百姓都说,今年泽安城的雨水比去年还少一些,正想着今年应该不会再淹了,却没有想到江堤崩塌了……现在长安的不少人都在启程回泽安城,去寻亲友……我当时听着也觉得奇怪,便问了几句。那些百姓说,泽安城年年都淹,不过是淹地都事,人倒是没有多少事,今天忽然有了大水,怕是有人在搞鬼,在修筑江堤上动了手脚。”李山雨道,她很明确地表达几件事。第一,这话不是她说,是她听百姓说的。第二,昨天坊间便已经传遍了泽安城水灾的事。第三,这泽安城发大水有可能有人动了手脚。
“李非良,你说这话可是需要负责任的。”吏部尚书杜峰道,他的眉头在拼命的跳。
“责任……我不过是把坊间百姓的说法告诉你们,你们要我承担什么责任?这位……呃……杜尚书,你要知道一件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山雨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杜峰正打算反驳,却发现任千秋在瞪着他,让他闭嘴。
“李非良,那你说要怎么办?”皇帝问道。
“既然陛下问了,那我就说说我的拙见。”李山雨丝毫不客气,清清嗓子。“第一,赈灾的钱是不能少的,只能备多不能备少。第二,灾民的日常生活需要的粮食、衣物这些也不能少。第三,最重要的,医师和药。”李山雨说出自己的看法,接不接受那就是皇帝和这些大臣的意思了。
“那这需要多少钱?”杜峰摸了一把冷汗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得吏部的人去核算。对了,还要提防黑莲教搞事情。在大灾大难之时,便是黑莲教死灰复燃之时。我不敢保证,而这是极大可能的。”
皇帝的脸色变了,王谦和任千秋互相看了一眼。
“陛下,李非良言之有理。”王谦和任千秋同时道。
“父皇,李非良说得有理。先不论这场水灾的前因后果,但黑莲教极有可能鼓动受灾百姓制造混乱,趁机树立威信,就像它们过去做的一样。”赵子洲起身一揖。
“臣也如此认为,此时兹关重大,必须谨慎处理。此时国库并不空虚,甚是满库,多花些钱财也无妨。”赵奕棠也站了出来,赵思澈和赵居夏相互看了一眼,异口同声说道:
“臣亦如此。”
“臣等亦如此。”
两位丞相,四位王爷都赞同这件事,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杜峰的汗越流越多,颤颤巍巍附议。这些人是要他的命吗?国库甚满,但有一大部分都不能用,死十座城的人也不能用呀,那是军库的用度,是国之根本,绝对不能动的。
“李非良!”皇帝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丝笑容。
“臣在!”李山雨一拱手弯身,等待皇帝接着说。
“我任命你为京巡,替我去调查泽安城水灾,要什么便开口。”皇帝道,眼睛在大臣中扫了一遍,最后定在了赵奕棠和赵子洲的身上,摸了一把胡子,点了点头。“晏王!”皇帝道,晏王随之出列跪在地上。
“臣在!”
“我命你一同前往泽安州,与李非良一同调查此事,无论关乎谁,哪个家族,都严惩不贷!”皇帝的声音很洪亮,正直,具有不容侵犯的权威。
“是!”晏王答应着,这个人才是他的父亲,具有无尽的威严,谁也不能挑战他底线,而他的底线便是百姓、黑莲教。
很快便退朝了,李山雨在殿外站着,周围经过的官员都在打量她,却不敢上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