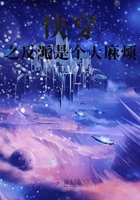正在杨继普父子三人商议对策之际,却闻听院落之中吵吵嚷嚷声渐近,紧接着便有家仆前来禀报,道是左金吾卫上将军魏新寅带领着禁军闯进了府中,管家想要问句原因,竟被以刀逼迫拿住了,说话便到这里了。
杨继普道:“这要如何是好,快派人私下去问一问严馥瑞,再晚就谁都出不去了!”
却听杨宗茂道:“父亲如何还要相信那严馥瑞,您不觉的如今的情势甚是奇怪吗?自打那宋书怀进京以来,严馥瑞便是春风得意起来,我们便开始诸事不顺,只怕其中缘故深着呢!”
杨继普正要说话,却见魏新寅已经带着人气势汹汹地进来了,训练有素的兵士们一个个持着长矛尖刀依次排开,站在两侧,魏新寅见到丞相倒是比想象中的要客气许多,先是行了参拜之礼,然后道:“今日魏新寅奉旨闯入府中,还望丞相大人恕罪。如今有一个案子牵涉到两位公子,下官奉旨前来有情两位公子前去配合查证一番,失礼之处,改日再来谢罪。两位公子,请吧。”言罢便向两位杨公子做出请的手势。
杨继普一见魏新寅如此客套,顿时心中明白,这是皇上和余琩澈他们亦不敢轻举妄动的意思,方才瞬间悬起的心便又落下了许多,然而今日魏新寅既是如此兴师动众地大驾来此,想必也不会善罢甘休,便对杨宗茂、杨宗繁二人道:“你们且随魏将军去一趟吧,清者自清,无论是何案子,去将事情讲明白也好。”
杨宗茂和杨宗繁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早已吓懵了,此刻闻听父亲之言,便道:“孩儿遵从父亲教导,定向主审大人开诚布公地解释清楚。”兄弟二人又向父亲道了别,便随着魏新寅走出了厅堂。
魏新寅带着杨宗茂与杨宗繁二人刚出去不久,门房便来通报,道严馥瑞来了。杨继普此刻虽是心中又多了几重疑虑,却又不得不打定主意笑颜相对。
严馥瑞进来之后依旧行了礼,后道:“丞相大人,下官闻听皇上已经听信了余琩澈和宋书怀之言,将这案子交与他二人审理了,方才来的路上,也已遇见了魏新寅带着两位公子出去了,不知丞相大人将作何打算?”
杨继普摇一摇头叹道:“老夫如今又能如何,此事既是事关两个犬子,又不适宜申辩,不过是静观其变罢了。”
严馥瑞道:“话虽如此,却还是要想一想对策才好,这余琩澈和宋书怀二人可是打定了主意要与我们争斗到底的,如今二位公子落入他们手中,只怕无事也能审出个窦娥来,更何况这其中的许多情由又是说不清的。”
杨继普道:“话虽如此,只是如今又能如何,总不能……”
却见严馥瑞看着杨继普深深地笑了一笑,然后道:“只怕是丞相大人与下官又想到一处去了,为今之计,也只好如此暂缓情势了。”
杨继普道:“此事怕是不妥,如若被发现,岂不是罪加一等?”
却听严馥瑞道:“所以,我们便需找一个肯肝脑涂地的死士来做这事了,待他一旦认罪便寻机自行了断,如此又有了签字画押的供词,又省了继续审理之功,岂不两下里便宜?”
杨继普道:“如此说来,此计倒是可行。且杨某为宰十载,找两个死士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如今杨继普既是对严馥瑞存了几分的疑心,这死士势必是要由自己来选定的,毕竟自己的人更为放心些,而且即便是他日严馥瑞将此事咬出,也无旁人佐证,大可反咬他一口。
严馥瑞见杨继普采用了自己的建议,心中还是有几分高兴的,希望这次事情的圆满解决能够让他们尽释前嫌。
严馥瑞走后,杨继普便仔细斟酌了许久,方才选定了一名最为忠诚的死士,名唤秦绍斐的,官居正七品的殿中侍御史,教他认罪的缘由是由于与宁穰不和,一直受到排挤打压,便想出了此种恶毒的法子,却不想宝石经杨宗茂的手被送进了宫,竟害死了四皇子,眼下深感罪孽深重,唯求以死谢罪。
宋府上,钟亦昭端起茶杯浅浅地饮了一口,润了一下喉咙,然后道:“我们姑娘又让奴才传两句话过来。”
宋书怀道:“你们姑娘倒真是料事如神,这一步步竟都于她的算计之中发展,她今日有何话,快快说来。”
亦昭道:“我们姑娘道,那杨继普与严大人此番必定狗急跳墙,思来想去便会棋行险招。以他人出来认罪然后再畏罪自裁便是最好的办法了,所以,两位大人提防这一招便可。”
“你们姑娘的意思是要我们万万不可让那人自裁便好吗?”因念奴屡屡出其不意,宋书怀如今听念奴传来的话倒是不敢着急做出论断了。
“并非请大人阻止那死士自裁,而是成全他,如此方能让杨继普与严馥瑞再度缔结信任,也才能更深地将那已经腐烂的根基挖出来。两位大人只需咬定此事并不会如那死士所言的那般简单,但凭一人之口不足定案,还要再将两位公子暂行收押以待案情明了便可,那样,定会有人耐不住,而狗急跳墙的。只是如此一来,两位大人便会在朝堂之上遭受杨丞相党羽的口诛笔伐,处境便不会如现在这般轻松了。”钟亦昭一五一十地将念奴的话复述一遍。
宋书怀却笑笑道:“这倒无妨,余大人和宋某都是惯见这些斯文刀光的,不足为惧,倒是难为你们姑娘,如此费尽心机地筹谋经营,直令我等七尺须眉自愧不如。我心中倒是经常想着,如若她身为一介男儿,定当不负凌云之志。且不论她,便是曲大人,也是常常叫我心生敬意的。”
亦昭笑笑道:“是呢,不禁她们心智卓尔不群,最令人敬佩的便是她们的待人之心,奴才当初帮她们不过是那时曲先生待我有恩,见她们有难处,便想着知恩图报,却不想着两位姑娘竟如此厚待与我石家和祝家,帮我大哥置了十几亩地和房子不说,还帮祝家又置买了两处铺子,所以奴才更要誓死跟随两位姑娘。”
不料宋书怀却道:“亦昭跟着念奴姑娘行事也越来越机敏了,不若等你们姑娘的事情了解之后,你便跟着我如何?”
只听钟亦昭道:“似我们姑娘这般无依无傍的,即便日后隐退,日常生活怕也是需要人照顾打理的,少不得我也同翠鸣、芙影一道照顾她一世罢了。”
宋书怀不禁感叹道:“难得你们都对她一片忠心,那我便不强人所难了。”
又闲话几句后,钟亦昭见时辰不早,心中又记挂花间袖事多,恐耽误了,便向宋书怀道了辞。
回来之后,钟亦昭途径后面假山之时,看见负责织补的程婶送来了半夏的一件织锦裙,正巧自己不在,林羽接待的,远远地只听林羽问道:“程婶,听口音你也是顾州来的吧?我也是由顾州跟着姑娘一道来的,如此说来,咱们都是老乡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程婶尽管开口,林羽定当全力相助。”
“老身确实是从顾州而来的,因来京城投靠亲戚不成,顾州也无甚留恋的,便在这里落了脚,也懒得再千里跋涉地回去,人老了,骨头也经不起这路途颠簸了。”程婶叹口气道。
林羽接过程婶递过来的包袱,解开来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道:“看程婶的气度,倒有几分大家夫人的华韵,不似贫寒门户出来的呢。”
程婶笑笑道:“这位小哥真会说话,怪道你们姑娘如此器重你呢。”
林羽又仔细端详了程婶一番,方道:“刚才一说,倒越发觉得程婶一副贵人相了,尤其是这鼻子,竟与我们念奴姑娘一样山根挺拔呢。”
却见程婶似是一惊,随即道:“这位小哥说笑了,老身不过残躯陋颜,如何能与你们姑娘的花容月貌相提并论呢。不知小哥还有其他吩咐没有,如是没有的话,老身就先行告辞了。”
送走了程婶,林羽便将包袱交到了翠鸣手中。回来的路上,这林羽便越发觉着事有蹊跷,自己虽是知道这念奴并不是当初的那个念奴,且她那时并不是一个风尘女子,看穿戴打扮,似是大家闺秀一般,那她为何甘愿来这烟柳肮脏之地呢?她究竟从何而来,所为何事而来?还有那翠鸣,她为何如此甘心听命于这念奴呢,她得了她多少好处?还有钟亦昭,当初不过是水烟阁一个不起眼的小厮,甚至还不如自己,可是谁承想如今竟是这般得姑娘信任,谁知道背地里都得了多少好处?当初本想着随着钟亦昭一道攀个高枝呢,哪知到头来也不过如此,虽是比在水烟阁跟着妈妈是要好上学多,却终究比其他的小厮丫头好不了太多,并没得到特别的照拂,连每日的吃酒耍钱都不敢尽兴。想至此处,林羽禁不住又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