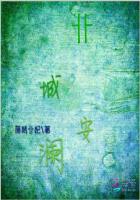周其山出门上了车,诚一才轻轻开口,“主子,我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诚一与周其山不知一起出生入死了多少次,对于诚一与其说是对待属下,不如说是对待兄弟,因此对诚一他也很有耐心。
“只要将沈小姐带到老爷面前,一切自会明了,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周其山转过头,“你想的太简单了。周其海毕竟是父亲的儿子,不管他做了什么错事,父亲都不会将他真的怎么样。更何况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沈家,如果到时候沈罗音倒戈,我们才是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诚一不再言语,他向来佩服周其山,思虑周全也狠得下心,只要是他想做的事便一定能做到,假以时日,他相信这个主子一定会成为一代枭雄。
“之前吩咐你做的事怎么样了?”周其山不知诚一的想法,自己在心中先将计划重新捋了一遍,以求万无一失。
“已经按计划布置好了。只是如果顾小姐…”诚一没有把话说完,意思却不言而喻。
周其山看着车窗外依旧灯火通明的聊城,许久才出了声,那声音听起来微弱又空洞,仿佛另一个人在说话,“能救最好,救不了…”他停了下来,脑子里闪过了很多张顾明月的脸,难过、嗔怒、怀疑、乞求,似乎他见过了顾明月所有的样子,终于,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定格到了顾明月的笑脸,那好像是在剧院,她想到成功捉弄了自己时露出的窃喜。
“救不了,就别让她走得太痛苦。”
得到沈罗音出逃的消息前,周其海正在于淑芳那里挨骂,显然于淑芳已经猜到了此事是何人所为,她一再叮嘱这个儿子要沉得住气,却不想他还是没有忍住先动了手。
“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一定要忍,你怎么就是不听!”于淑芳显然是气急了,一点都没有往日端庄高贵的样子。
周其海正跪在地毯上,嘴上却没有丝毫的服软,“母亲,我忍不住了,我和周其山斗了那么多年,现在就是我们分出高下的时候。”
于淑芳听到这话,更加生气,转身便给了周其海一个耳光,“蠢货!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你会是什么下场?就算你父亲能留你这条命,你也没有资格再去和周其山争那个位子。我们忍了这么多年,要的是一击制胜,不是百密一疏!”
周其海听到这话,向前膝行了两步,抓住了于淑芳的衣角,“母亲,就算儿子能忍,儿子也不想忍了。那个女人死了那么多年,你都始终得不到该有的名分。只有周其山死了,你才能名正言顺地当周夫人啊,儿子不想母亲再受这份委屈了。现在我和周其山,势必要争个你死我活。”
听到这话,于淑芳也不再忍心责怪周其海了,是啊,周其海的心情她怎么可能不理解。赵凤仪是周麓昌明媒正娶的正室夫人,而自己只是家族为求自保而送来邀宠的妾侍。若不是自己有几分手段,会讨周麓昌欢心,只怕会过得更加凄惨。饶是如此,前些年赵凤仪在时,自己吃饭不能坐着,穿衣不能穿正红,更不能上周家族谱,其中种种她都可以忍,唯独忍不了两个儿子和她一起被人看低,所以她才要争,只有争到这周家的权,两个儿子才能挺起腰杆地做人,而不是像她一样,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
和于淑芳想的一样,周其海也的确是无法再忍了,从被发配渭西开始,他就暗中扩张势力,为的就是和周其山决一死战,只要事成,到时候父亲只剩下自己和其林两个儿子,也就无可奈何了。
“夫人,有人送信给二少爷。”门外传来了丫鬟的声音,周其海开门取了信,拆开粗看了一遍,顿时脸色大变。只是很快,他就平静了下来。
周其海转过身,望着于淑芳,“母亲,你可曾记得我九岁那年的家族祭祀。”
听到这几个字,于淑芳心中一痛,她怎么会不记得呢。那年的家族祭祀,她趁着老夫人不在,向周麓昌哀求了半个月,才求来了其海和其林出席祭祀的机会。按照规矩,这两个儿子只能在成年之后才能在祭祀露面,这也是周家几代以来的传统,为的就是给正室夫人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只是她实在不想其海和其林再被人议论,所以才寻得了这个机会,想让他们提前露面,以示在周麓昌心中,这两个儿子的份量不比周其山轻。只是想不到,老夫人得了消息,从外地匆匆赶了回来,在祭祀上,命人生生把其海和其林拉了出去,还把自己和老爷痛骂了一番,让自己颜面尽失。她永远都没办法忘记,那天晚上,其海脸上挂着泪痕,怯怯地问奶奶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是不是自己和弟弟做错了什么。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她下定决心,一定要争到这周家,让两个儿子称为名副其实的周家继承人。
看着于淑芳的表情,周其海便知道她也没有忘记那件事,他缓缓开口,语气里满是决绝,“儿子养精蓄锐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刻,只要事成,从此母亲便是名正言顺的周家夫人。要是儿子败了…”周其海声音低了下来,“只求母亲照顾好自己和其林,不要想着替儿子报仇。”他这话听起来竟像是遗言,是啊,周麓昌不会杀他,可是周其山会,谁也不能保证今天过后,活下来的是他还是周其山。
说完,周其海跪下向于淑芳磕了三个头,便起身大步走了出去。留下于淑芳在原地,她不敢转身去看周其海的背影,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祈求这个儿子千万不能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