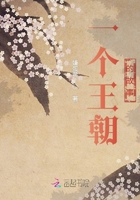“巧了。”
她们一愣,向门口望去——
那男子一袭青衣,清瘦修长的手里执着把飞花揽月扇,兰枝玉树般孑然立于琉璃灯下。
重毓心下一震,呆愣地和那人对视着。
这人好好的宰相不当,怎跑来做回老本行琴师了?
此人往日里遥不可及得如话本里才有的北澜神君一般,也不知是不是因着夜间街上万家灯火衬托的缘故,如今看来,竟不似以往那般清冷疏离了。
“小二,倒茶!”
重毓回过神来,敷衍着应了一句,才发觉那人早已被唐佛如殷切地迎了进来,男男女女一大群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他进了戏厅。
怎会是他呢?
重毓又朝戏厅望了一眼。
“大哥来了?大哥怎么来了?”颜儒胥猛地从柜台后的角落里爬起来,手里拿着卷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旧书。
重毓扯了扯嘴角,收拾着桌上的碗筷,一面垂眸笑道:“成天打着第一琴师的名号招摇撞骗的人除了他将迟还有谁。”
若是唐寒栖肯当众奏琴一次,将迟这名号定是不保的。只可惜唐寒栖远在云河的肆水城,没法千里迢迢的赶来青葵拆这厮的台,只能将这名号拱手相让。
“我看看去。”颜儒胥一听真是将迟,丢了书便往戏厅跑去。
自打重毓二人到这酒栈以来,还未见过这么多的客人。一个跑堂的一个算账的,还有个掌柜,平日里人少还算够用,人一多便忙得找不着北,光是端茶送水便能叫人累得吐出口老血。
也不知这些个酒客是慕名将迟这琴艺还是看上了他的皮囊,点的点酒要的要小菜,更有的哪怕听困了要床被褥也不肯走,一场接一场听个没完,直至半夜三更重毓才得了闲。
许是累昏了头,她在大堂里随意找了张桌子,刚一趴下就睡熟了。
重毓梦到自己回到了苍州城。
那一年她奉命率军北上进攻蛮涯,连收敌国十三座城池,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到之处尸横遍野。
这些城池,都曾是云河的失地。
苍州城是当年蛮涯攻下的第一座城,也是重毓收复失地的最后一座城。
重毓梦到自己动弹不得,手无寸铁的站在头颅堆里,只能眼看着成千上万支利箭燃着熊熊火光从城墙上铺天盖地的覆下来。
就在将死之际,画面猛然一转,她又回到了王都里。
大殿上,重毓看见自己穿着白色的囚服,伏首跪拜于地,殿上坐着一袭墨袍眉目漠然的将迟。
“你当真要去?”他问。
重毓醒过来,发现身上盖了层被毯。
烛火已熄,四下一片寂静。
她失神地呆坐了一会,静静地看着从高窗上斜斜的投了进来的月光。
重毓本以为离了云河便不会再做这梦了,奈何将迟却突然出现在了这里,还鬼使神差的是她债主的师父。
莫非是前辈子欠的不成?
回厢房时,重毓又意外督见那人独自在小亭里下棋。
石桌上燃着一支残烛,昏暗的火光在黑夜里摇晃着,映得棋子温润如玉。将迟执子不动,眉毛微蹙。
“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重毓抱着被毯,远远的看着他,淡然出声。
将迟轻笑一声,落下一子,也不看她。
重毓不死心,问:“有这么巧?”
“殿下何意?”将迟停了下来,侧首看向她,眼眸清明而干净,宛若天上星河。
重毓瞪他一眼,左顾右盼了一会儿,叮嘱道:“出门在外,不分劳什子君臣,好好说话。”
她甩手把被毯扛到肩上,轻哼一声,“倒是你,费尽心思做上了宰相,跑来这犄角旮旯做什么琴师?”
“倒也说不上费尽心思。”将迟微微一笑,反问:“准你跑堂,就不准我卖个艺?”
重毓被烛光晃得厌烦,问:“王上派你来监视我?”
“近来边疆少有战事,王上无需用你,自不会多管。”将迟顿了顿,又道:“况且我此番来青葵,未曾料到你会在。”
少有战事,无需用你,不会多管。
重毓默念着这句话,不知怎么又想起了方才梦里的景象。她似笑非笑了一声,“早知你今日如此辉煌,我当初便不去肆水了。”
十年前兵变事发,重毓是四皇子一派所有叛军里唯一活下来的人。当初她被人构陷押进大牢时原本有另一拨人要将她救下,结果却意外被揭竿而起的四皇子重廷趁乱救了下来,这才“莫名其妙”混进了重廷一派的叛军中。
四皇子谋反败北一行人皆被押禁于水牢时,重毓早知自己不会死。倘若王上重启赵下令要将她诛杀,只需重毓一声令下,云河内外分散于天下忍辱负重了十余年的安王遗党顷刻就会举兵四起,虽说未必可使江山易主,掀起一场载入史册的血雨腥风却还是轻而易举之事。
就在那千钧一发之时,当时还只是琴师的将迟找到在水牢里泡得发肿的重毓做了个交易。
重毓承诺他十年之内不再插手安王遗党之事,相应的,将迟答应替她办一件事。那一次重毓本可要求他带她离开王都从此归隐山林,可重毓却说,她想去肆水充军。
如今十年弹指一挥间,将迟成了只手遮天的当朝宰相,而重毓一路功勋累累,年纪轻轻就占据了青云司一席之地。这十年就像是一瓢冬日冰冷的河水,将他们二人曾有过的情意缱绻浇灭了个干净。
听得重毓此番言语,将迟只是沉默片刻,带着些许淡漠,道:“当初你一意孤行,我也别无他法。”
“也是。”
将迟仍是那副漠然的样子,不再看她,蹙眉又执起一枚棋子,全神贯注地下了起来。
重毓呆望他片刻,默然离开。
打从记事起,姜伯伯便常训导她何为忍辱负重,何为任重道远。她深知自己不仅背负着当今王上也就是她的皇叔重启赵杀父害兄的血海深仇,更承载着衷心奉主誓要报仇雪恨的各地遗党的殷切期盼。
正因如此,重毓才自幼刻苦研习武式仙决,所谓纵横捭阖、帝王心术、谋攻画策等更专有前朝老臣悉心教导,一日都不曾落下。
谁料十岁那年肆水城战火纷飞,重毓意外与母亲离散,尔后飘零流落至秦环城整整六年,才又被当时的太监总管高策发现并带回王都假冒失踪多年的十一皇子。
儿女情长一事,于重毓而言实在有些虚妄。
这日夜半时分,有人敲起了大门。
重毓的厢房离大门最近,平日里睡得又浅,这模模糊糊的声响将她吵了起来。可她睁开眼睛,外面又安静了。闭上眼睛没多久,敲门声又响起来,伴着野猫子发春般的呜咽声。
重毓疑心顿起,一个翻身便从床上起来推门朝大门口走去。
“姐姐,姐姐……”
“我不想死!”
“救救我,救救我!”
门外隐约传来几声断断续续的呼喊声。
重毓心下一惊,忙将门栓拉开,沉重的大门发出尖锐的吱呀声响,一拉开门,她就看到门口台阶上趴了个小孩儿。
男童七窍淌血,染红了白天重毓刚拖过的的石阶,一直流到街上的青石板上。栈口挂着的琉璃灯照清了小孩儿的身子,他袖口处露出来的两截手正以极为诡异的形式在痉挛。
重毓认出来人的身份,这才发现他原本灰色的布衫染上了成片的血迹,如今已几乎成了深紫色。
她只觉太阳穴处一阵抽痛。
重毓蹲下身去想要打昏冰糖,一只手却忽然伸过来拦住了她。
“做什么?”唐佛如沉着脸,问。
她似乎是听见了门口的动静匆匆赶来的,额头上都起了一层密汗。
“自然是帮他。”重毓道。
唐佛如深深得看了眼趴在门外半死不活的冰糖,深吸了一口气,叹道:“已经没救了,不必管他。”
重毓一愣,“他还喘着——”
“城里有人得过这种病,他马上就快死了!”唐佛如争道,说着便要关门。
重毓倏地站起身,神情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个个子还不到自己胸口的小丫头,推开她道:“我抱他去医馆。”
“不准去!”唐佛如红着眼眶大叫一声,死搂住重毓的胳膊,“店里的生意刚好起来,你是我们酒栈的伙计,抬个死人去医馆,别人会怎么看?!”
“我不做你家伙计了行不行?”
“不准,你和你弟弟还欠我一万两银子。”
重毓气急,又怕伤着唐佛如,只得敷衍说:“我枕头下有把剑,姑且当给你,等我回趟家立马还你银子,再多给你五百两。”
“你那把破剑值个什么价?”
重毓眼睛一瞪,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
正在两人僵持之际,唐佛如身后忽然传来颜儒胥一声大喊:“黄毛丫头,你还不快走,你师父要来了!”
唐佛如一怔,回头望了一眼,顿时手足无措起来,她低着头绞了绞袖子,带着丝哭腔咬牙道:“你们爱救就让你们救好了!”说罢便气冲冲的跑开了。
这雷打不动的女大爷一走,重毓舒了口气,立即点了冰糖的昏穴,扛起他便直往最近的医馆奔驰而去。
“出什么事了?”将迟赶到时,只看到一阵风似的背影。
颜儒胥干笑着挠了挠脑袋,指了指天空,道:“今天月亮好圆。”
待重毓找了家客栈将冰糖好生安置下来后,尖嘴猴腮的黄鼠狼医师才抱着他的药箱子姗姗来迟。
黄鼠狼刚一进门,只简单瞧了床上面如死灰的冰糖一眼,便连连叹气,给他开起了药方子。他说,冰糖得的恐怕是这几年城里令人闻风丧胆的“焚骨病”,正如唐佛如所言,不久便要死了。
“最多还能活多久?”重毓问。
黄鼠狼吁了口气,抓耳挠腮了一阵,说:“短命点儿,兴许今天就死了。不过也有人活了两三年,就那城东的老徐,不过人家是靠人参灵芝餐餐供着,说白了就是拿白花花的银子买命。”
他站起身来收拾好东西,出门时不忘好意嘱咐了一句:“这病是车石传来的,也不知道会不会传染,你们还是小心着些,得上可就必死无疑了。”
“欸,外边天黑,我送您一段儿。”颜儒胥拍拍重毓的肩膀,跟了出去。
冰糖躺在床上,呼吸时喉咙里发出阵阵嘶鸣,脸上呈出一种将死之人才有的蜡黄之色。重毓用热水泡过的布巾将他身上的血迹擦洗干净后,颜儒胥刚好拿着方子抓完药气喘吁吁的跑了回来。
“回去歇会儿吧。”重毓接过药包,动作熟稔的扇着柴火。
颜儒胥摇了摇头,“我在这儿陪着他。”说着便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本书,倚着墙角读了起来。
清晨必读书,这个习惯打从重毓第一次认识颜儒胥时他便有了。
还是他们二人在军营里的时候,有一次颜儒胥没跑得及被蛮涯俘获作人质,大早上在人家牢房里吵着狱卒要本书看,气得别人随手丢了本蛮涯的律法与他,竟也照样读得津津有味。
后来重毓把他救出来,颜儒胥第一句话便抨击起蛮涯的律法来,直说它过于严苛,动不动就诛连九族,难怪人少得可怜。
温暖的火光在重毓的眼前跳动着,驱散了深秋清晨刺骨的寒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草药蒸煮时独有的苦涩,缠绵湿润,惹得人直打瞌睡。
脑子的往事忽如走马灯般回放起来。
重毓撑着脸慢慢的晃着手里的竹扇,眼皮打起了架,终于睡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