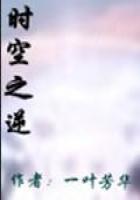雀官一怔,低头想了半天,才摇头道:“我父母只生了我一个人,芸娘便是我的亲妹子,我对她只有兄妹之情,除此之外,别无他想。婚姻之事,再也不要提,免得芸娘听了心中不高兴。”
田七“哼”了一声,怒道:“芸娘便象天上的仙女一般,哪一点配你不上?我看你虽然英雄了得,芸娘配你却还绰绰有余。”武班见他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忙道:“田七,你醉了!不要胡言乱语!”又忙对雀官道:“兄弟,都是做哥哥的不好,我见你们郎才女貌,十分要好,才说起这个话头,照理说这话头不应该由我说起,得由你们长辈们来说才是,却是我唐突了。”
雀官道:“我和芸娘一同长大,便象是一家人一样,只有兄妹亲人之情,却从来没有想过男女之情!今天哥哥们说起来,我刚才仔细的想了又想,心里只是把她当作亲妹子。”田七厉声道:“我看得出来,芸娘对你十分喜欢,你却说出如此话来,岂不是要伤透了她的心!如果是我,连性命也可以给她,不象你这样无情!”雀官摇头道:“我也能为她做任何事情,也可以为她不要性命,但委实心中没有半点男女之情。”
田七还想要说,武班与罗铁锤便一同按住了他,道:“你喝醉了,不要再说胡话。”田七哼了一声,不再言语,端起碗来,将一碗酒一饮而尽。
便在此时,猛然听得“砰”的一声响,一坛酒摔落地上,酒水四处流淌,芸娘脸色惨白,站在门边,身子颤抖,雀官猛然一惊,只喊得一声“芸娘”,便见芸娘猛然转身,冲进内堂,雀官拔脚便追,却见她已经进到房里,砰的把房门关上,把门栓栓得死死的。
雀官拍门喊道:“芸娘,开门。”房内寂静无声,又喊了数十声,才听芸娘冷冷道:“你只管来烦我做什么?我累了,要歇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罢。”便不再作声了。雀官等了许久,竟不知再说些什么,只好转身回厅来,心中茫然若失。
武班等人见到这样的情景,不禁面面相觑,心中万分懊悔,等到雀官回转,都默默无语,也告辞去了。雀官心中纷乱,独坐在厅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脑中一团乱麻,他本喝酒便喝得有八九分醉意了,过了许久中,竟不知不觉伏在桌边睡着了。
且不说雀官在厅外独坐,只说那芸娘,她和雀官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她自己貌美无伦,雀官也是俊朗如玉,哪一个见到的不说是他们是一对壁人?何况雀官从小对她百依百顺,万般呵护,就是她平常使性子的时候,也处处依着她,女儿家原本比男子要懂事得早些,她情窦初开,便已芳心暗许,一缕情丝,便已系在他身上。
此次出门,她见雀官为她不计生死,将她瞧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不禁心中无限欢喜,已是满腔柔情,只道是郎情妾意、至死不渝,只等到再稍大一些,父亲便会为自己作主,将自己嫁与雀官,那时便是花好月圆,长相厮守,她每每想到这里,常常独自一人笑出声来。
今天在桌上她见雀官陡发豪气,气概不凡,又听见别人夸奖他,心中十分自豪,眼见情郎英雄不凡,自己所托得人,不觉柔情无限,平时喜欢和雀官争辩的性子也不耍了,更亲自去为他们拿酒。她在后院找到了一坛陈酒,欢欢喜喜的来到堂前,刚走到门边,便听到雀官的言语,顿时如坠冰窖,一腔柔情,尽化作刺骨寒冰,越听越觉手足冰冷,那坛酒不觉竟失手掉落地上。
此时她坐在床沿,泪水泉涌而出,她本来性子就刚烈,既然喜欢一个人时,便已经是死心塌地,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相思,竟然都是自己一厢情愿。此时心中便如刀割一般,连嘴唇都已咬出血来,胸中无限酸楚,脑中每次闪过雀官影子,便象是喘不过气来似的,只是任那泪水滂沱而下,将床上的被子都打湿了。
她回想从小和雀官相处的情景,便象是昨天,历历在目,但自己刻骨铭心,想要共度一生的良人,却原来同自己并不是一般心思,自己无数次幻想的花前月下、良辰美景终究是化作一场梦幻泡影,自己的一腔深情,终究错付了人!不觉悲从中来,伤心、愤怒、绝望、期盼、难过、酸楚纷至沓来,一时之间脑中似乎万念杂陈,又似乎空空如也,连那魂魄也象是飘散了,无处寻觅,到处一片茫茫,只觉胸中一闷,喉头一热,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芸娘口中鲜血喷出,染红了衣衫,只是呆呆坐着,一动不动,只要一想起雀官,便觉心中一酸,那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但若要她不想,却又怎么能够?
她心中柔肠百转,只觉天地茫茫,竟不知何处才是归宿,心中想到,倒还不如就此死了罢了,好过受这无边无际的苦楚。蓦然间,她又想起父亲来,在这天地之间,依然有一个不论何时都会爱她、宠她、将她看得如珠如宝之人,自己不如便去河间府寻找父亲,一辈子守在父亲身旁,与那雀官再不相见,想必便不致于如此伤心欲死了罢?她想了良久,便起身擦干血渍泪痕,又换了衣衫,将些物银两包了,背在背上,又写了封书信留在桌上,将那“云魄”宝刀紧紧拿了,打开房门,轻轻走了出来。
她来到大厅之前,见雀官正趴伏于桌上,吃了一惊,转身就想往回走去,却见到雀官因为夜里喝了酒,已经沉沉睡去,并没有察觉。
这时夜已深了,凉意渐浓,她见雀官衣衫单薄,不觉心中一软,从旁边椅上拿起一件衣衫,轻轻披在雀官身上,走到门口,不觉又回头看了一眼,泪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