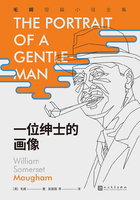州警离开后,下午已然过半。我躺在床上,感觉好起来,同时也因为这种感觉本身而感觉更加好了。我躺在这儿,回想着安珀之中蕴藏的危险。布兰德和我都被族人最钟爱的武器放倒了。我在想谁的伤势更重。大概是他,那一刀可能刺到了他的肾脏,而且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很糟。
在比尔的雇员把文件带来让我签署之前,我已经跌跌撞撞地在房间里走了两个来回。了解自己的极限是很重要的。一向如此。既然在这个影子里,我的康复速度要比常人快上几倍,我想经过大概一天半——或许是两天的休养,我应该可以站起来走动了。我确定自己可以做到。很疼,而且头一次尝试让我感到阵阵眩晕,但第二次就好多了。当然还是会晕。所以我又躺回床上,感觉好些了。
我无数次捻开主牌,玩些单人牌戏,从熟悉的面孔中读出那些暧昧不明的运势。每次我都要控制自己,压抑住联络兰登的欲望,我想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然后询问一下事态的最新发展。再等等,我不断告诫自己。他们每睡过一个小时,对在地球的你来说,就是两个半小时。而这里的两个半小时,对你来说相当于那些凡人们的七八个小时。忍耐。思考。恢复。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流逝,晚餐过后,天空开始阴沉,我决定展开行动。一个古板的年轻警员曾来查问情况,我把所有想告诉他的话都说了。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但他很客气,而且没待多久。实际上,他刚刚离开。
躺在这儿,感觉自己在逐渐好转。我等待着贝利医生来巡房,来查看我是否逐渐康复。躺在这儿,思索着比尔告诉我的事情,尝试将它们和我已知或猜测到的事拼凑起来……
感应到了联络!我已经料到了。某个在安珀的人起得真早。
“科温!”
是兰登,声音有些不安。
“科温!起来!开门!布兰德醒了,他想见你。”
“你刚才敲过门想要叫我起床,对吗?”
“是的。”
“就你一个人?”
“对。”
“那好。我不在里面。你正通过影子联结到我。”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我受了伤,但还活着。我以后再给你讲这事。跟我说说布兰德。”
“他不久前刚醒过来,跟杰拉德说必须马上见到你。杰拉德摇铃叫了一名仆人,派他到你的房间去。他叫不醒你,就来找我。我让他回去告诉杰拉德,就说我马上带你过去。”
“我知道了。”我说着慢慢直起身,坐起来,“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我拉过去。我丢了几件衣服,需要一件罩袍之类的东西。”
“那我最好回自己的房间去。”
“好的,去吧。”
“一分钟就好。”
联结中断。
我慢慢挪动双腿,坐到床边,收好主牌,放回盒子。我觉得应该在回安珀前掩饰好伤口。这很重要,就算在平时,一个人也永远不该暴露自己的弱点。
我深吸一口气,抓着床架站起身。练习有了回报。我保持着正常呼吸,松开手。不坏。我可以勉强维持形象,只要走慢点,只要别用力过度……我也许可以带伤行动,直到力量完全恢复。
这时我听到一阵脚步声,一名态度友善的护士出现在门口。她身材纤细、匀称,如雪花般明丽,但又不像雪花那样千篇一律。
“回到床上去,科里先生!你还不能起来!”
“女士,”我说,“我必须起来,这很重要。我必须去。”
“你可以按铃,请护士拿个壶来。”说着,她进入房间,向我走过来。
一等兰登的联结再度建立,我就冲他疲惫地略一点头。我很想知道她会怎么报告这件事——还有她会不会提到我跃迁后留下的五光十色的残像。我留下的市井传说越来越多了,这是最新的一条。
“亲爱的,请你这么想,”我对她说,“我们之间的联系是纯粹物质性的。但除此之外,世间还有别的联系……而且很多。别了!”
我鞠了一躬,送给她一个飞吻,同时向前一步迈入了安珀。她留在那里,手抓向眼前的虹霓幻影,而我则扶着兰登的肩膀,摇摇欲坠。
“科温!怎么……”
“如果鲜血是海权的代价,那我流的血足够给我买个海洋了。”我说道,“给我找点衣服穿。”
他把一件厚重的长斗篷披在我肩上,我摸索着系好了脖子上的扣绳。
“准备就绪,”我说,“带我去见他。”
他将我领出房门,进入过廊,走向楼梯。这一路我几乎都靠在他身上。
“有多糟?”他问。
“刀伤,”我说着把手放在伤口上,“昨晚有人在我的卧室里袭击了我。”
“谁?”
“嗯,不可能是你,因为我刚和你分手。”我说,“杰拉德正在藏书室陪布兰德。除去你们三个,要让我猜的话。最可能的是……”
“朱利安。”他说。
“他的行情显然看涨,”我说,“菲奥娜昨晚一直在跟我说他的坏话,而且我不喜欢他,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科温,他跑了。朱利安夜里离开了。仆人找到我,告诉我朱利安已经走了。你怎么看?”
我们走到楼梯。我一只手扶着兰登,休息了片刻。
“我不知道,”我说,“有时候猜测得太远,和完全不猜想一样糟糕。但我觉得,如果他认为已经搞定了我,那么待在安珀假装对此事做出惊异的表现,要比落荒而逃强得多。这么做确实很可疑。我倾向于相信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害怕布兰德醒过来后要说的话。”
“但你还活着,科温。无论袭击你的是谁,你都逃出了他的手心,而且他不能确信是否已经把你搞定了。换作是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跑到哪个影子世界去了。”
“也有道理。”我对此表示认同,然后我们继续向楼下走去,“是的,你可能是对的。现在先把这件事留在理论阶段吧。而且别让人知道我受伤了。”
他点点头。
“按你说的办。在安珀,一声不吭比四处张扬强得多。”
“什么?”
“沉默是金,阁下,是牌里的同花顺。”
“兰登,你的机灵劲儿弄得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无论是受伤的部分,还是没受伤的部分。还是把你的机灵分点出来想想凶手是怎么进入我房间的吧。”
“你的门闩?”
“从里面插好了。我现在一贯如此。而且门锁也是新换的。谨慎起见。”
“好吧,我想到了。我的下一个答案有个先决条件:凶手是咱们家里的人。”
“告诉我。”
“为了伏击你,有人情愿振作精神,再次接受试炼阵的考验。他去了下面,走过它,把自己投射到你的房间,然后袭击了你。”
“这个答案几近完美,只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几乎都是同时离开的。袭击并非发生在夜里晚些时候,我刚一进屋,他就来了。我觉得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中的某个人到下面去,独自穿越试炼阵。袭击者早已等在屋里。所以,如果是我们中的人,他必须通过其他方法才行。”
“那就是他撬了你的锁,只需一点小窍门就行。”
“有可能。”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中间的楼梯平台,并继续向下走去,“我们在拐角处休息一下,这样我可以不用帮助,自己走进藏书室。”
“没问题。”
我们这样做了。我打理好自己,拉过斗篷盖住全身,挺直肩膀,走过去敲响房门。
“稍等。”杰拉德的声音。
有脚步声向房门靠近……
“谁?”
“科温,”我说,“兰登和我在一起。”
我听到他向后问了一句:“你也要找兰登吗?”然后是轻声的回话:“不。”
门开了。
“他只见你,科温。”杰拉德说道。
我点点头,转向兰登。
“待会儿见。”我说。
“掀开你的斗篷,科温。”杰拉德命令道。
“没必要。”布兰德开口说。我从杰拉德的肩膀望过去,看到布兰德正背靠几个软垫,半躺半坐在沙发上。他冲我展颜一笑,牙齿有点黄。
“抱歉,我不像布兰德那么信任别人。”杰拉德说,“而且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让我看看斗篷下有什么。”
“我说了没必要,”布兰德重复道,“不是他捅的我。”
杰拉德猛一转身。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他问。
“还用说,因为我知道是谁干的。别犯傻了,杰拉德。要是我有理由怕他,就不会叫他来。”
“我把你带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失去意识了。你不可能知道是谁干的。”
“你确定?”
“好吧……那你干吗不告诉我?”
“我有我的理由,而且合情合理。我现在要和科温单独谈谈。”
杰拉德低下头。
“你最好不是在说胡话。”他说着走到门前,开门,“我就在附近。”他补充了一句,这才在身后关上房门。
我走过去,握住布兰德伸出来的手。
“很高兴你能回来。”他说。
“你也一样。”我说着拉过杰拉德坐的椅子,努力不让自己瘫倒在椅子里。
“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
“糟透了。但换个角度来看,比过去几年好多了。都是相对而言。”
“大多数事情都是如此。”
“安珀不是。”
我叹了口气。
“好吧。我不想玩文字游戏。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盯着我,双目如炬,在搜寻着什么。什么呢?我猜是我掌握的情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掌握的情报。负面的东西通常更难估量,他的脑子必须转得够快,必须从醒过来后就开始思考。我了解布兰德,他对我不知道的事情更感兴趣。除非万不得已,他决不会透露半点信息。他只想搞清楚一点: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少需要透漏多少情报。他不会浪费一瓦特的功。这就是他的行事之道,而且他肯定是想要什么。除非……最近几年,我比过去更加强烈地想要让自己相信,人是会变的。时间的流逝,不止会使本性更加稳固,有时也会改变一个人的本性,这全看他们的所为、所见、所想、所感。在世间万物仿佛都要脱轨的时候,这无疑是个小小的慰藉,更不用说它对我的世界观产生的巨大震动了。还有,布兰德很可能曾经挽救过我的性命和记忆,无论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好吧,我决定向他透露点东西,但不会暴露底牌。一个小小的让步,这个行为有悖于我的家人在游戏开局时遵循的那种微妙默契。
“凡事都不会像表面那样简单,科温,”他开口道,“你今天的朋友,也许是明天的敌人……”
“别废话了,”我说,“摊牌时间到了。我很感激布兰登·科里为我做的一切,另外,是我想出了那个小把戏联结到你,把你带了回来。”
他点点头。
“我想,你肯定有自己的原因,所以才会重燃久已失落的兄弟之情。”
“从我这方面看,我同样觉得,你帮我肯定也有其他原因。”
他又笑起来,抬起右手,又放下。
“那我们算是扯平了,或者都欠了对方的人情,随你怎么想。如果说,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我想,这会大大增进我们的亲情。”
“你在拖延时间,布兰德。你想看我的底牌。我今天本来打算当个理想主义者,可你坏了我的兴致。你把我从床上弄起来,是要告诉我一些事。现在就请说吧。”
“还是过去那个科温。”布兰德笑着说,接着他转开目光,“真的还是吗?我在想……它是否改变了你,你觉得呢?在影子里生活的这段时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为别的事奋斗?”
“也许吧,”我说,“我不知道。嗯,我想是变了。这种变化让我对家里人常用的小手腕感到极其不耐烦。”
“实话实说,直言不讳,坦诚相告?这样一来,斗心眼儿的乐趣可就没有了。但这种新鲜玩意儿也不是没有价值。它会让所有人丧失平衡……打他们个出其不意……是的,这可能有用,也让人耳目一新。好吧!别慌。我的开场白到此为止。所有的俏皮话也都收起来。我会敞开胸怀,抑制住‘非理性’这头巨兽,再从黑暗秘境中夺回‘理智’这颗美妙的珍珠。但还有件事,不知你肯不肯帮忙。你有什么可抽的东西吗?这么多年了,我真想来点臭烘烘的烟草,或是其他的东西,来庆祝自己回家。”
我正要说没有,又想起书桌的抽屉里有几支香烟,是我留在那儿的。我真是不想跑这一趟,但——“等会儿。”我说。
我站起身,走过房间,努力让自己的动作显得随意且不僵硬。我在抽屉里翻找时,极力表现出只是将手自然地扶在桌面上,而不是用它来支撑我的大部分体重。我尽可能用身体和斗篷掩饰着自己的动作。
我找到了那盒烟,沿原路走了回去,顺便在火炉旁点上两根。布兰德从我手里接过他的那根,动作十分缓慢。
“你的手抖得很厉害。”他说,“怎么了?”
“昨晚的聚会玩得太晚了。”我说着坐回椅子。
“这我倒忘了。但我估计会有这种事,不是吗?当然了。所有人齐聚一堂……出人意料地成功找到我,带我回来……一个非常紧张非常心虚的人,做出绝望的挣扎……只成功了一半。我受了伤,闭了嘴,但能有多久?然后……”
“你说你知道是谁干的。这是玩笑话吗?”
“不,当然不是。”
“那么是谁?”
“别着急,亲爱的哥哥。别着急。因果与次序,时间与重点,在这件事里都很重要。请允许我在安全的回忆中品味这个戏剧化的故事吧。我能想见那一幕,我被捅穿,你们都围在周围。哈!我怎么没能看到如此精彩的场面呢!你能给我描述一下每张脸上的表情吗?”
“恐怕在当时,他们的脸是我最不关心的东西了。”
布兰德叹了口气,继续抽着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