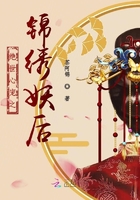李啸云鼻息所闻尽是赵瑗瑗身上的淡淡甜香,几乎令自己不得凝神静气,陷入想入非非的幻想之中,几经克制,不得不闭目静气,收敛脑中的种种迷惑心智的想法,不住地警告自己:“我不过暂且委身讨得此人欢心,实属虚与委蛇之计,待报了血海深仇,将仇人一个个杀尽,此人不再对我有任何用途,怎能动真情,难道因一时贪快却视爹妈尸骨未寒,冤魂不散不顾么?我李啸云活在世间妄为血性男儿。”
愈想愈气狭,对赵瑗瑗不过是逢场作戏,不曾动有真心实意,暗自发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是完颜宗_;给自己的忠告,也是从他身上学到的,如今看来你以真诚待人,并不能得到坦诚相待,何苦取悦于任何人。
劝慰赵瑗瑗道:“可福师弟,我看天色不早,总不至于在此露宿一夜吧?少林寺门规戒严,耳目众多,被发觉于大家无益。不如不如回房歇息,免得师伯祖担忧。”
赵瑗瑗羞滴滴地道:“好吧,今晚之事真是良宵美景,其意浓密,我必然铭心难忘,你关心我么?这个自然要听,反正”
闻她话到一半又不便开口,意味腼腆,足感心里美的甜滋滋,蜜奕奕,弄得自己也不明她到底要说什么,问道:“反正如何?”赵瑗瑗不答,依恋不舍地从他身上缓缓爬起来,顿觉浓情蜜意之时不便袒露心扉,一阵娇艳欲滴地用衣袖掩面窃笑,足显忸怩,娉婷。
李啸云一再掩饰自己的紧张与不安,未去注意此时的赵瑗瑗怎生妩媚姣楚,更令自己愧仄的反倒是骗取少女无邪天真,不惜以自己的虚情假意换取一份纯真爱意而做出有违良心的事,深表痛责,自己并非蓄谋已久,自己与面前这位炙手可热的帝姬更是身份天渊之别,若要博其信任必然是泯灭良心出卖自己尊严,但放眼天下,自己籍籍无名,又是个山野村夫,要令赵佶及其身边的狗党鹰爪为自己的身世付出惨痛教训,何况力单势薄、孤立无助,唯有在私逃的赵瑗瑗身上寻得机会接近仇家,否则要报家仇难如登天。
赵瑗瑗觉得今晚发生的一切都如同天降福祉,突如其来便至,自己又是自幼深荫家规庭训,就算再忤逆忌恨生世,也不敢直言不讳,在一位少年人面前积极表露心声,但有了心里的慰藉似乎满足踏实许多,一阵笑盈盈地快步抢回后院木门之内。
李啸云看着她欢欣愉悦、惬意无限的背影,那宽大粗鄙的缁衣也难掩她娉婷绰约的身段在黑夜中湮没,很快闪入院墙之内,本觉今晚之事都如愿以偿,甚为释然,反而半丝也高兴不起来,自己异常明白欺骗一位纯情少女是件多么令人不齿的行径,黯自神伤,愧疚痛惜。
一时胸臆填塞欣喜、自责、歉愧、得意、如愿、焦灼、无奈之情自恃难以抉择,不由在草地间熟练本相传授自己的那套“龙爪擒拿手”,以泄心中不畅。
这套高深坚刻的手法竟然不能了熟于胸,做到应变自如,刚才如是只消辨别赵瑗瑗出拳的劲风,或是方位便能将其一招制服,也用不着轻薄猥亵,有辱她的名节清白,从而令她误会自己也对其有好感,接下来的事或许用不着这么焦头烂额。一时难以痛快,全然单凭负气泄恨使出“龙爪擒拿手”的招式,“双龙抢珠式”、“蛟龙出海”“龙架祥云”、“青龙探海式”一练到“双龙抢珠式”不禁迟疑,嘲弄自己道:“又是这招,都是自己情急之下不加考虑,竟闹出今晚的笑话。”一想自己完全出于防备,才会情不自禁地使出龙爪手中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杀招,要不是及时收力,撤回大半劲道,恐怕更令自己悔恨不已,还哪有时间在此深究自责。
却不料一道稚嫩的声音惊叹道:“这不是可还师弟么?”李啸云猛然从梦中惊醒过来,不寒而栗,连忙收刹住拳脚,仆自站定,又恢寻常平日里那般兢兢业业的恳诚模样,生怕来者有所察觉,进而起疑自己出于何居心潜进少林。吃力地睁大双眼,来者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一大一小,依稀自己脑海中的记忆是那么眼熟,但心乱如麻却没有半丝兴趣去在乎来者何人了。
那个小和尚年纪也与自己相若,刚才的声音也正是他发出,从他身上所散发的一种难以抗拒的亲切,令人感到此人甚好相处。
在他身边年长的师兄却是冷冷地道:“哼!竟敢偷师学艺,趁大家不备,寺内安宁便在此处温故知新,终于掩饰不住,露出狐狸尾巴了。”李啸云一听正是当日在迎客亭戒剑石旁横加阻扰的可鉴,而身边的小和尚自然是可因无疑。
李啸云惶急,客气地站定行礼,揖身恭敬,足显自己的行止端良,暗叫糟糕,心下无措,只待能避过此劫才好,道:“原来是可鉴、可因两位师兄,不知深夜到此有何要事,不巧我也辗转难眠,出来活动惫懒松散的筋骨。”
可因正欲开口,全被可鉴鄙夷冷峻的言语拦住,骂道:“被我师兄弟捉个正着,还在闪烁其词,真是隐晦之深,狡狯之极,不尽不实,还要我等亲自动手不成?”可因生怕师兄的脾气过于暴躁,从而闹得同门情谊失和,劝慰道:“师兄,可能真如可还师弟所说出来散心也说不定,何必一本正经,弄至不可开交呢?”
可鉴哼哼冷笑,反讥道:“也只有你这种懵懂无知的小孩子才会被他蒙蔽,虽说夜深一时看不清,但凭他刚才出手时的劲风与矫健身法不难得知,怎能糊涂认为是出来活动筋骨这种掩耳盗铃可笑举动。你真不会隐情不报,就此敷衍搪塞了吧?”
李啸云不敢插话,何况脑中正在担忧如何应对良策,如是就此得过且过最好为妙,可惜的事可因年纪尚小,全无相庭抗力的辨能,不敢与这位刚正不阿的可鉴反驳,只听他胆小怕事,却又不想无情,念及师兄弟之间和气一团的气氛,似乎更加珍惜身边所有的人,劝道:“可鉴师兄,师父常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要令可还师弟难堪,就此受到廷杖责罚之苦,难道不能饶他一次,日后大家照样还是师兄弟。”
可鉴俨如一副铁石心肠,不从可因的劝说,训斥道:“那你又忘了师父还说偷师学艺便是武林一大忌么?是为武林所不齿,平日里装得老实巴交,背地里却不知干了多少坏事,我问你,来少林寺到底存有何居心?”
李啸云可不是那种暂忍一时之气便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安分性子,从小便是受尽****,遭受不凄待遇,更对旁人白眼鄙夷更是嫉恨在心,哪能任由别人践踏自己的限度,挺身凛然地道:“我不过胡乱打了一通,师兄诬赖我偷艺,屈打成招,我便是百口难辩,你若秉公执行,师弟我悉听尊便,听候发落便是。”
可鉴呼呼气喘,不想这个后进小子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犯了错还理直气壮地顶嘴,恨恨地道:“怎么?你当我是看花了眼还是存心诬陷好人,抑或是蓄意找你晦气不成?我看你是不知悔改,嘴硬狡辩,浮滑不实定是你的本性,是不是冤枉你,只消验证便是。”
说着跃跃欲试,准备上前动手,可因这时拉住可鉴,劝道:“师兄,难不成真要可还断绝佛门因缘不成?就不能念惜同为受难,心生恻隐?”
可鉴冷哼道:“少林寺已然落得香火渺渺、声威败损,在武林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还被天子逼迫要向道家低头,整日戴冠执简,纳入玄门,真是颓败不堪,如再由别有用心之人胡作非为,传入同道耳中还道我少林寺连叛徒都纵然,姑且放任不管,还有何颜面?”
可因又道:“这样做反倒于现时少林寺声威有益?何以见得?既是同门,念及情谊,就此放他一次,必然感恩戴德,计较少林好处,更加勤奋刻苦为少林寺重整竭诚竭力,何不快哉,逼人太甚,反违背佛祖意愿。”
可鉴不听,干笑道:“师弟真是考虑周全,禅机深刻,师兄真是愧为师兄,不过少林寺以清规戒律为根,以公道正派立本,在武林之中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无论上至方丈、下达行脚知客,头陀沙弥,犯了过错,必然受罚,绝不姑息,难道单凭他一人便能废除千百年少林的规矩,何况门庭森严,江湖中人无不对我等直竖大拇指,赞其好样的,你我从不敢丝毫违拗,就连方丈太师伯也是如此,定是他半路出家,心境不纯,六根不尽,才导致怙恶不悛,遗害无穷。”
可因心底善良,纯真率直,不及可鉴为人正直,听他的言辞激越,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焦急自责地向李啸云道:“可还师弟,我”
李啸云深表感动,也不想他处于两难危境的窘态,向他所站的方位,微微笑道:“师兄的心意我可还心领了,感激不尽,但这位可鉴师兄处处为难,咄咄强势,实在可恼。”
“你说什么?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看来你早有预谋,我问你,到底来我佛门有何贵干,居心何意?”可鉴乍然一听李啸云对可因小师弟如此客气,说到自己时丝毫不顾年长于他,语气过激,不由恼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