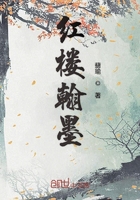李啸云倒钦佩他们的一诺千金,但凡行走江湖的,不以善恶,大多是言出必践之人,出尔反尔者很少有朋友在身边。他们既然都答应自己,也全无顾虑,自己在几日前犯过一错,吃一堑,多了留心谨慎,免得又误伤措意,无后顾之忧的束缚,自己也该大展手脚,试试自己的医术长进如何?杵着长棍的本是黄山四友中的“云海”古一鹤,在四人之中年纪排老二,也属他心眼最多,诡计多端,所受之伤也是较轻。
几人之中都是他出谋划策,现在老大“落日长河”童定柱双耳受伤,对双方的谈话又听不到半个字,自己咿咿呀呀地乱叫反而添乱,还在有这个向来机杼二弟主持操心,定然放心,也不打搅他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鬼交涉,安心地坐着喝起茶来,而那个双目红肿血赤,暂时失明的是“石中火”雷羽,什么也看不见,先前的力气都还像用完了一样,现在直顾着哭爹喊娘,疼得呻吟不止,最小的就是“苍松手”林一峰,从进屋至今,年纪虽最小,腰身好似受到极重之创,难以直立,坐立不安。
“云海”古一鹤迫不及待地追问道:“小师父你到底放心不下?有话直说,我们竭尽全力遵照便是。”
李啸云镇定自如,有了前几日的初试身手之后,变得稳重不少,又道:“江湖之事我无暇过问,也不想介入其间,免得一生也脱不了干系,麻烦不断,无奈师父谆谆教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见死不救者不得超生,左右为难,哎!真是麻烦,我想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具躯体也是父精母血赐予的,你们的痛楚我也痛在心啊,所以还是甘冒良心的谴责,不惜师父的责骂,为你们排忧解难。”
“那废话少说,我大哥的病该如何医治?”古一鹤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跟李啸云闲扯,不忍心见兄弟们都痛不欲生而还要被一个后生小子捉弄一番,喝止住他的撇开避躲,蓄意给自己谈条件,提价码。
李啸云咂舌,知道这些所谓的江湖人修养颇浅,又大多是粗人,不喜废话,干咽一口唾沫,问道:“那你大哥以前是练什么功夫,到底成名绝学又以什么见长?”
古一鹤还来不及回答,站在旁边弯曲身子,苦苦支撑瘦弱残退痨病模样的林一峰实在忍不住痛苦,抢断说道:“我大哥都叫落日长河了,定是练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暗器,江湖上都赞他手法繁复,令人炫目多彩,就像日落长河,直耀人眼睛,但是真正厉害的还当属听风辩器的本事,一个真正的暗器名家,如只是眼疾手快,不过三流角色,所以”
李啸云听他细致入微的解释,自己总算明白,加上应变之活,灵动变幻之快,自己也打断话插口道:“所以被人用最不耻的手法折了你大哥的耳朵,让他再怎么厉害,没有耳朵的聪慧,也使不出数一数二的暗器手法?”
古一鹤也差点被这个柔弱俊俏的少年骇得惊犹未定,疑惑地直盯着他看,也在暗叹此人的举一反三,真知灼见,但最沉稳地他并不想表露出来,又隐忍回去,站在原地让受伤的脚好好放松。
林一峰赞不绝口道:“小师父果然是个奇才,一点便知,佩服,其实我们四人合称黄山四友,也是根据黄山的四境而得名,二哥古一鹤人赞‘云海金鹏’,以轻功负有盛名,能达轻飘似鸿,直上云霄,所以被歹人伤了腿脚;三哥‘石中火’雷羽,惯使一柄长剑,剑法快如电光火石,以快出奇,以奇制胜,可惜眼睛却被人伤了,再快的剑法没有了目标也是乱舞;我自己‘苍松手’以掌法、拳术见长,也可惜一双手掌只得拿来支撑腰痛,那还能腾出手来与人比较,我们兄弟四人定要让我们吃尽苦头之人加倍偿还,以血今日之辱。”说着,不免凄婉地流出眼泪。
“云海金鹏”古一鹤见林一峰如此没骨气,训斥起来:“老四,哭哭啼啼成何体统,事已至此何必怨怪他人只恨我们学艺不精,自负傲慢,才落至今日的地步,怨不得谁?”
“可这笔深仇大恨,奇耻大辱我们就算了么?二哥,难道畏惧此人,不敢报仇了吗?”林一峰与古一鹤争论此事,看来对方致他们兄弟伤残至这般田地的是同一人所为,倒令李啸云也好奇这个能让四人生平最得意的武功都惨败重伤的高人是谁?古一鹤和解与兄弟之间的误会,不想再为此事伤了感情,回应道:“我们现在这副模样,痊愈还未知,恐怕治好也回不到以往的全力,暂且休养生息,待日后再作打算。”林一峰可不是那种冲动不经考虑的莽汉,也觉二哥说得极有道理,隐忍负气地咽不下一时的恶气,站到一旁看古一鹤是怎么让面前这个小神童答应医治自己的。李啸云不敢再擅做主张为他人看病,这关系不只是师父的名声威望,还是考验一名大夫的修为,治好了莫大欢喜,万事大吉,可因自己的失误给病者带来悔不当初的病危命颓,一辈子也会活在阴影之下的,师父前些日刚循循善诱完,自己还不痛改前非,故技重施,更给他添乱,甚至颜面抹黑。
自己可不想在为此节上有丝毫的差错,婉言回绝,推辞道:“只是我医术浅薄,各位又是成名英雄,我不敢拿各位的性命开玩笑,还是等师父他老人家回来吧,到时候真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还轮不到我在此献丑丢人。”古一鹤刚见兄弟几人的病情有所期望,事情在向有利自己的一边发展,大费口舌一阵之后,这个小神医有点起色,万未料到居然临阵变节,突然改口,实在令自己纳闷,惊愕。眉头深锁地问道:“小师父是乎有所顾忌,难道自己不敢相信自己的能力还是怕你师父责罚?”
李啸云年少气盛,被他一语中的,脸色涨得通红,惭愧不如,在他人的言语相激之下,自己也并未逞能好强,反而清醒地一执立场,并无动摇,笑道:“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否则,自毁清誉名节事小,累了各位性命事大。”
连林一峰在旁听着大显着急,着实令自己想不通为何这个小神医会突然改口拒绝,身受重伤,希望就在眼前,反倒弄得僵持起来,急躁起来道:“小师父,我们可是真心实意前来求医,不念我们一路奔波这份辛苦,也得体谅我们此时的如坐针毡的感受吧?”
李啸云执意不绝,仍不为悱恻心动地道:“你们暂且多忍耐一会儿,我想师父他即刻就回来了,急也无用。”
古一鹤哀声怨叹,能明白此人的顾虑,只好闭口沉心下来等待。
林一峰却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四人之中倒不是他脾气最为急躁,可兄弟四人,心意相通,遭遇如出一辙,就算先搭救其余三人也总比心急如焚地等下去好上许多倍,每人都重伤在身,要是拖延下去,说不得就算治好了功力也恢复不到以往的巅峰之时,戳指恐吓道:“臭小子,我们好言拜访,居然不识抬举,告诉你,我姓林的也不惧死,可要是接二连三受气,实在令我怒不可遏,再拖下去,本就虚弱,精疲力尽,恐怕迟则生变,我也不跟你讲究什么江湖规矩,要是再不出手解救我们兄弟,我就一把火烧了你这个破医庐。”
李啸云无动于衷,神情自如地站在门外,对他的危言恐吓不以为然,古一鹤见四弟如此沉不住气,也不念及什么自己的身份,作为这个少年的长辈,竟然有失体面地威胁起来,立马喝止道:“四弟,休要冲动,对这位小师父客气点。”
“二哥,你就知道忍让,被那个混蛋欺辱也就罢了,谁叫我们四人联手也伤不到他丝毫,可不惜重病在身前来求医却还让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小子看轻贬低,这口恶气实在难咽。”
林一峰将逼忍在心口多时的话吐出来,还是更加气甚。
李啸云可不是什么胆小怕事的小子,对他的话反倒一点不惧,挺胸自傲,不闻不理地站在原处,看他们还能忍耐到什么地步,真是修为自负之人也决计不会难为自己的。古一鹤也顾念他的感受,好心温和相劝道:“这位小师父所说的也不无道理,依你的脾气,要是他治的不彻底,或是旧伤未愈又添新病,那还不得杀了这位小师父一泄其恨?他有所考虑也是为我们兄弟着想,你何必一点情面不讲?”
“我不讲情面,二哥你本末倒置了吧?要是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真以为我们这些人恃强凌弱,虽是伤病在身,可对付他绰绰有余。”林一峰强忍着自己腰间上的伤痛,恶狠狠地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李啸云,双手摩拳擦掌着,似乎就要发难,连在旁一直端坐的童定柱也大声问道:“四弟,怎么回事?这小子也欺辱我们兄弟四人现在是病猫不成?”说完啪一声拍案而起,随时动手,他一直憋着怒火,没地方发泄,加上又不知双方交谈些什么内容,唯有干着急,现在见老四居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看来定是有架要打了,正合他的脾气和胃口。
“石中火”双目暂时看不见,一直也听着双方的对话,这要是打起来,依李啸云的口吻,自己人称他一声小师父,有此可以判定对方不过只是一个少年而已,但要是对方欺辱到自己头上来了,别说对方是千军万马也好,是只身一人也好,无论老弱妇孺,还是童叟女流都一视同仁,一并而上。古一鹤眼看着情形就要一触即发,到时真难以收场,中气十足地大喝道:“够了,你们都是江湖之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欺负一个小孩,也不怕被人耻笑?”
林一峰被摄震住,一脸难堪,雷羽和童定柱二人相互扶持着,一个听不见,一个看不到,此时英雄末路,只得唇齿相依着,雷羽拉住大哥,生怕他一时冲动真把事情闹大了于己不利。
李啸云镇定自若,心想面前这些人杀自己轻而易举,易如反掌,可是毕竟在江湖之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干出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欲盖弥彰,任由他们如何软硬兼施,自己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