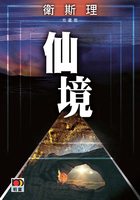曾姓女,明总——郑黎明,兄公司——程雄,这几个欲盖弥彰的名字显而易见并不是试图掩盖什么,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曾可心忽然想到了这两天办公室的气氛有些诡异,他们看自己的目光都有些异样。常常是几个人议论得正起劲,她一走近,大家都四散离去。有几次,他们趴在电脑上,看到她,就急急忙忙把电脑关了。她以为这些人在玩游戏,因为没有抓到把柄,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刘虻提醒过她,要先学会忍耐。她却没有想到,原来他们都在看这样一个帖子。曾可心久久地呆坐着,甚至连午饭也忘了吃。她从来没有遭遇到这样令她耻辱的事情。就像被人狠狠扇了一记耳光,甚至是比这种羞辱更为恶毒的行径。你不知道这样的羞辱从何而来,你只能猜测一个卑劣的无耻之辈躲在阴暗处,发出鬼魅般的笑声。人言可畏。可畏的不是语言,而是那些无处不在的陷阱。这些小说才有的情节,怎么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最让她难堪的是,她不知道以后该怎样面对郑黎明。说心里话,对于郑黎明,她有着一种很亲切的如父辈样的感觉,这种感触她曾经在QQ上和行者说过,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行者就是刘虻。
天外来客:素昧平生的两个人,或是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或是隔着几千里的地域,机缘巧合,在某一刻某个地方,居然碰上了,一见如故,义气相投,这种不期而遇是不是今生来奔赴前世的邀约?
行者:呵呵,你不会是爱上某个人了吧?
天外来客:这不是你理解的那种爱,在他身上,我能感受到一种父亲似的疼惜。说心里话,我很珍惜。你相信世间有这样纯净的感情吗?
行者:认识你之前,我不信。现在,我信。
后来,他们知道彼此真实的身份后,再也没有探究过这个问题,甚至谁也没提过这个问题。只是,每次陷入惆怅与郁闷中,曾可心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郑黎明,想起他的办公室,想起那浓郁的茶香,那种味道和父亲书房里的味道一模一样。曾可心忽然觉得这个城市真的太小太小了,或者,这原本就不是她的城市,抑或,她这个过客该回家了?
一直捱到快上班时,曾可心发现自己的手脚冰冷,心好像已经不会跳动了。
她很镇定地站起来,给郑黎明发了个信息:“郑总,我身体不适,请假半天。”而后,告诉办公室负责接待的女孩子,自己身体不舒服,有事儿找李志文或直接请示郑总。坐在出租车上,她越发感到冷,甚至不住地哆嗦。司机惊讶地说:“姑娘,你不是发烧吧?怎么还打摆子?”曾可心闭着眼睛没吱声,她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也不想听任何人说话。司机看她一脸倦容,也就没有继续说下去。回到住处,曾可心把自己丢在床上,手机在路上已经没电了,她没有充电,她累了,想好好睡一觉。
大脑好像已经睡着了,可曾可心的梦却乱七八糟,没有一刻停歇。她梦见一只非人非兽的怪物在追她,她拼命跑,拼命喊,可是,除了一望无际的茫茫沙漠,她看不到丝毫有生命迹象的物体……
家门就在这时被敲开了。刘虻出现在面前时,曾可心强撑的镇定一下就瓦解了,她哭得很委屈,也哭得很痛快,这种哭泣在刘虻看来,好像还有压抑的怨怼,他对曾可心的疏忽,还有袁满,他一直在回避,现在他还要躲到哪儿去?
刘虻决定搬出去。他拐弯抹角和刚出院的袁满说了搬家的意思:“我和可心的事儿你也知道,她最近的状态很不好,我想我应该照顾她。”袁满起先没说话,顿了一会儿,她忽然嘴一撇:“不就是嫌姐姐碍眼嘛。姐姐搬出去,这儿留给你们这对小鸳鸯乐呵吧。”刘虻觉得自己很不地道,想和她解释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还是你住这儿,我一个大男人好找地方。”袁满手一挥:“得了,留着你的甜言蜜语哄你的小辣椒去吧。”袁满说到做到,两天后她就搬走了。刘虻问她地址,她笑着说:“干吗?不放心,还是别有企图?”她调笑的样子让刘虻轻松下来,他坏笑着问:“你这么为我着想,不是爱上我了吧?”袁满狠狠啐了他一口:“呸!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小心你家小辣椒收拾你!”
下午,刘虻就拿着钥匙找到曾可心:“以后咱俩住一起。有我,谁也伤害不到你。”曾可心哭着倒在他怀里。刘虻亲吻着她,呢喃着被无数人重复了无数遍的情话。曾可心搬进了袁满住过的房间,她把墙壁粉刷成淡淡的粉色,床单也是淡淡的粉色,推开门,就看到一个胖乎乎的熊仔憨厚的笑容。曾可心坚持和刘虻分摊所有的费用:“我不是个随便的人,你也不是吧?所以,我俩要定个规矩,除非结婚那一天,否则你——”她的脸忽然涨得通红。刘虻恶作剧地问:“我怎么了?”
曾可心低着头,好一阵儿才说:“不能和我有过分的关系。”
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
刘虻居然与曾可心一道来上班,他毫不回避别人探究的目光,殷勤地对曾可心嘘寒问暖,中午只要没饭局,他一定会与曾可心一起吃饭。偶尔也会带着曾可心去附近的饭店点几个可口的小菜。没过几天,天宇上上下下都知道刘虻和曾可心在谈恋爱。
最让曾可心意外的是,久不露面的高天居然给她打电话,约她吃饭。她正想寻个借口回绝他,话筒那头的高天似乎揣测到了曾可心的心理:“我不单单是请你吃饭,还有一些事,想请你帮忙。”高天的话说得很诚恳。刘虻晚上去赴约,程雄为袁满出院特意设宴。曾可心想了想,答应了高天的约请。
几个月不见,高天比以前瘦了一些。但他的精神很饱满,尤其是那双眼睛,炯炯有神,似乎有源源不息的旺盛的火焰。“主要是老出门,换了谁也受不了。好在我还不算老,能扛得住。”高天玩笑之间,做了一个很绅士的手势,一个年轻的服务生走过来。高天微笑着示意曾可心点餐,曾可心摇摇头:“客随主便,我可不会点菜。”
高天便不再客气,开始点一些曾可心听说过但总也记不住的食物。
虽然以前曾可心很在意他是否在利用自己,现在,二人坐在装潢精美有几分罗曼蒂克的西餐厅里,曾可心发现,自己已经心静如水。耳边流淌着理查德·克莱德曼弹奏的《思乡曲》,淡淡的、闲适的柔婉,却又有几分如雾轻笼心间的怅然。曾可心不喜欢咖啡的苦涩,即使放多少方糖,还是觉得嘴里有长久的苦涩。此刻,曾可心慢慢品尝着一种叫卡布其诺的咖啡,闻上去有牛奶的浓香。“这种咖啡,越品越有滋味,你试试吧。”高天说,所有的饮品里,他最钟情的不是酒,而是咖啡。
浓香,继而有咖啡的苦涩,或是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在舌尖慢慢渗透,那种滋味,让曾可心久久回味。她一时竟忘了说话。“怎么样?”高天饶有兴致地问道。
曾可心忍不住赞道:“果然是味道独特,你真有品位!”“很多人说卡布奇诺象征着爱情,不过,在我看来,它更像人生,浓香苦涩复杂的味道。”高天的声音浑厚低沉,餐厅里《秋日的私语》清澈流淌,卡布奇诺的味道渗透在曾可心的四周,她在氤氲的香气里渐渐有些慵懒的迷醉。她忽然发现,原来,美味是可以拿来享受的。
“想过换个地方吗?”高天小心翼翼地问。曾可心摇摇头,她不习惯用刀叉,旁若无人全力对付着九分熟的牛排,嘴里还嘟囔着:“左刀右叉还是左叉右刀,哪头也不顺手,这头牛看起来也是冤死的。”高天被她的话逗乐了:“需要我帮忙吗?”“要是退化到吃个牛排也得找人帮忙的话,我这个所谓的代理经理以后还怎么镇住下属啊?”曾可心有些恶作剧似的用力切割着不听话的牛排,而后把一大块都塞进嘴里。“大块小块,吃到肚里都是牛肉。”每次,和曾可心在一起,高天总觉得空气都是活色生香的。他到了纵横以后,曹大富和他聊过好几次,他也听出了曹大富的意思,很想把曾可心挖到纵横。虽然高天与曾可心交往并不多,他却自认为很了解曾可心的脾性。她是不可能轻易离开天宇的。她在天宇颇受重用,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特别是自己辞职后,曾可心居然被任命为代理经理,全权负责人力资源部工作。在没有把握之前,高天不想与曾可心过多接触。他了解程雄的为人,要是获知二人来往,曾可心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他跳槽到纵横,毕竟是借助或者可以说是利用了曾可心的这层关系,而小五也借机给他说了不少好话。曹大富正值用人之际,两人后来也吃过几次饭,每次他都能让曹大富看到新的希望。没用多久,曹大富就盛情邀请他出任纵横传媒总经理。
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本地业务没有突破性发展之前,他把目光转向了周边地区,这一招果然奏效,公司业务明显上涨,曹大富喜得几乎每次都会亲切地说:“高天,你是的我福星啊。”前些天,高天看到论坛里关于曾可心的帖子,对此他压根不相信,想到曾可心的处境,他动了游说曾可心跳槽的念头。
“我现在很缺人手,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你不适合搞人事工作,你太单纯,没有防人之心,更适合做技术类的活儿,比如策划。”高天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图,曾可心答复得毫无商量余地。“我不能去,我现在走了,不是正好落人话柄,说我吃里扒外,不怀好意。”曾可心说这话时,刘虻那天劝她的话又在她耳边回响:“你想过没有,这里面有没有其他文章?这件事是针对你的,还是要对付郑总呢?你要是就这么离开,就会被人看笑话,也就真的让躲在幕后的小人得逞了。
还有,你不能去找老小子,他即使可以开会为你们辟谣,你也必须清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被人议论得更起劲。这就像是小丑,看客越多,表演得越卖力。所以,你必须要装得若无其事,人正不怕影子斜,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我相信,有些事,郑总会用他的办法解决的。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等着看结果。记住,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
送曾可心回家时,高天诚恳地说:“可心,很抱歉,我当初利用了你。”曾可心笑了,“这世界没有那么多坏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能理解。再说,你和嫂子不也帮过我嘛。咱们这叫互相成就。”望着曾可心的背影,高天若有所思,他的心,好像在那一刻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