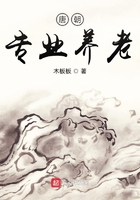与后世的越富有越低调不同的是,来到这个时空,秦萧还从未见过比对方更显富贵,或者再确切的说,是更显气派之人。
当然,在后世的着装中,常人很难一眼从对方的衣服面料及剪裁上做出细分判断。
而在信息发达的后世,那些商业巨子亦无需在衣着上下很大功夫,哪怕只是随意的穿搭简单的拖鞋、T恤,旁人也能很轻易的知道他是哪个首富,又或名人。
可这个时代则不尽相同,他们需要在衣食住行上有所体现,才能彰显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
他们需要旁人一眼认出自己,可总不能见人就介绍“我是某某首富名人”。
至于那些什么故意低调的鬼话,不过是些骗人的把戏,如果全世界都几乎认识你,那样做无非是标榜另一种特立独行,掀起另一场舆论风暴罢了。
但有一点世人绝对没有说错,那就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或许在后世,普通衣服与名牌的剪裁和布料已经差距很小,但在这个更多人犹自挣扎于保暖的时代,一套剪裁得体的精美华服绝对会让人立刻变得鹤立鸡群。
就如当初采石场的萧,一块破麻布围住下半身,被人鄙视。
又如现在的秦萧,捡的是封不寒给予的衣服,有谁认识?
再如眼前的罗荣,光是头顶高冠上镶嵌的那颗明珠,在这个刚掌灯不久的厅内闪熠生辉,就让人知道肯定价值不菲。
他年约四十,正值一个男人最辉煌的阶段,身上的锦袍剪裁合体,束腰的玉带松紧适度,奢华贵气却又暗含内敛,全无半分后世暴发户的气质,反将他保养得极好的身材衬托到极致,亦将他的威严展露无疑。
他踞坐首席,两名虎背熊腰的武士分列左右,气势逼人,胆小者光是看到这等阵势,恐怕早已被无形的威压吓得胆战心寒。
范嫣然盈盈跪下叩礼时,秦萧忽然有点失了方寸。
这倒不是他被对方的气势吓到,对他来说,罗荣并非那个能一锤定音将他命运主宰之人,他又何必畏惧对方?
说起来,他似乎还更害怕范嫣然一些。
毕竟如果将她惹恼,那可是老天爷都救不了的存在。
而此刻他之所以感到慌乱,不过是因为本以为是兴冲冲的进来对质,可自家主君却盈盈拜倒,而且执的是晚辈之礼。
那自己呢?作为府中的奴隶,又该怎么行礼?
他在脑中迅速回想,似乎自从来到这个时空,还就对范嫣然行过跪拜大礼,她是自己的主人,那是再无奈也不得不为之的当世礼仪,可眼前之人……
就不用了吧?
当一个人习惯站立,就不会轻易跪倒,何况后世而来的他?
秦萧拿眼偷瞥向另一侧的封不寒,见他只是抬手作揖,当下也立刻照办的胡乱行了一礼,懒得再去琢磨对方是门客,而自己是奴隶的区别。
再则稍后少不得就要撕破脸皮,这些旁枝末节又还有什么好计较?
而自打三人甫一踏入大厅,他就感倒罗荣虽然面色纹丝不动,可身形却稍稍变正,凌厉的眼神朝他们轻扫,似乎更在自己身上停留片刻。
当然感受得最热切的,还是罗林那喷火的目光。
只等范嫣然落座,罗荣没有任何多余寒暄的直入正题,淡淡道:“嫣然回来了,此行可还算顺利?”
“回舅父,途中虽然遇到些许波折,不过尚算顺利。”范嫣然回答得不紧不慢,不过秦萧还是从她的话中察觉出一丝心悸的异样。
这也不难理解,当一个人长期被某人压制,就算下定决心反抗,总是难免条件反射的依旧会有些忐忑。
罗荣点了点头,似乎陷入思索的静了片刻,开口道:“我此次前来雍都,主要是处理一些重要商事,至于府内前不久那事,你表兄曾经修书告知于我,可却语焉不详,昨日我前来府中,亦曾召范管事几人加以询问,此事……确是林儿不对……”
听到这话,不知秦萧,包括范嫣然等人尽皆愕然。
他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
同一时间,恭立一侧却暗暗眼睛冒火的罗林亦是脸色一怔,情急之下脱口一声“父亲”,就要进言。
“孽畜!”罗荣暴喝一声,举手示意他闭嘴,本就含威不怒的神情此刻更是盛气凌人,细长的眼睛瞪了开来,射出两道摄人的锋芒,却又并未转向罗林,只是落在下首范嫣然旁边垂手恭立的秦萧身上,将他死死罩住,把秦萧看了个内心委屈无限。
你只管教训你的儿子,却死死盯着我干嘛?!
就在他不满的腹诽之际,罗荣口中迸出的话语似乎也意有所指:“逆子!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府内的所作所为?范管事等人将你的行为全说与我听,当初,我遣你来都城,乃是看嫣然年幼,希望你身为表兄能够多多帮衬,可你呢?”
怒哼一声,“你之所以有今日,不过是咎由自取!”
罗林被父亲的一番怒斥弄得哑口无言,本来满腹的理直气壮被杂七杂八的其他事情掺杂进来,顿时心虚的说不出话。
然而秦萧却从这通看似疾言厉色的斥责中听出别样的味道。
因为这番话里,对方只说出了罗林之所以有今日结果的活该,却并没有关于其行为的谴责。
相反话里话外甚至还透着一股子对自己的指桑骂槐,让他忍不住的一顿暗骂。
教训完自己不争气的儿子,罗荣的怒火似乎平息了些,容色放缓道:“嫣然,舅父当初让林儿来都城,一则是希望他能对你多加看顾,二则希望他能对府内事务有所帮衬,没想到这逆子竟如此胡作非为……唉,真是……”
说着又是一副愤怒兼具惭愧的复杂模样。
范嫣然见状连忙出声劝道:“舅父莫再气恼,其实表兄在府内这些年,对甥女及府内事务亦算照顾得面面俱到,甥女心中只有感激,又怎会因些许小事而有所怨言?只是,只是今次之事与往常不同,若是没个交代,嫣然担心府内恐怕人心浮动,才不得已而为之。”
“舅父知道,舅父知道。”罗荣伤感的点头表示理解,接着一脸痛心道:“没有照顾好你,反而将府内闹得乱成一团,我只是觉得愧对妹妹妹婿罢了!唉……”
范嫣然亦是眼眶一红,“舅父此话从何谈起,若是先父母在天有灵,亦只会对舅父的无私照拂深为欣慰感激……”
说到后来更是哽咽难言,两人一时相对追思,默然无语。
唉!成功之人,总是天生的演员!秦萧听着这种言不由衷的话语暗生感慨,然后再瞥一眼正怒目瞪着自己的罗林,又忍不住心忖:便似他,就永远都无法成功!
两人默对片刻,罗荣率先从情绪里抽身而出,蔼声道:“尚幸你如今亦算平安长大,他日舅父去到黄泉,也不至于完全没脸面对妹婿,以后府内大小事务,就全部交还由你来打理吧!至于林儿,哼……”
“舅父!”范嫣然急声打断,惶恐道:“舅父,甥女虽然长大成人,可却甚少接触府内事务,恐怕……恐怕难以胜任,甥女心想,不如还是先由舅父再照料一段时日,如何?”
罗荣缓缓一叹,疲态尽显道:“我这身体如今亦是大不如前,光是安定那些琐碎杂事,舅父便感力不从心,又谈何两者兼顾?无妨,此次邙山之事你不就处理得很好吗,舅父相信你。”
说着一顿,再续道:“至于以后若遇不懂再或不决之事,尽管来信询问舅父便是,舅父虽然老而无用,总还有点世面可谈。”
话已至此,范嫣然表达了对舅父身体的关切之后,也就半推半就的“无奈”应承下来。
而解决了头等大事,罗荣一时也陷入无话。
此时厅外传来轻微却纷乱的嘈杂之声,借着昏暗的廊灯,隐约能看到三三两两的衣衫褴褛之人影穿过走廊,正朝其他院落行去。
罗荣微不可察的皱了皱眉。
范嫣然见微知著,解释道:“他们是府内的门人和邙山的臣妾,当时去到邙山之后,甥女听到消息说有数队马贼或许会袭击车队,而甥女所带人马太少,便集合了采石场所有人一同护送,今日抵达城内时天色太晚,城门关闭,甥女便让众人歇在府内。”
罗荣了然的微微颔首,没有继续深问。
毕竟无论如何,范嫣然此刻已是范府实至名归的一家之主,所有安排都是她的权力,让人无权过多干涉。
总不能要他刚讲出那样的话,现在又来横加干涉,打自己的脸吧?
而说完这番话后,厅内再次陷入沉默。
默然旁观的秦萧感受着这种气氛,忽然心生一种悲哀,在这样的一个亲戚网中,似乎除了利益,竟变得无话可谈。
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过多感慨,矛头的焦点已经向他直指而来——
罗荣陷入深思般的失神片刻,眼中复又聚起犀利的光芒投到他的身上,忽然道:“你便是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