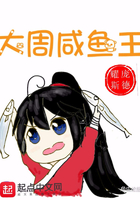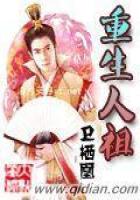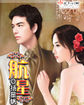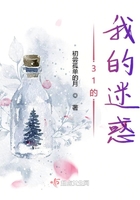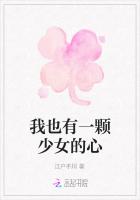野史:曾国藩好相术
曾国藩喜欢钻研相术,有人向他请教看人的方法,他念了一套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他又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
曾侍郎主持严打
咸丰三年(1853)的上半年,太平军从金陵、扬州一线把战火烧到了黄河以北。金陵的太平军又向西线回攻,再次攻克安徽省会安庆,包围了江西的省会南昌。
官军在各条战线都陷入全面防守的被动态势。金陵—扬州—镇江战区,由满人文官琦善和汉人老将向荣看守,攻击毫无进展,还放走了一批又一批敌军;黄河以北,由托明阿、西凌阿、胜保等一批满人将领率领旗营劲旅阻截,与林凤祥的北伐军相持,京城如临大敌,调集重兵拱卫,进入了一级戒备;在安徽,官军没有一支得力的部队阻击太平军的攻击;在南昌,全靠着江忠源为数不多的楚勇在极力支撑,才牵制住了赖汉英的西进部队。
咸丰皇帝起用了几乎所有的前朝重臣,但他一次又一次失望,只能把扭转战局的希望寄托于弃文从武的胜保和从基层崛起的江忠源身上。他希望江淮之间、河洛之畔涌现出更多的“北胜南江”,为他保住已经岌岌可危的大清江山。谁也不能指责这位皇帝未能摆脱自己的局限性,他已经尽力地不断解放思想,大力推进用人制度的改革,呼吁重视基层人才。
但是北胜南江的提法明显带有褒满贬汉的色彩。把胜保排在江忠源之前,本身就是为了抬举满人。其实胜保岂能跟江忠源相提并论?江家军战功卓著,从广西、湖南、湖北打到江西,身经数百战,作战顽强,经验丰富,见识不凡,是胜保望尘莫及的。
在咸丰眼里,能有胜保这样的满人官员挺身而出捍卫帝国的利益,已经是够不容易的事情了。尽管胜保投入战争不过几个月,也未打几个胜仗,从金陵赶到河南的怀庆,拖拖拉拉走了一个多月。但即便是这样一名战将,在满人臣子中也显得弥足珍贵。
而且,到这时为止,江忠源脱颖而出只被视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并没有令朝野对更多的湖南人刮目相看。没有人注意到,湖南一地正在涌现大批江忠源式的人才。江忠源是一个先驱,一个典型,一个榜样,正在带动湖南的读书人投身于这场战争。咸丰和所有当局者都没有料到,尽管许多省份都在朝廷号召下大办团练,但真正足以捍卫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只是在湖南一省酝酿形成。这个从前默默无闻的江南省份,形成了一个必将深远影响后世中国的人才格局。湖湘人才从此崛起,将改变中国甚至世界的命运。
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找不到任何的预言。只有野史传说,李星沅曾经寄望于曾国藩平定粤逆。另外有一个名叫朱骏声的江苏长洲人,也预见到曾国藩将为本朝平定动乱,带来太平。曾国藩奉诏在长沙帮办团练时,朱骏声卧病安徽黟县山中,听到这个消息,大喜道:“太平有望了!”
别人问:“您怎么知道?”
朱骏声说:“前些年,我拿着自己的著作,要呈送皇上御览,就是此公带领引见。常人眼斜颧高,此公却两颊平直,髭髯甚多,直连颌下,披覆于宽博之胸,益增威严。我看他办一件平常的小事都慎重周详,所以相信他能办大事。”
这些说法,即便有几分真实性,恐怕也难逃事后诸葛亮的窠臼。
湘军的崛起不是在一声号令下发生的事件,它经历了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经历了许多偶然性的碰撞与糅合。所有湘军大佬都在咸丰登基前后逐步开始注重军武,但他们都未策划过一支新式的军队。可是咸丰三年的国家大局,以及咸丰皇帝求贤若渴的人事路线,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成为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于是湖南民间的武装力量开始呈现出爆发之势,逐步凝聚成清末最强劲的一股军事伟力。
由于湖南的不少书生热衷于团练事业,该省民间军伍的形成有了不错的基础,但还需要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曾国藩的出山。湘军的崛起绝非发端于曾国藩,也绝非由他一人之力而生成,但跟他出任帮办团练大臣的确有直接的关系。湖南的乡勇原来各自为阵,由于曾国藩的出山,他们才有可能脱离本乡本土,整合在统一的旗号、统一的指挥机构和杰出的指挥员之下,集结力量,进行大规模和大范围的作战。
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三年所做的事情,对于湘军的诞生举足轻重。
曾国藩年初来到长沙任事以后,和代理湖广总督张亮基、代理湖南巡抚潘铎一起于二月三日奉到上谕:
封疆大吏翦除百恶,即可保卫善良,着该署督抚等认真查办,并着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体察地方情形,应如何设法团练以资保卫之处,悉心妥筹办理。
虽然咸丰只给了曾国藩一个辅助的角色,但对于团练乡勇保卫全省的责任,曾国藩有心一肩挑任。这位团练大臣自从决定出山以后,心中就打好了算盘。既然在守孝期间奉旨办差,就要大干一场,如果只是玩一玩地方的团练,那就太没意思了。
曾国藩要办大事,就要把手伸向湖南的官场,控制一些要害的职能部门。他盘算着如何借助皇上的天威来为自己打开局面。奉到上述圣旨九天以后,他就上奏了《严办土匪,以靖地方》一折。他说湖南存在各种各样的土匪,但近年来当局隐瞒不报,任其猖獗,只有动用严刑峻法,才能把大规模的动乱制止在萌芽状态。
这位团练大臣说,太平军在湖南走了一遭,这里的会党多半都随太平军去了,但仍然有串子会、红黑会、边钱会和香会聚集闹事。湖南的崇山峻岭,有利于会党的孕育。东南部的衡州、郴州和桂阳州,南部的永州,西南部的宝庆和靖州,到处隐藏着会党。地方官府知道会党的势力无法遏止,都不想自己的辖地里发生祸患,千方百计地加以遮掩,苟且偷安,留下了几十年应杀而没有杀的人,听任他们横行霸道。现在乡下的无赖刁民气焰高涨,他们见有人命在身的强盗首犯常常逍遥法外,又见太平军势力强盛,朝廷没法制止,便以为法律只是一纸空文,官员也只是摆设,对他们不起作用。如果不用高压手段,就无法打掉他们嚣张的气焰。
曾国藩相信皇帝一定赞成他的这个分析,更会赞赏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他告诉咸丰,他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严打,铲除强暴势力,给良民以安生之日。这话听起来有些像申韩法家治国的主张,似乎不应该出自一个理学家之口。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他会借重不同的理论观点。现在他把仁恕放在一边,鼓吹治乱世须用重典。这种做法体现他实践学问的博大,不会吊死于某一种学术之上。同时在并非贬义的基础上,也可以说他是某种程度上的机会主义者,体现了湖南人特有的变通精神:灵泛。
曾国藩所说的严打,就是从重从快打击犯罪活动。从重,是靠严厉的刑罚对罪犯形成威慑;从快,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手,把罪犯打蒙,但不免简化程序,错判罪案。这跟儒家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但曾国藩此时急功近利,已把儒学修养抛到脑后,连身败名裂都在所不惜。他说,他虽然会由于严厉的司法得到残忍严酷的名声,但他也认了。当今的急务,要使全省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清除大小各路会党,就可以指望涤荡一切污浊。对于那些曾经有过抢掠、拜会、结盟行为的人,要当即正法。只要清除了内奸,太平军从外省再次打来,也无法有什么作为了。
咸丰看了曾国藩的奏折,心绪颇为激动。这位大臣讲出了皇帝心里的话,咸丰完全支持他推行严打,在他的奏疏上用朱笔批道:
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咸丰的朱批无异于赐给曾国藩一把尚方宝剑,可以号令湖南的大小官员。他在长沙设立自己的行辕,不叫帮办团练衙门,而是叫湖南审案局,一听名字,就像一个面向全省的专政机构。这个机构设在鱼塘街,紧挨着巡抚衙门,有了跟巡抚平起平坐的味道。曾国藩明确了审案局的功能:专管治安案件,凡有加入会党、抢劫及其他严重侵害治安行为的嫌犯,都由审案局审理。如此一来,曾国藩成功地操控了湖南的司法管理。
曾国藩现在有了两种面目,在接近绅士和书生时,他和蔼儒雅,令人觉得容易亲近,一脸优美的须髯,有助于缓解对方的不安;作为审案局的头子,他表情稳重,举止威严,看人时瞪着一双三角眼,眼光凝注对方,看得人毛骨悚然。但无论在何种场合,分手之后,他会记下对方的优点和缺陷,准确无误,这是他颇为得意的识人方术。
曾国藩委任了审判员,拿获犯人,立即严讯。他借用巡抚的令旗,掌握了死刑判决权,可以将犯人立即处死。有些犯人在杖击之下当场死亡,他也无动于衷。他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把自己当成了法家的代言人:既然是为民除害,他就问心无愧,要用重法以锄强暴。你要说他冷酷无情,他也敢担负尚武不仁的名声。于是继江忠源戴上“江屠夫”的帽子之后,曾国藩也有了“曾剃头”的绰号。
湖南的土匪成分复杂。曾国藩将土匪区分种类,有会匪、教匪、盗匪及寻常痞匪。有了区分,就能根据罪情分别处罚。
在他执掌审案局的初期,他要对付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主要不是盗匪,而是残留在湖南境内的散兵游勇。太平军进攻长沙时,官军调集各省兵勇几万人,后来主力由向荣率领追击太平军,留在湖南的散兵游勇十人一队,百人一群,出没在长沙附近的村墟,或者打着兵差的旗号,在湘江上下游封存船只,敲诈勒索。商旅畏惮,不敢行走,物流几乎断绝。官军逮捕了三名强封民船的川兵,曾国藩下令立即斩决,割下首级,挂在江边示众。从此游兵敛迹,风帆畅行无阻。
审案局采用严打的方式,从重从快审判罪犯,不再遵循正常的办案程序。有些嫌疑人已被州县立案,尚未进入审讯环节,审案局为了加快速度,立即把他们提来,讯出供词,就立即正法。
咸丰初年的严峻局势,使一些官员深化了对社会的认识。他们指出,官场腐败,导致民不聊生,盗抢成风;而软弱的官员又对治安混乱放任不管,甚至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总之,社会不得安宁的总根子,都在官场的弊端。咸丰皇帝头脑清醒,赞同这个判断。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就曾在奏疏中强调这个问题。如今皇上授权他负责社会治安,他决定两手都硬,一手惩治“恶民”,一手查办贪腐的官吏,尤其不放过那些镇压土匪不力的官员。
他动员全省各级官员积极整顿社会治安,只要接到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举报,马上严参。他的行馆成了审案的公堂。三个月内,他杀了五十多人。这件事震动了湖南官场,激起了文官和司法官员的不满。这些人叫苦不迭,却又害怕曾大人拿自己开刀,不敢不打起精神料理公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