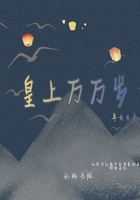且说崇寒玉含怒带愁转身去了剑冢,自是寻不见惜泪的。却在剑冢寻见了越长涛——寒玉不认识长涛,长涛却听惜泪说过寒玉,因此见了寒玉,便猜出来了,立即引她去药池找惜泪。
兆惜泪正与宋玉京说话,说起兆灼的毒,绝无活路。不免叹了一阵,复又说起云泽的伤。那宋玉京穿一袭青色轻袍,长身玉立,干净白皙的脸,一双亮目,黑眸滴溜溜一转,透着一股子精明劲儿。细而挺鼻梁,长长淡淡的两条眉毛,厚厚双唇,深长人中,他的前额宽大却挺平,下巴稍宽成个略方的脸,眼下宋大夫神情严肃,只说道:“暂时易控,余毒难解。仇门主那么了得的神功,却也年年发作。这回陆师兄反噬这般严重,内力怕是大损难复了。以后再上进,怕是武功上头终难大成了。”
寒玉站在长涛身侧,轻轻击掌冷笑道:“这才好呢!姓陆的这贼,我定有一日可杀了他的!”
惜泪循声看过去,见了寒玉,知她素服前来,是寻仇的。阿泪上前拉了她右臂,劝道:“妹妹!小田的事,我也痛心疾首!虽是云泽他承认了,可我看这事……”
“哈…哥!我知道了!”寒玉按了腰间剑,恨声道:“你早不是崇家人了!田遇时也不是你什么人了!我…我也不是你妹妹了!”
兆惜泪也是无奈,江湖纷争了无休止,今日是小田,明日也可能是自己,便递了块杏色手巾给妹妹,柔声细语地劝道:“妹妹!你怎么不是我妹妹了?可是玉儿,门中事情复杂,乱斗之下,小田也有可能会刺死云泽呀。”
哪知崇寒玉听了这一句,愈加愤怒,怒目扫了阿泪一眼道:“我知道,你们本是一丘之貉,没什么道理可讲!我今日…便与你击掌,断了这兄妹之情!而后,我只在竹城专等那仇问,只等他给我个说法。”
“玉妹妹要说法,不必等师父,我可以给你!”
众人听得是云泽的声音,转眸去看,只见陆云泽一袭淡蓝轻袍,在药池温泉的水边立着,看那气质,却正如晨间朝露,晚来残云,虽清俊隽秀但恐不长久。
云泽道:“玉妹妹,当年你哥与你父,接了岩香国主的无字阴符密诏,说明了要杀我,可他们却宁可自己获罪,也要将我放了。这份恩情,我永世难忘!然,贤妹夫他乃太师尊的徒弟,以目前门中的局势,我也只能这样做了。…贤妹,虽然到今天为止,我也不确定小田是不是真的死于我的剑下,或是当时另有什么人杀害了小田?这一切我都没有把握…可是玉妹妹!小田的事我脱不了关系,贤妹若是一心想报仇,等师傅回来,你就一剑刺死了我吧…云泽也没有怨言…我只想,只想等师父回来再见他一面,当面谢过他的恩情,虽死无恨!”
惜泪听了,也觉无奈,便劝玉儿道:“玉儿,休要任性!小田既然选择留在凤都,又投了尹师兄门下归属凤太师尊,便无形中与我等为敌了。你若要报仇,则连你哥也是仇人了。今日你便听我的话,且在西阁你嫂子处住下,等师父回来,我去回禀了,将你收在门中,我们兄妹好在一处,也热闹快活!”
寒玉见阿泪并不向着她,心里生气,但又恐同门不和,阿泪在门中不安,权衡一番,寒玉道:“我不问你们充好人!我自与女伴菊影在城外风来栈等候,仇问回来了,我必再来要个说法!”
寒玉说着,抱了灵位含恨转身离去。阿泪知道妹子向来任性的性子,并不去追,倒是云泽见了,忙道:“她一个小女子,伴着另一个姑娘家,若没你这大哥照拂,没的受人欺负,阿泪…你去追了她回来吧!”
惜泪白衣当风,望着妹子去的方向道:“她长到二十二岁了,我的妹子,她的性子我最了解!你两个若现在一处相见,她恨意迷心,必要一剑刺你!且寒玉行事一步,必有下步成算在心。你再劝也没用的。她肯暂时离去,已是顾惜你我颜面的了。”
不说寒玉,且说那袁秋,她本是风月场中的老手,这回见星柔双目明澈,秋波媚人,大异于前,心里便明白几分。星柔与袁秋坐在榻沿闲聊道:“秋儿,这回门中内斗,你不曾卷进去吧?”
袁秋道:“尹师兄看在田哥儿是公子妹夫的面子,常来咱家醒竹巷的宅子,给婢子送些贴补。夫人走的这些时日,夫人及公子寄来贴补原是足夠的,不过有了尹师兄的这份,我日子更宽裕些。故此,尹师兄这回死了,秋儿也是受害的。”
星柔道:“你是我陪嫁丫鬟,原是最知书识礼的。如今怎么也这么糊涂起来?竟还去收尹师兄这个对头人的贴补!好在如今姓尹的死了,不然你这女孩儿的名节扫地!以后这件事当着谁也别说起,尤其不要让你家公子知道。”
袁秋心里怪星柔迂腐,嘴上却唯唯称是。星柔道:“门中尽有地方,醒竹巷的房子也就关着吧。你自今日起也跟着我吧,我们这院子虽然叫慕蝶西阁,地方却大得很。眼下,北屋是空的,给你搬进去住吧!”
袁秋听了,心中略安,但想起尹清、黄仲迴,心里泛起隐恨,口里略略谢过也罢了。
时光易过,早已又到这日晚间。那兆惜泪却又不归,却招呼宋玉京的小僮幺哥捎了他亲笔书简回家。说明今晚留在兆灼的石室守他,又要冷落娘子了。星柔叹了一声,也不怨他。自用了饭,没情没绪歇了。
不想不到初更,那惜泪又回来了。俊脸坏笑,不免甜言蜜语讲了些陪情的话,胡乱吃了宵夜,陪了星柔歇了。两下里情爱甚炽,星柔在帐冲携了阿泪的手,那手细如凝脂,明明与平日不同,可星柔哪里有察觉?当下她却又把袁秋来投的事说了,那阿泪枕上全不上心,道:“来便来了,全由你做主,和我并没干系。娘子如名花入眼,我何必再去管别人?”听得星柔心花怒放,哪里会疑!
看官知晓此夜这人又是假的,那真正的惜泪又在何处?此时他却在城外的倦仙楼,与越长涛喝酒。只为那倦仙楼,与寒玉、菊影订的那家风来栈相近。兆、越二人,对着清冷月色,坐在二层楼上,品着丝丝缕缕幽怨箫音,偷偷喝起闷酒来了。
原来今日傍晚早些时侯,那宋玉京说出新制了一丸好药,可以压住“长乐”身上之毒,长涛见兆灼服药之后睡得老实,便托了原住在那间石室的季师弟帮忙看护,那季师弟平白得了好些馈赠,满口答应做个顺水人情。长涛本想阿泪已经劳累多日,今日定然想回家的了。谁知兆惜泪踌躇半日,便说要去拉玉儿回来,又拉了长涛同去。
长涛拗不过,只得相随了。可两个来到风来栈门前,阿泪又换了主意,拐到隔巷的倦仙楼去了。
两个在二楼雅间,临轩而坐,弄些个清雅丝竹,不觉阿泪喝得大醉。长涛也有些醉意,便一面重重敲桌,一面问阿泪道:“惜泪哥,我瞧你从来活得不快活。我看嫂子待你甚好,你却甚是冷情。可我知你向来非薄情寡恩的人!兄弟不说虚言,你只明白告诉我,你到底…怎样打算?”
那兆惜泪竟默默落了一回泪,这也是头等的稀罕事,只见他泪珠落杯,端起盅儿猛啜一口,又重重摔在桌上,酒液溅污了艳红桌布,惜泪恣意哭道:“涛子!醉中言语,不怕你知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知该如何了。如今,我也只有对你说说心里话。当年,义父母定了这门亲事,我见阿柔端丽秀美,倒也心足了。只因我二人是初见不久,不敢唐突,便把良宵错过。谁知新婚即别,又谁知一别,我便见了白师妹这个魔障!那日自作主张,去刺你家主公伍信,在月下一见了她,才觉自己一瞬之间通晓‘人事’!我不知她心里怎样想我,我却只是一心一意想着她!虽我也知没名没分,不能想她,却宁可万劫不复,心里还是挂着她呢!大约这情爱之事,就该是这般扯不清理不明的吧?后来我同阿柔聚少离多,到后来竟怕与她守在一起了。我心底里,又深愧自己亏待了她,实在不知该如何弥补。我有心爱她敬她,可冷待久了,岂是几句暖心言语便缓得的?我又想收了本心,好好与她携手共命,可偏偏骗不了自己这心,口不对心的事,万万做不出来!我还有心,索性和离了,自己哪怕去做和尚也甘心的。可你知道江湖险恶,陆大哥虽说疼爱她,也能护她一生周全。贸然丢开她,叫她往何处安身?又叫我拿甚面目去对义父母的天灵?又怎么去对云泽及师父交代?左不过一个抛弃结发的恶名是免不了的!”
如此晚秋静夜,兆惜泪与越长涛在倦仙楼买醉,却不知楼外在此夜已发生了惊天之变!
原来,兆烨打败楚公子后,岩香向腾龙归降。岩香即告灭亡,不意兆烨在归来途中,旧伤迸裂,中途草草医治,却不见好。兆烨无奈搬师,退在府中静养。他那奶公孙敬安,深怕兆烨失了权柄,祸及自己,竟连夜入禁宫,秘会那位王太后。那位王太后,那盲目的太后,也非什么善类!她本藩王妾室,夫君早已下世。正妃夏氏仁懦,被她活活气死。夺了小儿兆熵,自幼抚养。兆烨挑选旁支,那王氏自薰双目以表忠心,兆烨见她难起风波,遂编了一套说辞,将兆嫡扶立为君。王太后上位之后,暗里找了名医邓太医,早医好了眼睛,却只扮作盲眼的,思量要哄兆烨。如今见兆烨卧病,王氏也动了心思,勾结孙都管并非一日了。那孙太监一心自握权柄,想拔兆烨羽翼,便说服太后,派兵去剿血槎门。
这王太后,怕自己跟湛翠太后一样,便铁了心要除去异己。当下书了一封凤诏,付与孙敬安。老太监退出又与自家心腹商议许多要事,正是:暗里定下杀人计,谁知害人是害己。
那孙敬安勾结了御林军将领毛正,趁兆靳受伤昏迷之际,袭杀兆烨的心腹兆靳,又以兆烨害振武帝之事,借敏惠帝口吻写旨,幽禁兆烨待查。
且说孙太监心腹乃同乡李公公,是日夜中带太后的凤诏,带兵前去慕蝶楼,正欲一并抄杀,谁知同来的张副将不愿进兵,大兵只在濛水驻扎。李公公趾高气昂,拉了张副将一个,旁的只带个把太监,自去宣诏。云泽自不露面,吩咐门人不必留情,尽力抵挡。乱斗之中,李太监被门人花某砍杀。
原来李太监此回所带人马,原是那毛将军带的,可毛正是个刁滑之人,对副将道:“我今抱恙,江湖之事便不去了。你需谨记,咱们的人去是去了,千万莫要轻动!那兆烨一日未死,他与孙太监的胜负难定!我借手杀了兆靳,不过想得些权势,如今抄杀血槎门,实乃不智之举,我若做的太卖力,伤了兆烨的心腹,一而再再而三,就当真与他结下死仇,到时不好退步了!”那副将见毛将军不出面,也不敢轻动,当下收了李太监的尸首,退回龙都去了。
大乱暂平,云泽听那位在石室看守兆灼的师弟说起阿泪与长涛去了倦仙楼,不由大怒,唤过门人王师弟,急令他速速找回他二人。
闻听传信,阿泪也顾不得寒玉,只得愧颜满面回楼。实无颜面去正厅见云泽,便思量躲到自己的西阁。
这一回并不要紧,只是他日后命运,又要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