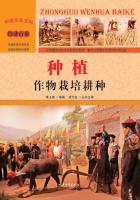最后爸爸只有说:“那你明天来嘛,明天我们彩排,都是屋头的人,来看我们彩排然后一起吃顿饭嘛!”
走人户,意为走亲访友。
“屋头人都来啦?”陈修良说。
“啊!我哥嘛,还有我姐也回来了!”
“莉珊也回来了啊。”陈修良抽了一口烟,把烟锅巴在地上杵了,又用脚板踩了踩,“那我来嘛,也来帮忙嘛!”
“哎呀!你帮啥忙哦!你就带起眼睛来看,带起嘴巴来吃就对了!”
抽完了烟,说完了闲话,爸爸心里总算舒坦了些,陈修良转身子走了,留下他一个人买软中。
买软中就买软中嘛,这头爸爸正在摸钱,那头他的手机就嘟嘟嘟响起来了。还是那,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唱得那叫一个婉转。爸爸把一张一百的票子挥给周老四,空出手来接起了电话。
真是见了鬼了,电话那边居然是姑爹。
“胜强啊!”姑爹还是那个声音,斯斯文文,讨讨好好。
“啊!啊!”爸爸下意识还是想喊他一声哥,又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妥当,“你说嘛!”他最后说。
周老四把零钱找给爸爸,他一把抓过来塞进裤子包包里,转过身去好专心致志地在心头骂姑爹:“你个龟儿子!现在来找我,找我肯定没好事,有啥事嘛,几下说完,老子好回去吃夜饭。”他想。
“胜强,”结果人家姑爹说,“我回来了,现在在北街这边,你看你有没空跟我见一下嘛,我有事想跟你说。”
不用说,肯定是姑姑的事嘛,既然是姑姑的事,就是个泥水坑爸爸也只有扑通一声跳下去了。只可怜妈妈备了一桌子的饭菜,可怜爸爸累得心慌慌,还满心想着回去吃两颗神仙药,也只能勒转了缰绳去见姑爹。一个家这么大,按到这头按不到那头,就像奶奶说的,管个家真的难难难啊。
一见到姑爹的打头,爸爸就懂了:穿个吊垮垮的衬衫,胡子也没刮光生,脸上污一坨黑一坨的看起来霉得慌,坐到茶楼里头,位子边上放了个女兮兮的公文包,一看到爸爸走过来了,端手的茶杯子扑通一声放到桌子上,站起来笑嘻嘻地喊他:“胜强!在这!”
还有啥好说的?爸爸心头骂了句怪话,一屁股坐下来:“肯定是这瓜娃子后悔了,要找姐和好嘛!你早到哪儿去了呢?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龟儿子的!”
姑爹倒还想得美,面子上还要虚晃一下:“胜强啊,你姐回来这么多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爸爸呢,就没他那么好的涵养了,反正他本来就是鬼火冒,想着“刘瞿康你回来就是跳炸药堆堆的”,他就说:“大哥,当时我咋给你说的?好自为之!好自为之!我姐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说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姑爹的脸唰地白了,然后又红了,粉嘟嘟的倒也好看。“哎呀!胜强!这事弄成这样,真是……我也不想啊!”
“那你说要咋办嘛。”爸爸懒得跟他废话。
“这事啊,”姑爹说,“你真的要帮我劝一下你姐,你说我们这么大了,离啥婚嘛!离婚协议你姐签了字,丢给我,我还没签……我真的是不想离婚啊,她又不见我,胜强,你要帮我说句话啊。我们离了对哪个都没好处,有啥事不能好好商量呢?”
听他这么一说,怪得很,爸爸心里面觉得落了一块石头,他暗暗松了一口气,说:“大哥,不是我说你,姐肯定是被你气慌了,不然也不得闹成这个样子,你说我姐好好的脾气!”
“是啊是啊,”姑爹赶紧点头,“本来也没啥事,不知道你姐这次为啥这么坚决,一下子就说要离婚,然后就搞成这个样子了,真是一点预兆都没的!”
“没的预兆?”爸爸真要背后伸出手来给他两个耳巴子了,他想,“你龟儿子租个房子养个婆娘的时候不是预兆啊?”——按理说,他肯定是要骂姑爹两句的,骂舒服了再骂个四五句也可能。但,将心比心的,爸爸也不是不讲道理,也不是不想家头的人好,要得公道,打个颠倒,他想到自己这头的鸡飞蛋打,想到妈妈的宽宏大量。
他就稳了稳气,说:“好嘛,我就帮你这一次,但是我先说清楚了,这是最后一次!你要是再搞点啥花样出来,不要怪我不客气!”
“哎呀胜强!”姑爹抹了抹额头,“我懂我懂!我哪还敢嘛!你姐一走啊,家不成家,刘星辰天天都在念我,说我把他妈气跑了没人带娃娃,唉!我简直不活人了!”
爸爸不说话,他想问一问他呢又觉得没什么好问的,想劝他两句呢又觉得他真的是该得该遭。他看着姑爹放在椅子边上的公文包,正在想事,那茶房的小妹却想起了,这个时候才跑过来问他要喝啥茶。爸爸干脆就说:“喝啥喝!话都说完了!人都走了!”
他就站起来走了,也不问姑爹吃不吃饭,喝不喝酒,晚上到哪儿去消遣。姑爹呢,在他后头喊:“胜强!这事你要放在心上啊!”
爸爸走出门去,看见姑爹的雪铁龙轿车停在路边上,心里面又是一阵鬼火冒。他还是讲信用的,拿出电话来给姑姑打电话,一边打,一边想:“你们这些人啊,一串糖葫芦样跑回来!叮叮咚咚的!还嫌老子不够烦!
他倒是骂着,饿着肚皮,等着姑姑接电话,却不知道自己以后还是要记着姑爹的好的。“鬼才想得到,事情居然是这么长起在!”他后来说,“要不是大哥回来这一趟,我一辈子都是个瓜娃子!
以后的事啊,神仙也说不清楚。我们镇上的人怎么唱的呢,唱:讨口子,惹人嫌,挑根锄头出城关,田坎间,挖一挖,挖个红苕好吃饭,挖到一箱金元宝,抱个婆娘把家还。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爸爸跑到金叶宾馆去找姑姑,那个时候他还没体会到这个道理。姑姑正在房间里面看书,把门打开放爸爸进来,问他“胜强,你怎么现在跑来找我?有事啊?”
爸爸呢,嘴里头包着话,看着姑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说了。他先是上了个厕所,然后又说要吃饭,姑姑就打电话让总台送一碗牛肉面上来,两个人等着等着等这碗面,没法了,爸爸终于开了口。
“姐啊,这事本来也不该我开口,不过大哥找到我这,我就只有硬着头皮来了……”
姑姑手里面本来拿着书,这下把书也放下了,说:“他还挺聪明的,找到你了!
“姐,”爸爸喊了一声,觉得气虚得很,他搜肠刮肚地想找两句话出来,又饿得钻心,“其实啊,前两天陈安琴才说要跟我离婚。”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
“哦?你们俩又怎么了?”姑姑问。
爸爸就把这次和妈妈的曲折,深一句浅一句说了,本来,他早就想跟姑姑说,憋了一肚子也找不到时候,这下终于一吐为快了。跟大伯还不一样,和姑姑说起来,啥妈妈啊,钟馨郁啊,娃娃啊,他就说得格外动感情,中途服务员送来了牛肉面,他抱怀怀里头也没顾得上吃,继续说:“所以姐啊,本来你和大哥离婚我是支持的,但经过这个事,我觉得两口子能在一起真不容易,怎么说还是原配好,大哥又来求我,我就来当个讨人嫌,当这个说客。你考虑一下嘛,毕竟离婚书还没递上去,递上去后悔就来不及了,几十年的夫妻,你说呢?”
姑姑听爸爸有声有色地这么说了一番,哭笑不得。“胜强长大懂事了啊。”她心里闪过去想了这么一句——就是这个意思嘛,真像是河马嘴里面钻出了黄鹂鸟。
“你先把面吃了吧。”她说。
爸爸这才想起面的事,他收拾起心情,埋头吃牛肉面,一边吃,一边等姑姑说话。
姑姑呢,坐在沙发上看他穷痨饿瞎地吃面,看到爸爸脑壳顶上真真切切有两三根白生生的头发长出来了,她说:“胜强你多吃点,不要饿到了。”
这句话她倒是说就说了,爸爸心里面呢,不知道想起了多少往年间的穷日子,旧年月。他还是笑嘻嘻的,说:“姐,不能多吃了!你看我这肚皮!”
两个人看了一回爸爸的肚皮,笑了一笑,姑姑终于说:“你大哥这事,你也不要帮他说好话了,我和他这婚是离定了。”
“为啥呢?”爸爸没想到,这姑姑真是雷打不动地坚决。
“你想啊,”姑姑把两只手抱在膝盖上,“我和他早就没感情了,过一天挨一天日子,本来也就这样了。可现在有了妈这个事,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子了,不然等到妈遗产一下来,他不是捡了个大便宜?其他也就算了,他拿我的钱养个女朋友,那是我自己的失败,可是妈的钱还要给他,我真是不忍心。”
爸爸真的吓到了。天外面第一次听到这一声响雷。他简直莫名其妙,脑壳光光,把面碗放到写字台上,问:“姐,你说的啥啊?我咋一句都听不懂?妈为啥要分遗产?她有啥遗产?”
姑姑看了他一回,这才想到这个小娃娃可能真还蒙在鼓里。毕竟也是自己的亲生弟弟,姑姑就放软了声气,对他说:“以前外爷留下来的东西,妈说了,现在算下来七位数肯定是有的,这些都是要留给我们三个的。”
爸爸扳着手指拇数了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不得了!哪时候家头冒出这么多钱来了?他咋屁都没听到一个呢?他就问了:
“不可能吧!我怎么从来没听过!我还守到厂里头在呢!”
“厂是厂,其他的钱是其他的钱,”姑姑细细地给爸爸解释,“你那个时候还小,妈可能也没给你说,本来啊,豆瓣厂连着半条西街都是薛家的,后来充了公——就算是充了公,外爷也私自藏了些下来,都是古董,到现在真是值价的,所以,就有这么多钱。”
爸爸张着个嘴,真像在听说书先生讲神话,脑壳里面嗡嗡嗡的,这倒不是钱的问题——他薛胜强这辈子钱还是不缺的——问题是,这么大个事,奶奶居然从来没跟他提过!
“这事你和哥都知道?”爸爸脑壳里面轰隆隆的,忽然想起那天在鱼跃庄大伯好像也提到过遗产这两个字。
“对啊,”姑姑点了点头,“就是你哥给我说的,他说,”她顿了顿,“好像从安琴那听说的。”
姑姑一张脸白白净净的,映着宾馆房间里面的灯,瓷盘子一样,一点也不显老。爸爸就想到以前每天守着电视看她播新闻的时候:今天美国要打仗,明天非洲饿死人,后天下雨,大后天出太阳——就是这些事,反正嘛,跟平乐镇这一块二方地似乎都没啥关系,爸爸也就是看个亲热,听个稀奇。
现在这一回,也算是个新闻了,但爸爸听在耳朵里,响在心口里,那卡在喉咙上的何止是一口浓痰。
这下子,他没闲心管姑爹的事了,姑姑把他送出来,喊他早点回家休息:“胜强,明天还要彩排一天,事情太多了,你也不要多想了,早点休息,啊?”
爸爸答应了她一句,继续往外面走,心里面一阵一阵扯起扯起地痛。他给大伯打了个电话没人接,这才想起他去约会了,好嘛,他就给钟师忠打电话。
还是老钟对啊——钟师忠一把就把电话接起来了,欢欢喜喜地说:“薛胜强!你个虾子这下放出来啦?我还以为你终身监禁了!”
爸爸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走下了金叶宾馆的台阶,他想说:
“老钟,老子又当闷猪儿了!结果我妈背到我存了一笔钱!”他想说:“老钟啊,你说陈安琴对我这么好,难不成真的龟儿子是为了这笔钱?你说我哥我姐我还想得过,他们毕竟是挣工资的,我!我又不缺钱,有好多钱嘛,那婆娘不至于嘛!”他还想说:
“老子想不通!老子这回真的瓜了!老子找你喝酒!”——但是他哪敢说?奶奶早就教育过了:“胜强,你啊说话真要注意了,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得过过脑子,不要当着外人说家里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他就只有说:“老钟,上次你说的那个医生,小姚找的,不然我还是去看一下嘛,我这两天心口真的有点不舒服。”
钟师忠真是关心爸爸的,在电话那边马上吼了起来:“哎呀!你咋回事胜强?你赶紧回去休息赶紧回去休息,这事马虎不得,心脏病不是一般的,你要记得吃药啊!”
“哎呀,我现在就回去吃药嘛,你不要吼嘛。”爸爸一步一步下台阶,觉得走一步脑壳就跟着痛。
“你这人啊!”老钟说,“你说你在倔啥?这么大的事,还鼓捣不许我说出去,安琴现在知道这事了吗?真的瞒不得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她说,喊她这两天好生照顾一下你,周一我们好去城里头看病。”
“哎呀哎呀!”爸爸一听到妈妈的名字心里更不安逸了,“你不要给安琴说,说不得啊,这两天更说不得!”
“有啥嘛,”钟师忠也是生气了,“不就是你妈过生吗?有你哥你姐在,你怕啥,不能说给老太太祝个寿,把你的命收了嘛!”
话是说重了,爸爸知道他还是好心,他好声好气地说:“不是这事,是我和安琴自己有点事。”
“你们有啥事嘛,是不是外头那个事闹起来了?哎呀胜强,我不好说你的,这事真的是你不对……”老钟还要啰唆。
爸爸正儿八经累得心慌,没精神跟他扯,他说:“哎呀,电话里头说不清楚,不然明天你来厂里头嘛。明天我妈过生彩排,一起吃个饭,家头人都在,不然星期六就闹了,话都说不到两句。”
“来嘛!”钟再干脆不过了,“我来给你帮忙,你娃给我注意到点,好生休息,不要瞎搞!”
爸爸走在北门上,黑漆漆的一条路一直走到了十字口,越走越是荒凉。本来,这镇上的每一个铺面,每一根电杆他都再熟悉不过了,过了十字口打个右转手,就走到了西门这条街。这条街道上古来是开私塾的,解放前有一家岷阳书院,爷爷还在那里教过书,后来成了平乐二小,一到下午,门口水泄不通都是接娃娃下课的家长。过了二小,两步就走到了神仙桥,过了神仙桥,就是豆瓣厂,过了豆瓣厂,就是曹家巷(以前爸爸他们住的院坝也在这开了个后门),曹家巷斜对面过去是庆丰园,然后再往城外面走一走,过了新修的二环路,就是那个住着妈妈陈安琴和他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