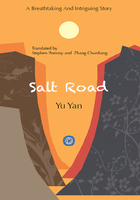塔罗小阿卡纳分为杖、杯、剑、币四大组,分别代表火、水、风、土四大元素。每组牌中都有侍从、骑士、国王、王后。小阿卡纳便是:侍从成长到国王或王后的路程。权杖代表火,权杖侍从便也是热烈的、极具行动力的少年。如光如希望。
弟弟米开朗
文/潘云贵
初春的北京,雪依旧在下。夜里,我从酒吧踉踉跄跄地跑出来,准备回自己的住所。走在路上,感觉世界都在一个劲地摇晃。脚下的高跟鞋情绪亢奋,一路上摩擦着路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我停下来,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双5厘米的高跟鞋脱下来,扔向了垃圾桶。一只进去了,一只砸到垃圾桶的外壳,孤单落地。胸口囤积了数日的雪球仿佛滚走了,我突然感觉好爽:“在我面前嘚瑟的全都不得好死!”喷着酒气的脸颊洋溢着骂人的快感,我想此刻,全世界都没有人比我幸福了。
大学期间没拿过奖学金,搬到校外住地下室负二层,挤地铁从来没有占到座,被男友玩弄后抛弃,还被小三推倒在地,现在就连打个的士,兜里也掏不出半毛钱,全世界没有人会比我幸福了。我要怎样感谢这个世界的恩赐呢?
我要尽情舞蹈,我要放声歌唱,这个伟大的时代太美太美,我喜欢!没有人可以阻拦我去爱它,去爱它,爱它……
“够了没?醒醒吧,老姐。”视野里闯进来一个小男人,模模糊糊的衣着、面容,只是声音太过熟悉,烧成灰烬都能辨认出的那种熟悉,“瞧瞧你现在的德行,简直就是一个泼妇,怪不得全世界的男人都不要你!”
没有发育彻底的声音像生锈的铁,这是我的弟弟,米开朗。“滚!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见一个爱一个,都是挨千刀的。滚,走开!”我朝他醉醺醺地叫骂道。他倒没被我喝醉酒的样子吓到,见我的双脚此刻苍白得就要碎了,立马跑到垃圾桶边把高跟鞋提了过来,就连那只深藏在桶中深处被果皮、易拉罐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高跟鞋都能找到,提过来,像小时候提着死耗子一样表情猥琐地提过来。
“丢了就是丢了,别给我,我不会再要了!”米开朗递过来的鞋子转眼间又被我扔回了垃圾桶,死状跟先前一样。
“你倒真是感觉累了不会再爱了啊!只会咆哮的女人,活该只能当个李莫愁!”米开朗鄙视地看着我,然后把脸甩到一侧,双手插在裤兜里。
“你这臭小子,以后也是进化成臭男人的料,不如现在我就先替以后成千上万受苦的姑娘消灭你!”语毕,我就咬着牙向米开朗扑去。他一溜烟就闪到一边,我晕晕地趴在了雪地上。“从小到大,你的‘九阴白骨爪’什么时候赢过我的‘凌波微步’啊,哈哈……”米开朗得意地笑起来,一排牙齿白得就像今天晚上消失的月亮,我的眼前这下一片漆黑了。
脑子里再有意识的时候,苍白的脚踝又被那双高跟鞋包上了,我发现自己正趴在谁的肩头,虽不算厚实但也能支撑我105斤的身体,还有一阵暖暖的热气涌进我的心里。
“见鬼了,瞧你体型也不算胖,竟然是个实心球。这么沉,比我的妞还沉,果然腿肚子大的姑娘不能背啊……”
生着铁锈的声音一瞬间打进我的耳鼓内部,我知道此刻背我回家的人还是我深深讨厌的弟弟,米开朗。
只是什么时候,他的个头竟然蹿到了180cm,噢,这才是叫人见鬼的事。
严格一点说,米开朗并不是我的弟弟,首先在血缘上,他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其次在长相上,他是标准的锥子脸,双眼皮,而我是大饼脸,“内双”;最后他跟我也不同姓,他叫米开朗,姓米,我叫乐瑶瑶,姓乐。
很多人会觉得米开朗的爸爸一定是个留过学的建筑师,其实只是一个医生。他爸和我爸在同一家医院工作,所以米开朗自小便跟我玩在一起。因为我钻出我妈隧道的时间比他钻出他妈隧道的时间早一天,加上后面女生发育得比男生快,所以那时个头上稍稍领先的我就喜欢叫他弟弟。米开朗很早的时候就显露出了自己作为帅哥坯子的潜质,在学校、公园、街边,或者大马路上,只要有人拍照,我就知道那些可恶的咔咔声所瞄准的对象就是米开朗。和他走在一起,我很好地发挥出了自己提早作为配角大妈的潜质,压力如山大。
我怕米开朗长着长着,不小心就长成了胡歌或者霍建华,所以每次只要他一跟我走在一起,我都会让他戴一顶棒球帽,并把帽檐不断往下扯,直到他的那两道剑眉看不见为止。米开朗没有对我的举动表示抗议,相反他总会在我每次给他帽子戴的时候笑,那么天真无邪,让我顿时羞愧。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即便这样遮盖米开朗的锋芒,他这颗小星星还是发光了,一堆女粉丝就像撞墙后流血的脑残给他写大批大批的纸条,全是粉红色的信纸,画着一朵朵羞答答的玫瑰,偶尔在他单车的篮筐里还会捡到一些,上面写着“你戴帽子时的样子最酷最帅,就像越前龙马,我好喜欢”,气死我了。所以从小我就深刻认识到米开朗的“后患无穷”性,包裹不住的美少年永远都是少女们的灾难。
当然和我走在一起,米开朗也有不戴帽的时候,比如在太平间。夏天真是活活闷死人的季节,我和米开朗被拼尽全力修筑长城的妈妈们抛弃了,待在我爸和他爸所工作的医院里,办公室的空调无聊地吹出一些风,后来它吹累了,索性连一丝冷气都没吐出来。我就拉起米开朗的手直往太平间跑去。
“为什么要往那里跑?”“因为那是通往幸福的地方啊。”“可是,那个房间看上去好奇怪啊。”
“会吗?可我爸爸说,那里会通往天堂。弟弟,你见过天堂吗?”“没有。”
“那你想见吗?”“嗯!”
就这样我学着大人们编谎话的本事,成功地把那时还很单纯的米开朗偷偷骗进了太平间。太平间真是避暑的好地方,里面是一片雪白雪白的世界,凉飕飕的,我们会爬上一些床,跳来跳去。那天的太平间似乎真的很太平,一具死尸都没有看见,只有一张一张铁架子的床,被我们推来推去,东一张,西一张,横七竖八地碰撞着。
窗外是一排樟树,茂密的叶子在太阳下仿佛被酒精刷过似的发出一层层青翠色的光,偶尔有风从我们打开的窗户外刮进来,把凉飕飕的太平间吹得更凉了,同时也掀起了角落里几张床上的白布,露出一张张惨白惨白的脸,那种惊悚的效果绝对不是弱智的国产鬼片可以拍出的。那一刻我才见识到死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当你没有设防的时候它们悄无声息地出现,可以夺走你最大分贝的喊叫。那个震耳欲聋、绕梁三日的尖叫至今还叫我爸记忆犹新,那时他闻声跑进太平间,看着蜷缩在一边的我,对着围成一窝蜂的院领导、医生和护士,低头尴尬地说:“这是我女儿。”我第一次发觉我爸在介绍我时背是驼的。米开朗他爸倒是在一旁看得兴致勃勃,他的儿子很聪明,很争气,没叫,一溜烟就爬出了窗,一点蛛丝和马迹也没留下。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叫米开朗的弟弟,面对死人他一点都不害怕,面对哭泣中的我他跑得比孙猴子都快。
或许是他太过勇敢,勇敢到神经已经在他小学毕业前就达到麻木的顶峰状态,所以在他六年级他妈从五楼阳台上一个箭步跳下做自由落体运动时他都没有感觉。他妈死得很美,美得就像一朵梅花,因为她穿的裙子是红的,碎掉的脸颊是红的,吐出的鲜血是红的。可惜这样美丽的花一个女人一生也只能开一次。他爸错过了。
米开朗他妈进行这样一种危险的行为艺术完全是因为米开朗他爸,一个外表看上去没有任何优势可以招到小三的男人却用自己的工资和平日收到的红包成功填补了这一弱势。一贯喜欢修长城的米开朗他妈闻讯后,不得不从麻将桌上撤下来而转到实际战场,智斗小三。或许每个人的智力确实有限,加上米开朗他妈嘴皮子功夫还没有那些专职小三修炼到家,每每捉奸在床后又迅速败下阵来,望着自己男人那一脸咬牙切齿恨不得用手术刀杀掉自己的表情,米开朗他妈彻底绝望了,她纵身一跃,用实际行动向米开朗他爸证明了原配是这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唯一会为你付出生命的人,而小三她会吗?
可惜他妈的这一壮举并没有让一个平日见惯了人体器官的外科医生产生愧疚之情,倒是顺水推舟扶小三坐上了正妻的宝座。在米开朗上了初中后,他爸就顺利和小三结婚了,从此他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米开朗却从此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占据了S城几乎一半的地方:网吧、迪吧、酒吧、KTV、桌球室、地下放映室,人们都叫他们痞子、流氓、混混,学名称作不良少年。
在米开朗还没有进化成不良少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在学校的天桥上吹风。我喜欢脱了鞋子,露出两条萝卜腿,伸到桥下,在风里荡来荡去。米开朗没有学我,他盘腿坐着,像个童子,仰着45度忧伤的角看着天空,脸上很落寞,似乎世界上没妈的孩子表情都应该像他一样。
“你妈妈离开那天,没看见你哭,现在怎么装起忧郁了?”“姐,你说我要不要去找我妈?”
“呃,找你妈妈?”米开朗没有回答,他站了起来,伸开双臂。
我见情况不妙,立即抱住他的腿,大喊道:“娃,你还年轻,可别想不开啊,你要是一跳,全世界的少女都得为你发洪水了!”
“什么嘛,我只是伸伸懒腰啊,姐!”“不早说!我还以为你真要去找你妈呢!”“姐,我要找的妈不是那个整天把麻将看成自己亲儿子的妈,我要找的是我的亲妈。”“呃,你在演连续剧吗?”
没想到米开朗真像流落民间的王子一样还有个身世之谜。他亲妈在生下他后不久就离开了他爸,从S城回北京生活。他爸随后就和米开朗跳楼的那个妈结婚了。那时米开朗还小,自然不知道这些。最近他爸把米开朗新一任继母的肚子搞大了,新继母自然扮演着恶毒女人的角色,怂恿他爸把这些告诉了米开朗,意思是叫这小子滚蛋。听说米开朗跳楼的那个妈原先也是个小三,她用死其实是想证明一点:看,做小三的,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米开朗说着说着,神情越来越失落,像梁朝伟,又像张国荣,看得姑娘我潸然泪下。
“弟弟,其实我们的命都一样。”“呃?”
“我妈也不是我亲妈,她总说我是从垃圾堆里抱回家的,是从大马路上捡回来的,呜呜呜……”
米开朗真是好孩子,他竟然相信了我,于是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唱着《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我为自己编谎话成功骗取纯情小男生的绝世神功而沾沾自喜,胳膊肘一不小心把身旁的鞋子推了下去,砸到了天桥下正想偷偷接吻的一对学生情侣,那女生哎哟地叫了起来,一抬头,又见我两条晃荡晃荡的白萝卜小腿,顿时吓晕了,倒在她对象怀里。那男生看看四周后,背起那女生,跑了。我和米开朗都笑了,我说那男生绝对是练体育的,背着那么重的女的还跑得那么快。米开朗却盯着我的两条腿,又大笑了半天。我赶紧把腿拿上来,拉下裤腿,说道:“笑屁啊,我只是腿上小肚子大了点,我人真不重,要不弟弟你背背我就知道了。”米开朗咂咂嘴巴,继续唱着《鲁冰花》,一脸鄙夷地走掉了。“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
米开朗开始学会抽烟的那一年,我才意识到一个少年也可以坏得这么帅,连抽三块钱一包的“友谊牌”香烟都可以抽得这么有范儿,一投足,一个眼神,绝对不是抽烟抽得再凶,姿势摆得再酷的体育老师、教导主任、校长或者周润发可以与他相比的。我说他可以直接去演戏了。他问我演戏是不是不用学习就可以赚钱了,我点点头。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打上发蜡,穿上他爸的西装,系着粉红粉红的领带,衣冠楚楚,站在我面前,说:“姐,我要去演戏,我不读书了。”我顿时目瞪口呆:
“亲爱的弟弟,我没叫你去做小白脸啊!”米开朗愈发成为众多女孩发育期思春的对象,打电话的,发短信的,还有写古典情书的,一堆一堆,每日只增不减。而他不知是脑子还没开窍,还是根本无心理睬这些自己长腿跑来的野花,一次电话也没接过,一条短信也没回过,一封情书也没看过。那段时期,世间不知多少痴女子为他哭成了泪人,米开朗却假装浑然不知。他继续抽烟、喝酒、打群架,被罚站,罚扫地,罚跑操场十来圈,围观的少女总是一波一波,海浪般汹涌。仿佛这样的美少年越坏,女生越爱。真是奇怪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