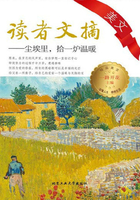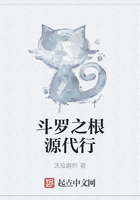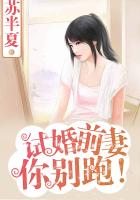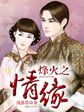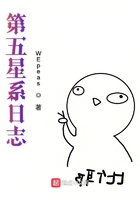爱斯基摩人的生死观
日本著名探险家植村直己征服了北极以后,颇为自得地写了一本小册子:《我站在北极点上》。书中写到地球最北端的爱斯基摩人部落里一个跟鲸鱼搏斗的小男孩,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男人们都出海打猎去了,部落里只剩下妇女和小孩。一大群鲸鱼像是乘虚而入,蜂拥在离人群不到四十米的海岸边。每一头鲸鱼足有六七米长,鼻孔里喷出高高的水柱。部落里顿时骚动起来,枪声大作。才满九岁的小奴卡也抱着一支长枪,向海边冲去,一边跑一边射击。整个海面被鲸鱼的鲜血染红了,中弹后的鲸鱼变得更加狂暴。突然,小奴卡扔下猎枪,扛起一只海豹皮做的小船,冲进血浪飞溅的鲸鱼群中,他站在颠簸的船上,右手举起鱼叉,朝一头鲸鱼腹部狠命掷去。这一叉击中了要害,鲸鱼翻滚几下就漂到海面上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不要说常人,就连十年间以坚强的毅力将亚非欧美四大洲所有最高峰都踩在脚下的植村先生,也被惊得“目瞪口呆”。爱斯基摩人个体生命的强悍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最近,在一份旧报纸上读到上海赵鑫珊先生论及爱斯基摩老人自杀方式的一篇短文,使我得以了解这个古老原始民族个体生命强悍的另一面。
据赵鑫珊先生介绍,到了老年,爱斯基摩人常会走向自杀的道路。他们大多在年轻时是位勇敢的猎手,当他们年迈,行动不便,再也无法拿起猎枪,获得昔日豪迈的气概和光荣,就会有一种失落感。他们不想牵累别人,又不愿接受命运对老人的嘲弄性安排,于是就毅然决然选择了自我了结生命,以此摆脱尴尬的困境和痛苦。自杀前,他们会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亲友,然后便独自一人静悄悄地离开家,走向茫茫的雪地,找个理想场所,自沉冰窟,永远安息在万古不化的冰海之中。
植村直己以探险家的眼光,目睹了爱斯基摩人轰轰烈烈的生;赵鑫珊先生则以智者的眼光,洞见了爱斯基摩人彻悟后自觉自愿的死,他甚至认为,这样的跳进冰海,“就有作为一个哲学家而死的况味和意境”。我对于这个每一个个体生命从生到死都奏出最强音的古老原始民族,如果说十分羡慕未免有点矫情,那么实在是非常敬佩的。并且,我还固执地认为,爱斯基摩人既然是三千年前(那正是我们的甲骨文时代)从亚洲迁徙到地球最北端的格陵兰岛的,他们至今仍是黄皮肤、黑头发,而且驾驭狗拉雪橇的口令(在植村的书中,这些口令全部是音译)与我们北方人赶马车的吆喝声极为相似,那么,很可能他们跟我们这个民族有血脉上的联系。真是这样的话,则我们在进化的途程中,某些方面令人遗憾地发生了不应有的退化。
也许只是瞎猜吧。这样更好。
《三晋文明》 1994年第10期
审美的生活态度
人过三十,心灵之翮渐被现实的绳索捆紧,再不像青春年少般飘然于理想的玫瑰色天空了。面对纷至沓来的种种无奈,我们除了咄咄称怪又有何良策?
“逍遥。”六十岁的王蒙说。“对于我个人,它基本上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把生活、事业、工作、交友、旅行,直到种种沉浮,视为一种丰富、充实、全方位的体验。把大自然,神州大地,各色人等,各色物种,各色事件视为审美的对象,视为人生的大舞台,从而获取一种开阔感,自由感,超越感。”这段话出自王蒙新著《逍遥集》。本书是群众出版社“当代名家随笔丛书”之一种,收文六十篇,恰与著者年龄暗合,想必是有意为之,留作纪念吧。王蒙近年刻了三枚闲章,又以闲章为题写了三篇注文,曰《无为而治》,曰《逍遥》,曰《不设防》,而偏偏拈出“逍遥”二字冠于书前,可见这两个字在花甲王蒙心中的分量。我读《逍遥集》,透过恣肆的文笔,时时遇到王蒙从容微笑的目光,觉得缚住心灵之翮的那根绳索松动了。
《文汇读书周报》 1995年8月12日
诱人的“唐注”
读这部书(《胡适口述自传》),最有兴味的不是“传”,而是占全书半数篇幅的“注”。注者唐德刚先生,是胡适晚年入室弟子,在胡夫人眼里是“最好的好后学”。他的尊胡是不消说的。难得的是能尊之外还能批,且于尊批两端都出自历史的、科学的分析,尊得可信,批得在理。类如唐先生认为胡适整理国故的成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却又不止一次地指出乃师治学“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既推胡适为“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作”的“第一个英雄”,又尖锐地指出“文言是半死的文字”这个著名口号的病害,等等。常听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真要做起来,且白纸黑字,像唐先生这样的,鲜矣!又,唐先生天才卓异,胸襟透脱,雄于诗文,每将切身体验穿插其间,挥洒开来,不经意而成一篇有学有识有情的美文。如此,则“唐注”绚烂而多姿矣。
《文汇读书周报》 1996年3月16日
两种人生
唐寅一生,旷达自矜,名士风流,临终前的绝笔诗亦不改常态:“一日兼他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漂流在异乡。”他是以“狂”来衡量人生的。
徐志摩才气横溢,一册《爱眉小札》,记录的却只是“因爱而流出的思想”,除此,“决不愿夹杂一些不值得的成分”。他说:“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种事情”;“我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爱的成功,那就是生命的成功”;“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他是以“爱”来衡量人生的。
《火花》 1998年第2期
路翎的悲剧
路翎两度入狱,成为胡风集团中唯一“二进宫”者,终于“幕落秦城”。他的好友冀汸在回忆录中写了如下一段沉痛的文字:
1955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将你一个人变成了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岁(1923—1955),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位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1955—1994),但艺术生命已经消磨殆尽,几近于零,是一个衰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这使我想起茨威格笔下的旧书贩门德尔。门德尔是个超级书迷,他对书籍以外的世事一无所知。战争(一战)已经爆发,他还安静地坐在咖啡馆一隅读书,甚至不管不顾地接连给敌对国去信,催索他战前已付全年定金,但战争爆发后竟好几个月都没收到的期刊。在信中他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和恼怒。这些信当然走不出国门,警察局以通敌嫌疑逮捕了他。门德尔在集中营待了两年后,才被几位以前经常托他买书的身份高贵的主顾解救出来。但他已判若两人,不再是“世界奇迹”,不再是一切图书的“神奇的索引柜”了。
归来的路翎不再是路翎,正如门德尔不再是门德尔。但路翎更惨。门德尔不过在集中营待了两年,而他竟服刑十九年!门德尔毁于世界大战,路翎呢?
《火花》 1998年第2期
误读
今年看到两篇关于傅青主的短文:一篇是4月23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陈鲁民先生的《厚道与刻薄》,另一篇是10月13日《太原晚报》“天龙”副刊上刘建武先生的驳论《不要误读傅青主》。我赞成刘先生的意见,陈文确是误读了傅青主;还想抄一点资料,以补刘文。
陈先生说:“而傅青主对赵子昂的字也是一个贬:‘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以此证明傅青主属于“历代都有”的那种“文人相轻,出言刻薄者”。刘先生的意见是,傅青主是“硬骨铮铮的汉子,自然要‘极不喜’奴颜软骨的赵孟,由‘薄其人’至‘遂恶其书’,这是合乎情理的,倘是别一态度别一情怀,则傅青主倒不是傅青主了。”同一论据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傅青主在《字训》(见丁氏刊本《霜红龛集》卷二十五)中,确实说过上面被陈、刘两文作为论据的那几句话。问题是,那并非傅青主对赵子昂书法的基本态度。傅青主这样讲:“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紧接着又说:“近细观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显然,傅对赵只是“薄其人”,对其书法的认识则前后有变化,以前是“遂恶其书”,现在(即写《字训》时)仔细看过后,则认为“亦未可厚非”。并非如陈先生说的“也是一个贬”。要之,不因人废字,傅青主正有一颗“过忠过厚之心”,恰恰属于陈先生文中所倡扬的那种有“大家风范”的、“厚道的文化人”。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情怀,才是真正的傅青主。倘非如此,则真的如刘先生所言“傅青主倒不是傅青主了”。
《太原晚报》 1999年11月22日
夜读小札之一
【题记】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则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我在年轻时即以此自警。虽资质所限,收获寥寥,但差可欣慰的是,读书在我已成为习惯,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偶有所感,便题在书眉,或写在日记里。兹章录六十六则,汇成小札。这些文字,有的距今二十多年了。
一、读《巴黎圣母院》第六卷。精彩绝伦!仅此一卷,亦足成世界名著,雨果真是旷世奇才。
夜读第七、第八卷。艾丝美拉达和她的小山羊被一群混蛋以“圣神”的名义判处绞刑;克洛德虚伪、阴毒、无耻;侍卫队长的花花公子气和迷信,等等,使我愤怒窒息,恨不得撕碎这一切丑恶的东西。然而,卡西莫多出现了,他抡起巨灵般的拳头,把两名行刑人员打倒,一手托起姑娘,就跟孩子抓起布娃娃似的,一个箭步就跳进教堂,把姑娘高举过头顶,以可怕的声音高呼:“圣殿避难!”看到这里,我心胸激荡,跟着他高呼:“避难!避难!避难!”仿佛跟夏莫吕和刽子手们挑战。
连伟大的雨果也激情难抑了。他写道:“正是此刻,卡西莫多显出了他真正的美!他真美,他——这个孤儿,这个弃婴,这个被唾弃者,他感觉到自己威严而强大。”“这样的畸形人保护这样的不幸人,这是受自然、社会虐待的两个极端不幸,会合在一起,相濡以沫。”
真舍不得把书放下,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激动了。《茶花女》让我激愤,却不像这次热血沸腾,文学的力量真正了不起!
二、读《歌德谈话录》,爱克曼章,朱光潜译。爱克曼第一次见到歌德时惊叹:“多么崇高的形象啊!”我第一次读这谈话录,不由得惊叹:“多么卓异的声音啊!”我的心在每一行跳动,就像小时候过八月十五,从母亲手里拿过一份月饼,贪馋地看着,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思,一点一点啃,品着那一年才得一次的滋味。爱克曼真有福气,能与歌德这样的大师朝夕相处,他说:“尽管他有时并未说出什么重要的话,在默然无语时,他的风度和品格对我就是很好的教育。”
三、夜读《鲁迅全集》毕,掩卷后长舒一口气。一年多来,从这十六卷、六百万言中所得营养将终生受用无穷。鲁迅先生也是人。在厦大,先生住楼上,厕所很远,且须经过一片草地,而此地多蛇,为防止发生意外,先生晚间常就瓷痰盂小解,无人时从窗口倒下,“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先生竟这般真率。他的笔下无一处虚妄、矫情,有的只是锋利,切实,真率,赤子之心。
与一般弄笔者不同,先生是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的,因为“它们与黑暗同在”,只有那黑暗消亡了,他的作品也就不复存在,他才会满心欢喜地笑出来。然而我们至今还在读着鲁迅,我们的子孙也会接着读,从中汲取养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四、看电视剧《山峡中》,根据艾芜同名小说改编。发箧找出《艾芜短篇小说选》,正有这一篇,读完又把鲁迅《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重读一遍。鲁迅的深刻是无处不在的,即如这封给艾芜、沙汀的复信,指出:“若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一位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这里强调的首先须是“战斗的无产者”,其次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二者兼具,才可以对“现代以及将来”有意义。孙犁、赵树理、艾青便是这样的。
五、季镇淮《司马迁》共七章二十四节,前五章十五节从纵的角度叙述了司马迁的一生,贯穿始终的红线是司马迁的实践主义和坚持理想的精神。第六章共九节则从横的方面,即通过剖析《史记》的基本方法、司马迁褒贬历史人物尺度的人民性等来塑造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形象。《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实践主义和坚持理想的伟大精神的结晶。第六章从文体上看更像是一篇研究《史记》的论文。因为出发点是人,不是文,所以并没有很好地展开。末章即第七章总论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提纲式的,点到为止。著者在《后记》里写道:“人物传记基本上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的,它不允许驰骋想象。写《司马迁》也只能根据这点资料说话。空白的地方只好让它空白。”这是他的传记观。
六、读托尔斯泰《复活》。封面人物是围着白头巾、斜睨着两眼的玛丝洛娃。我却认为不论从人物在全书篇幅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刻画的深刻程度,第一主人公不是玛丝洛娃,而是聂赫留朵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