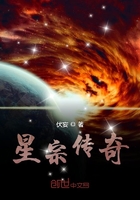一故乡新路
龙城下了一场薄薄的雪,虽然薄薄的却寒冷异常,我揉揉冻得生疼的耳朵,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着。各个商铺张罗着挂红灯贴对联,时不时传来零星的鞭炮声,空气中弥散着浓浓的年味。我肚子饿极了,走进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老板娘迎出来说:“对不起,大师傅回家过年了。”我苦笑一下,无可奈何地又走出来,这已经是第六家了。实在没办法,只好到一家小门市里,买了几包方便面,准备回旅店去冲泡。
“过大年,响大炮,爷爷扶着奶奶尿,奶奶尿得刷刷刷,爷爷笑得哈哈哈……”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疯子嘟囔着熟悉的儿歌,从我身边寒飕飕地经过。我不由得心里一颤,何其相似的心情,何其相似的背影啊?此刻在车站在路上,到处是匆匆归家的步履。而我只是有遥望家乡的渴盼。
“我还有脸回家吗?”目光越过楼群,望着关城方向的天空,我不停地追问自己。
“喂,小心些!”一个老头猛地拉我一把,我差一点就撞到停在路边的一辆桑塔纳车上。
朔风扑面,我脸似刀割,心如刀绞,在一滴滴滴血。自我落魄以来,不光是我对过年恐惧,所有的家人都恐惧,过年成了一道可怕的门槛……
一辆出租车缓缓驶过,在前边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两个年轻人有说有笑地拎着大包小包下来。就在车门关上的一刻,我仿佛听到了一声召唤,不由得心头一热,飞快地跑了过去,一把拉开车门。
“我去关城!”我急切地说。
“那么远的路,又下了雪,你还是找别人吧。”司机没有出远门的意思。
“我多给你钱,三百行不?”
“大过年的,三百有点少,五百吧。”
“五百就五百。”
我摸摸口袋,仅有两百,便要司机等一会儿,去附近的自动取款机取了一千元。一路上,我的脸一直冲着外边,司机也不多跟我说些什么,一个半小时的行程过去了,前方出现了关城陈旧的轮廓,熟悉的场景与乡音在心中升起。到了关城的大街上,路过一个五金店时,我让司机停下来,去买了一把冰亮的斧头。司机看着吓了一跳,恐惧与疑问写在脸上,你不会跑到这里来是杀人吧?到了一个热闹的街口处,司机突然停下车说:“哥们,就到这儿吧,我赶回家还有事,钱,你看着给就是了。”
我面无表情地“哦”了一声,看着手里冰亮的斧头,接着扑哧一声笑道:“那哪能呢,说多少就多少。”我丢下五百元下了车,拎着斧头无比郁闷地站在街边,许多视线都朝着我凑过来,马上醒悟到这样会被人误会的,得赶紧离开这里。
我步行在关城郊外灰蒙蒙的乡间,冬天的原野一派悲天悯人。在一只乌鸦的注目下,我来到离城二十里的馒头山前,凝望着山上蜿蜒残破的长城,想起小时候和玩伴经常在城墙上,对着下面的大好河山撒尿的壮举,想起撒尿处还留有我写下的“我来也”的字迹,一股热流不禁奔涌胸际。
“馒头山,我来也,今天陪你一起过年!”我大声叫喊着,爬上馒头山裸露在风中的岩石。在山顶的烽火台上,我看着腿上被荆棘划破的血口子,如一只受伤的狼悲悯而又狂奋。我挥挥手中的斧头,仰天大声朗诵起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夜色笼罩了古长城,我用斧头砍下一抱柴火,在烽火台碉楼里燃起一堆篝火。我一边烘烤着熊熊的篝火,一边透过碉楼的[]望口,目光极尽地眺着远处的关城,但是什么也眺望不到,只有连绵不绝的鞭炮声远远传来。寒风穿过碉楼门洞呼啸而过,一种旷古的悲凉侵彻五脏六腑。我想起了此刻团坐在桌旁的亲人,父母妻儿兄妹杜心,可我却无颜去同他们团聚。他们会想我吗?我值得他们想吗?我顿时神情恍惚,面对家的方向“扑通”跪下:“爸爸,妈妈,儿不孝啊!”
这一夜,馒头山不寂寞,长城不寂寞,关城也不寂寞,因为情绪疯狂的我,在大声为它们吟诵《孙子兵法》《行路难》《长恨歌》,吟诵了一篇接着一篇,就像一个鬼神附身的疯子。轰轰烈烈,忘乎所以,“我与圣者有何不同?”“天地为大,不薄微小”“我立天地间,有天为朋,有地做伴,何孤之有?”
在激昂中,我拿出手机来,开始狂发短信:“值此春节来临之际,我谨向您表达诚挚的谢意,感谢多年来的支持和帮助,真心祝愿您和您的家人平安、幸福、如意!谢达。”一百多条短信发出去,等着自己真诚的祝愿,如夜幕中闪亮的星辰一样,然后热切地等待着可能的回复。近半个小时窒息般的沉闷过去以后,手机的铃声一下令我心悸地响起:“你在哪里,兄弟?田亮。”
在除夕万家灯火,而苦守在长城碉楼里的我,收到了第一条挂记我的短信,读着短信,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兄弟这个词曾离我是那么遥远,我无比庄重地站起身来,再一次面对家的方向。很快,铃声又响起来,一声接着一声,就像整点报时,在告诉我春已来临,冬寒无惧。我一共收到十二条短信,虽比我发出去的少得多,但足以给我信心与力量,不再自卑与逃避,我毫不犹豫地离开碉楼,走下黑暗中沉默的长城,投向灯火与鞭炮声温暖的世界。
从下午开始,父亲就长立于案前奋笔疾书,一张饱尝浓墨的宣纸是他的世界,可以忘忧,可以解愁。母亲在一旁观看良久,然后叹了口气,起身缓缓离开了。她的糖尿病愈厉害了,浑身总是发软,有深深的困倦感。自从我出事后,她一直处于强打精神的状态,小儿子的变故对她打击太大了。我本是她心头的一盏灯,如今却成了心底黑暗的痛!让她恨铁不成钢,让她牵肠挂肚。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吃得怎么样?喝得怎么样?她想知道又怕知道。她支撑着病体忙碌了一个下午,把备好的鸡肉、香菇、土豆、干豆角切碎,炒成鲜香味美的调料,把和好的荞面擀开,先切成面条似的长条,再把长条切成小方粒,最后用大拇指挨个儿推成猫耳朵。我从小就喜欢吃荞面猫耳朵,她这顿饭是专门给小儿子做的。
可他会回来吗?虽然几年来一直没有音讯,但偶尔她也会听到姐姐说起我在外边的一些情况。只要一听到我的情况,她就会激动起来,就会不自觉地摇头:“不要提他,不要提他……”心里越渴望知晓,嘴上就越倔强。
此刻,她脑子里全是我,幼时的淘气,童年的聪颖,长大后的孝顺,渐渐地我的眉目变模糊了,像玻璃上雾着的一层,郁结着的一层。她不想这样,想一切清晰起来,可是徒劳。
“收拾了吧,他不会回来的。”一天未吃一口的父亲,停下了疾书的笔说。街上的鞭炮声渐渐零落稀疏。母亲满是失望满是不甘,望着父亲消瘦的背影,叹了口气,她一天也没动一下筷子。
除夕凌晨,母亲听到了敲门声,她从睡梦中醒来,脑海里浮过一个念头,但很快就被自己否定了。尽管很想是儿子,但她又有些疑惑,毕竟都凌晨了。敲门声在持续。她缓缓地起床出屋,走到院问:“谁啊?”好像没有人回应。仔细听,敲门声依旧在清晰地持续。她开门,看到门口默然立着的我,惊愕地摇晃,继而爆发出悲喜交加的呜咽。
“老婆子,哭什么呢?”父亲也披衣出来,看见相持在门口的母子俩,一时间眼直了,接着大声说:“不嫌冷,尽管站着干什么,卖冻肉啊?”我望着口寒心热的父亲,跪下:“爸爸,不孝儿子回来看您了。”
“我死不了。”父亲摇头大步回屋,母亲把我的手拉起来往屋里走。我边走边说:“妈,我饿了,给我弄点儿吃的吧。”母亲擦泪说:“好,好。”把儿子拉进门后,倒了杯热水,就直奔厨房。父亲又进了书房,拿起了笔,想要写点什么,脑子里却杂乱无章,随手写了三个字:“不成器”,又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没再理我,自顾自睡去了。
正月初一,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接到我的拜年电话,让他们的年过得颇有些“滋味”了。许多亲戚朋友都不愿意我再一次打扰他们的生活,尽管没有提及一句关于借钱的事,但大都一致认为迟早会的,甚至有些人开始打哈哈了。跟我说,马上要去海南旅游,全家人都去,怕我会在某一天登他们的门。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是需要他们的帮助,但不会为难他们,现在我要做的,只是告诉他们我还活着。
我有了本钱,却没有好的项目,在人际关系中寻找财路,是我下一步最重要的事。在打第一个电话之前,我颇有些提心吊胆,选择了几个心中想起就温暖的人,最终硬着头皮拨通了姐姐家的号码。
早晨起来吃过饭,姐姐觉得自己的眼皮不停地跳,问姐夫:“右眼皮跳什么意思?”
姐夫犹豫一下:“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好。”
“那左右眼都在跳呢?”
“好坏参半,无所谓好,也无谓坏。”
姐姐“哦”了一声,不再理会眼睛跳的事。今天,她打算先去给公公婆婆拜个年,正要出门听见电话响了,是我打来的电话,直觉告诉她我遇到困难:“你有什么事情?跟我直说,我们一起想办法,但不能麻烦别人。需要钱吗?多少?你说个数。”
“我不是借钱,是想找个项目。”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我还没想好。”
“我先帮你问问,回头跟你姐夫商量商量。”
我接着给哥哥打电话,听了我的打算后,哥哥却跟我说:“你的问题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不是项目的问题,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人要靠本事和本分起家,一个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愿意做他自己。”对于哥哥的意思,我表示了理解,同时告诉哥哥,我会本分做人。哥哥说:“那就好。”他不是商人,不知道从哪个角度才能帮上我的忙,但我并不气馁,这在意料之中。一上午的电话,赔尽了小心,笑抽了脸,全关城的人都知道赌鬼谢达回来了。
从供电局长位置掉下来之后,我突然有了非同一般的亲和力,加之能言善辩,无论国家大事还是家长里短,都说得头头是道,再加上我冒死赌博的传奇经历,邻居们都想和我多聊几句。我脑海里迅速分析着刚问到的资讯,邻居王大爷家二小子的媳妇在东北一家厂子里做各种工作服,作为库管的二小子媳妇能搞到最优惠的价格,还会送货上门,二小子媳妇很热心地为我介绍了自己厂子的所有产品。听着听着,我想到了自己在电业系统的关系,想到了电业局的农电工,大部分活儿是农电工干的,但待遇却与正式工有很大差别。在他们心中有个很大的愿望,那就是穿上正式工穿的那种工作服,而事实上上头并没有统一配发,克隆正式工工作服,绝对是好点子!我眼前一亮,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二初战告捷
打雷了,打雷声让我很恼怒,因为雨大我就不能去送货,我心情起伏不定,喜怒无常,有一种遇佛杀佛、遇神杀神的感觉。
春节一过我就没闲着,先是掏腰包报销了二小子跟他媳妇的路费,让两位原本打算舒舒服服过满正月的小夫妻早早回东北,拿回服装样品。我每天去串门,从过去的同事到过去的领导,一个月开个面包车跑完全省一百多个县。总价不高,单位又有这种需求,领导看我很诚恳,给了一些单子,有的给了一个许诺。成绩是明显的,一切都往我设想中靠拢,虽然这段时间里磨破嘴皮子磨破鞋底子,但毕竟看到希望。
有时候面对投在自己身上的异样目光,我难以承受,自己以前还是供电局局长,现在在门卫面前都得满脸堆笑。但我明白,自己必须扛下来!凤凰落架不如鸡,为了打消父母亲戚的顾虑,为了活命,为了站立,我必须承受一切,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家还能够相信我。
我把现有资金全部订了工作服,这次不是赌博,不是头脑发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回不再是单打独斗,有了合作伙伴田亮。
田亮非常讲义气,我们认识有二十年了。虽然认识很久了,但我们并没有多少交往,可谓淡之如水。以往田亮没有得到过我的帮助,就如杨文广一样,他也一直信得过我的人品,觉得我是个有魄力善于行动的人。他相信我异于常人的执著能使我反败为胜,他深信此刻我看起来非常落魄,但总有一天会成就一番事业。与杨文广不同,田亮没读过多少书,只开着一个小卖铺,卖着一些五金杂货挣钱糊口。他在大场合上帮不了我什么,但他认为小者虽微,却也能办大人物办不了的事。只要我需要,他就全力以赴,所以收到年夜短信的时候,第一个给我回复,欣喜地问候我。
正月初一,田亮从朋友那里听说我回来了,迫不及待地与我见了面。小葱拌豆腐,最好的搭配。两杯温酒下肚,田亮敞开心扉:“有什么项目,可以合作?兄弟我一直没什么办法,开个小买卖,也就十来万的本钱,不要嫌少。”我呵呵笑着,眼睛微微湿润,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有,一定算你一个,一分钱没有都行,只要有你这个人在。”田亮摇摇头:“我出钱出力,你出策。”那一夜的酒酣分手的时候,我感叹地吟了一句“长风当舒我怀,明月可照我心”,把田亮搞得莫名其妙。走了几步远,猛地回头说:“谢达,别嫌哥们没文化。”我仰天大笑:“要文化干吗,不也得吃喝拉撒?扒了那身皮,谁都一样。有文化当不了神仙,没文化也不一定成不了豪杰。人生在世,一切都是缘,随缘则定。”田亮很严肃地点点头:“不错,我认准了,跟你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