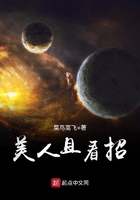这是一座很大的庄院,朱红色的大门有五级台阶,高大气派,门口两边,一对石狮子,狰狞恐怖。可是,没有看门的人,静悄悄的。透过围墙上的花窗,总算可以看见院子里闪烁的灯光。汪秀才心里盘算着,是不是上去敲门?自己衣衫褴褛,一副叫花子的模样,人家会开门吗?但是,不敲门,今夜里怎么过?总不能就在野地上睡,白白地让老虎、狼什么的刁了去。哎,敲吧,跟他没怨没仇,就是他不让进,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汪秀才登上台阶,轻轻地敲了敲门。敲了几下,“吱呀”的一声,门开了一道缝隙,一个老太婆从里面探出头来。汪秀才赶忙说明来意。老太婆听了,脸上露着十分为难的神色。
老太婆说:“真是不凑巧了,我家的男子都不在家,现在家中净是女流,让你住下来恐怕不便。”
“我就借宿一夜,天一亮我就走。”汪秀才说。
老太婆重新打量了他,觉得他斯斯文文的,像个读书人,就说:“好吧,看你无处安身,这里又经常有老虎在夜间出没,我老婆子就私自让你在这过夜,明天天亮以前得赶快离开,不要让我家的小姐知道,怪罪我。”
汪秀才大喜,跟了老太婆到了一间空房子里。老太婆抱来一条薄被,放下就走了。汪秀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躺倒在床上。窗外的月亮渐渐地照进一些光来,地板上缓缓地升腾起一层淡淡的雾气。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目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汪秀才不由得在心里吟诵起前朝人的诗来。这两个多月,东逃西窜,难得有读书吟诗的雅致。他想起了家,想起了妻子和儿子。他逃出来的时候,妻子把家中所的积蓄、十多两银子装在褡裢里交给了他。想到妻子平日间省食俭用,汪秀才的眼泪就悄悄地流出来。
他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糟了!他赶忙起身,正想往门外走。这时,昨晚的那个老太婆来了。汪秀才恭恭敬敬地站着,等着挨老太婆骂。出乎意料,老太婆和颜悦色,说:“先生,我家小姐有一件事相求,先生是否肯帮忙?”
“只要我能办得到,我一定效力。”
“我就知道先生侠心义胆,果然不错。”老太婆非常高兴,“我家小姐近来的夜里,总是梦到附近的城隍庙里那个黑判官,黑判官说,要娶我家小姐做妾。为了这件事,麻烦先生到那庙里,替为祷告。”
汪秀才一听,牛性子又上来了。凭什么死鬼要娶活人做妾?这还有王法了吗?他立即捋起袖子,破口大骂。“祷什么告?我去把庙里的泥像都推倒算了。”说着就要往外走。老太婆连忙拦住,劝他别急。一个丫环端了一大碗云吞面进来,放在他的面前。老太婆叫他吃了面,然后告诉他到那座城隍庙的路。汪秀才饥肠辘辘,二话没说就吞了这碗面。肚子饱了,底气更足了。
汪秀才出了门,这才看清了四周的景色。昨天因为天黑,加上心情惶急,只是看见这所大院子。院子四周,净是一些叶子稀疏的栗树,再没见到什么人家。院子的前门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牌坊上面有“青鉴山庄”四字。他照着老太婆的话,出了前门,穿过牌坊,朝东北走。他涉过一条小溪,果然看到一座城隍庙。
城隍庙飞檐琉璃,非常壮丽。这么高大的城隍庙,汪秀才还是第一次看到。庙门的一尊守门神,塑造得比人还高,青面獠牙,一手高举铁锤,好像随时会向人砸来。汪秀才心里有点发虚,真想就此溜了。但想到人家小姐,——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小姐——好端端地要受魔鬼折磨,他的心里就不忍。再说,这城隍爷充其量也是个泥鬼,总不会比邹知县厉害吧?这么一想,他就从守门神的铁锤底下钻了进去。
正殿上端坐着城隍爷,旁边站着那个握笔的判官。一看那个黑判官,他心里就不舒服。不过,他还是忍着,向城隍爷作了个揖,说:“城隍爷呀,我汪国真胆子小,但是胸中还有一点正义,您别瞪着眼睛吓唬我。您的懿德,万民景仰。可是,您手下的判官却无法无天,要娶我们活人,也就是前面那个庄子一户人家的女儿为妻。城隍爷呀,阴阳相隔,您说,这成个体统吗?我想,这件事您一定也还不知道。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揭发,免得您蒙在鼓里,损了您的光辉形象。这个黑判官,您要狠狠地整他一整。如果他还不改变他那个荒唐的想法,我汪国真就拼了这条小命,下一次来就推倒他的偶像,平了你们这庙。”
汪秀才说完,昂首挺胸地出了庙。他站在庙门前,向庄子的方向望了望,如释重负的叹了一口气。他想折回去告诉她们已经祷告过了,免得她们挂心,但转而一想,这么回去,只怕她们会疑心他汪国真是回去要报酬的哩。于是,他放开步子,朝前面的大路走。究竟要到哪里,他心里也没底,反正,有路就先走罢。
走了一阵,到了一个山口。前面几座高山,好不险峻。树林茂密,涧水潺潺。这山口能穿过去吗?他犹豫不定。这时,一阵尖细的嘨声响起,从密林中冲出一群山贼。汪秀才一见,双腿打颤,软在路上。喽啰们把这半死的汪秀才拖上了山,绑在一根柱子上。
汪秀才像在睡梦中,耳边模模糊糊地听得一个喽啰说:“大王,俺们下山,没遇上什么客商,只拿得一个牛子,就给大王醒酒吧。”
“好呀,现在就动手宰了吧。人心我好久没吃了。”一个声音嗡声嗡气的说。
立即有两个喽啰走了上来。一人一手握着明晃晃的牛耳尖刀,一手端着一大碗清水;另一个把汪秀才衣襟解开,然后双手紧紧地抓住秀才的胳膊。持刀的那个先喝了一大口清水,含着,用力地向秀才的胸口一喷。秀才一激灵,微微地张开了眼睛,看见明晃晃的尖刀正向他的胸口插来。
“哎呀——瞎眼鼠,你妈的,你的刀插在我的手腕上了。”
汪秀才看到抓他胳膊的那个喽啰正捂着冒血的手腕,叫瞎眼鼠的那个喽啰丢了尖刀,惊慌失措地站着。
坐在虎皮椅上的大王大怒,连骂“饭桶”,一脚踢翻椅子,走过来。他拾起地上的牛耳尖刀,一手按住汪秀才的胸部。刚要下手,突然,他感到肚子一阵疼痛。他弯下腰,捂着肚子,说;“哎呀,慢来,我先解手去,昨夜着了凉。你们好好看住。”
过了一顿饭的功夫,那大王才回来。他坐回虎皮椅里,喘了几口气。他歇足气力,重新操起刀,慢慢地走近汪秀才。这时,肚子又疼起来。他丢了刀,急急忙忙地又解手去了。怎么啦?我们大王拉肚子都拉上瘾了。喽啰们都捧腹大笑。
大王又回来了。这次他不急于宰人剜心,而是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地转动着他那双红眼珠——那双因为吃人吃多了而变红的眼珠。今天该不是撞上什么邪了吧?他细细地端详垂着头的汪秀才。这人中等身材,皮肤白皙,瘦瘦的,弱不禁风的样子。
“喂,小子,你打哪里来的?”大王问。
汪秀才没有反应。一个小喽啰上前,托起秀才的脑袋,喝道:“说呀,我们大王问你话呢。”
汪秀才朦朦胧胧的看到虎皮椅上的大王,满脸胡须,以为就是阎王爷了。连忙哭求:“阎王爷呀,我家中只有一妻一儿,儿子才一岁。没有我,她们母子难活下去。您就可怜可怜我,暂且放我回阳吧。”
“什么阎王爷呀,这是我们大王。你看清楚。”喽啰们大笑。
汪秀才眨了眨眼,确信自己还未死,立即忘了目前的处境,高兴起来。
大王用手摸了摸自家的脸,看着手下人大笑,脸立即红了。我真的长得跟阎王那么丑吗?他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仪表堂堂呢。他尽量把脸色放慈祥,压着嗓门说:“小子,我问你,你打哪儿来的?”
“大王,我从前面来的。”汪秀才想用手一举,但动不了,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还被绑着呢。“大王,您行行好,饶了我吧。”
“前面有一所大庄院,你看见吗?”
“看见,我还在那里住了一夜。”
“什么?你在那里住过?”
刚才吵吵闹闹的场面顿时鸦雀无声。每个喽啰都屏住气,凝视着汪秀才。汪秀才便把他投宿的经过说了一遍,他不明白他们为何对这件事这样感兴趣。
大王瞪着红眼,又问:“你看见庄院里有些什么人呢?”
汪秀才正想说,那里只有几个女的。但转而一想,这不是告诉他们可以到那里抢劫的吗?于是说:“啊!有好多人啦,还有很多兵马,数都数不清,八成那是个大官的庄院。”
喽啰们面面相觑。
大王慢慢地对眼前的这个文弱的人产生了好感。“我不杀你,你认得字吗?”
秀才听了,很不自在,便大声说:“怎么不认得?我还是个秀才呢。”
“太好了,我这里正缺少一位军师,你就留在这里。以后,迎送往来,请帖文书什么的,你给我写。”大王一边说一边吩咐喽啰给汪秀才松绑。
汪秀才一听,急了,连忙说:“大王,这万万使不得。打家劫舍的事我又做不来,你还是饶了我吧。天下能认字的人多得是,大王高抬贵手,莫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
“什么?”大王圆瞪红眼,怒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罢。来人,把这呆子带下去,好生看住。他哪天答应了,哪天就放了他。”
汪秀才被关在一间昏黑的屋子里,门外有两个小喽啰守着。汪秀才愁眉苦脸,心想命该如此。逃了邹知县,却逃不了山大王,到底还是要坐牢。
一眨眼,天就黑了。两个小喽啰送来饭菜,同时给了他一小断蜡烛,好言好语安慰了一番才出去。两个小喽啰关了牢门,就在门外边也喝起酒来。不一会,汪秀才听到两个小喽啰吵闹起来。汪秀才侧耳倾听,才知道是他俩喝醉了酒,正在发疯。
一个说:“你说我胆小是吧?”
一个说:“怎么不是呢?你舅舅被大王拿住,锁在这大牢里,还让你来看守。你有胆量就放他出来呀。”
“好,我这就去放了。大王也真是!什么人不好拿呢?偏偏拿我的舅舅。”
哐啷几声,门开了。一个小喽啰进来,满口酒气,咕噜着说:“舅舅,你走吧。我、我、我就不送您了。”
汪秀才傻了眼。嘿,我哪里有你这样一个外甥呀!他来不及想什么,夹起尾巴就逃。正担心不知道如何走,这时,黑暗中,一条大路慢慢地清晰,像一条带子在黑暗中飘动,伸向远方。他脚下生风,狂奔起来。他跑了大半夜,终于发现有了人家,灯光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他跌跌撞撞地登了几级石阶,敲门。“吱呀”一响,大门开了,出来一个老太婆。汪秀才一瞧,嘿,这不是那个老太婆吗?怎么跑来跑去,又绕回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