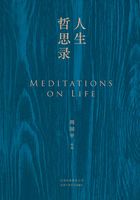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乎每个周末他都打电话来,聊得天地渐广,彼此的了解渐深,我越来越感觉到他的抑郁和那份出世的孤傲,只有在我的天真前,他才把矜持拿掉。我对这个说过几百句上千句话却没见过一面的人不再是好奇,而是有一种想抚慰他、陪伴他的冲动。很傻是不是?昭也这样说,与他的交流对于我越来越重要,有时上课中他的话也会在我脑海里冒出两句。他的人生观、社会观也深深地影响着涉世未深的我,一直到现在。越来越经常地,我望着楼前走来走去的同学们,猜想着究竟哪一个会是那个昭,心里默默勾画着他可能的样子,那样子却几乎一天一个样。我又悄悄地想,昭会不会时常想起我,想象我的样子呢?
那个初秋的夜晚对我是历久弥新的,就连最难让人记忆的气味那夜中弥漫着干巴巴的枯叶的香味,我也记得。那天一晚我都在等他的电话,可直到10点多同寝都准备睡觉了,电话也没来,正当我沮丧地决定进入睡觉预备级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定是昭!”我神经质地抓过话筒,却不说话。电话那边也是一片沉默,然后那个百听不厌的声音问道:“出去走走好吗?”好吗……好吗……好吗……他的声音似乎在我的胸腔中回响,我望望旁边镜中那个手握话筒的女孩,她双颊泛粉、眼波明亮,是的,她跃跃欲试,她不怕危险,“5分钟之后楼前见。”我说完就挂掉了,然后才想起我不认得他,我望望窗外仍然来来往往的人们,略一踌躇,不管了,出去再说。5分钟后我下了楼,身后还跟了个“小尾巴”同寝姐妹派出的间谍,她们怕我只身涉险。也对这个天天被我挂在嘴边的“昭”实在好奇。楼前的人不少,我的目光独独被一个瘦瘦高高、手指夹烟的人吸引住了,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昭。他背对着我,看了看表,转过身来。一阵风轻轻吹过,几片树叶悠悠地在昭的后面飘落,他似笑非笑地望着我,一双很锐利的眼睛,不过此时目光温柔,这一幕是我永远难忘的生命风景。我呆呆地望着他,心怦怦地跳得我以为全世界都听得见。他很帅,比我想象中的帅还有味道,我奇怪我以前为何从未见过他,如果见过我一定不会忘。沉默,似乎许久,然而也有可能是一瞬,他微笑着伸出手:“我是昭,你一定是宝宝。”我也笑了。就在两手相握的瞬间,我有想哭的冲动。我深知从此后这个头次见面的人定会升级为我生活的主角。他扔掉烟蒂,十分自然地把我的手握到他的另一只手里,说:“走吧。”
空气中落叶的香气使人踏实,路上行人渐稀,我居然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天气的确不错。我们走了很久也未说一句话。看得出他很开心,我则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我的手握在这个叫昭的男孩子手中,这是种多么神奇的感觉。夜是如此的沉默,夜是如此的温柔,我分明感觉到天地间一张情网就要将我罩住,然而此时此刻我终于知道大学中为何有这么多浪漫的爱情?
“知道吗,一开始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家乡的情况,没想到找个宝宝。”走到一片草坪,他拉着我席地而坐,开口说话了。我四周望望,“尾巴”不见了,大概跑回去发布特别新闻去了。“找哪个小尾巴?她们不放心我吗?”他带着点嘲笑的口气笑着说。我的脸一下红了。
“就是不放心你,你以为你真的让人放心啊?”我想抽出手示威,他却更快地拉过我的手放在他嘴上,一种柔软、轻柔的碰触,我触电了。他眼睛亮亮地看着我,说:“你真可爱,真是个宝宝。”我的世界颠覆了,我的世界又重建了。我的生活属于这个敏锐又细心温柔的男孩不,是男人了。他已大四了嘛快独立的男人了。
接下来的日子岂止是花前月下,从早上起床到晚上闭眼,我的每一分钟都叫昭。我渐渐了解他的忧虑来自前途不明,抑郁来自不得志,一切都源于他的孤傲不群。我不管,我只想用我的柔情将他缠绕抚慰,我只做给他开心什么都不懂的宝宝。他也说和我在一起时快乐得像在天堂,然后告诉我,他爱我,我爱他,那么我们在哪儿,哪儿都是天堂。
欢乐的时光总是飞得快极了,转眼要放假了,昭仍不回家,为他的工作奔忙。执手相望,泪眼相别。他依然用他迷死人的笑容安慰我:“只有两个月,笑一下,宝宝!”是啊,只有两个月,我带着泪笑了。
这两个月好难熬啊,昭的电话总是匆匆忙忙的,让我好无奈。然而如果我知道等待的结果,我宁愿永远甜蜜地无奈,也不愿回来。
昭来接站时我很吃惊于他的变化眼睛无神、言辞闪烁。一定出了什么事,再笨我也看得出来。我追问昭,他沉默地望着我,目光温柔得有些痛楚,却还有些坚决冷酷的我不能了解的东西。“你先休息一下,晚上再说。”他说话时特意表现出的距离击得我倒退一步,我一声不吭地走了。不管怎样,总会有答案的,是吧?
“拿到毕业证我就出国。”晚上,面对满桌菜肴,这是昭说的第一句话。我心里一疼,我只收到一个信息他会离开我。我只望着他,这久违了的黑黑的发、粗重的眉毛、挺括的鼻子,他的眼睛却不看我,仿佛在看好远、好远的一个地方,自顾自地一口气说:“我不能回去,不能回那个束人手脚的地方。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能帮我出国。”略一停顿,“你很可爱,我很喜欢你,真的,你的天真和美好让我觉得这世界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糟,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可是……你明白吗,宝宝?”“不要叫我宝宝!”我早已泪流满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说什么有我们的爱就是天堂,原来这天堂玲珑剔透却是玻璃做的,抵抗不了物欲横流的外界压力。”一个出国签证就将它击个粉碎,我的心早被这天堂的碎片割得鲜血淋漓,我早已看出他不惜伤害我一个付出全部真情的傻女孩,虽然他也痛苦,虽然他不敢看我。America的魅力无人能敌,就如没有女孩脱得开昭的诱惑。“她爱你吗?”我问,泪又一次滑落,昭点点头。“宝宝,其实我真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的目光霎时碰撞又分开,无论多傻的女孩在这样的时候也会聪明一点的。“再见!”我起身向外走,突然停步回过头来对木然的昭说:“永别了!”
我很想象电视中的大度女孩一样说句祝福的话,可我每吸一口气都觉得彻心彻肺的冰冷,每说一个字都强忍泪水痛楚得要死去。此时此刻我仍然坚信昭是爱我的,只是,只是我敌不过那个国旗上满是星星的美国。泪还在流着、流着,我喊不动呼不出,只有用这种方式宣泄。鸟儿在枪声中折羽,花蕾初绽就香消玉殒,正如我夭折的恋情。
多少个夜我愁肠百转,却不知到底该怨恨谁。
我不忍恨昭,甚至一点点的轻视都不忍,毕竟他是我最初爱过的人,然而这只会加深我的痛苦。恨那个女孩吗,是女孩谁能逃脱昭的魅力?何况她有资本竞争?强烈的愤怒、委屈过后,我深深地失落。原来我只知道现在的社会有许多人不可理喻,却没想到我身边的人也……崇洋、拜金、出国热,一浪又一浪,惧怕竞争,逃避艰苦打拼的人总是不惜血本走捷径,甚至不惜抛却生命的尊严和真挚的感情。昭错了,他一定错了。失去水分的干花和失去真情的生命即使存在、即便美丽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背水奋斗的勇气即使出了国,就真的会成就一番事业吗?大恸之后,我仍不明白,越来越聪明的人类为何苦苦追求金钱、权力和物质享受,难道他们不知道有个永远美好的精神家园爱才是永恒的吗?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难道真的成了一个遥远的童话吗?不,不会的,没有什么比情感的包袱更重,昭是我的伤痕,我却是他心上永远的十字架,我坚信我深爱的人会警醒,用真爱把这人间变成一个坚固的永不破碎的水晶天堂。
精品赏析
我很想象电视中的大度女孩一样说句祝福的话,可我每吸一口气都觉得彻心彻肺的冰冷,每说一个字都强忍泪水痛楚得要死去。
爱不流泪
贡·贡纳尔逊
父与子住在离小渔村不远的地方。他们在小渔村的外面买了一片陆岬,并自己动手盖起了两间茅草屋。
父与子相依为命,简直是一刻也不分离。父子两人都用同一个名字:斯乔弗。大家都管他们叫老斯乔弗和小斯乔弗。老斯乔弗50多岁,小斯乔弗刚满16岁。
老斯乔弗曾经很富有。那时,他拥有一个4英亩大的农场和一位贤惠的妻子,但13年前的一场天灾,夺去了一切。
在父子两人不多的交谈中,有一句话被再三再四地重复着。每次吃饭前,在做完祷告后老斯乔弗都会对儿子说:“付清一切债务,不欠任何人的情,上帝保佑!”
他们父子常常宁愿挨饿,也不到乡村商店去赊购任何食物。从小斯乔弗记事时开始,他们就不欠商店一分钱,而他们的邻居,家家都在商店里赊购东西。
小斯乔弗长得十分健壮,无论什么天气,他都可以和父亲一起划着自家的那条小渔船出海捕鱼。
有一年春天,在经过一个相当严寒的冬季之后,灾难再次降临到老斯乔弗的头上。一天清晨,一场雪崩掩埋了他们的茅屋,把他们父子两人都埋在了雪堆之下。
当人们赶来,把他们从雪堆中挖出来的时候,老斯乔弗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人们把老斯乔弗的遗体放在一块石板上。小斯乔弗站在父亲的遗体旁,轻轻地抚摩着老父亲花白的头发,喃喃自语,但是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不过,他始终都没有哭。
当人们陆续离开后,小斯乔弗来到海滩,寻找渔船。他看见那条小渔船已经支离破碎,片片船板在海水中漂荡。这时,他的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
如果小渔船没有坏,他还可以把渔船卖掉,因为父亲的丧事要花很多的钱,这一点他知道。老斯乔弗生前经常说,一个人总得准备足够的积蓄,用作体面的丧葬费用,用教区的钱办丧事是不光彩的。
小斯乔弗坐在父亲的遗体旁,陷入了苦苦的沉思。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他站起身来,径直朝乡村商店走去。他直接走进店里,以一个成年人的姿态问店主能不能和他谈谈。
“好吧,孩子!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店主问道。
小斯乔弗几乎就要丧失勇气了,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不紧不慢地说:“你当然知道,我家的码头,要比你的码头好,是吗?”
“有人曾这样跟我说过。”店主回答说。
“好,假如我同意,今年夏天,让你使用我家的码头,”小斯乔弗问,“你能给我多少钱?”
“我从你的手里把码头买下来,不是更好吗?”店主问。
“不,”这孩子回答,“假如我把码头卖掉,我就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
“可是,你的房子已经倒掉了呀!”
“今年夏天,我打算盖个茅屋,在这以前,我可以住在我刚刚搭起来的帐篷里。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渔船也没有了,所以今年夏天,我没法出海捕鱼了。因此,我想,夏天我可以把码头租给你,假如你愿意租下,给我租金的话。从我们的码头上,你们店里的人,无论什么天气,都可以外出。你不会忘记去年夏天,我们出海的时侯,你们店里的人常常不得不待在屋里吧?父亲曾告诉我,那是因为你们码头的地势要比我们的低。”
“一个夏天,你要多少钱?”店主问。
“只要够为我父亲办一个体面的丧事就行。这样我就不用花教区的钱了。”
店主站起来,向孩子伸出了手。
“就这样讲定了,”店主说,“我来为你父亲办理丧事,你用不着担心。”
交易谈妥了,可小斯乔弗仍站在原地未动。他还有没办完的事情呢。
“今年春天,你的货船什么时候靠码头?”小斯乔弗以先前那种镇定的口吻问。
“后天,或者明天。”店主回答。他的目光盯着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究竟想干什么,他有点儿捉摸不透。
“你需要再雇一个伙计吗?就像去年春天一样?”小斯乔弗坦率地问道。
“要,不过我要雇一个强壮的小伙计。”
店主说着,情不自禁地笑了笑。
“能请你出来一会儿吗?”小斯乔弗说。他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有力气。
店主摇摇头,笑笑,跟着这孩子从店里走出来。
小斯乔弗一句话也没说,走到一块大石头跟前,弯下腰,猛地举起了这块石头。
放下石头后,他转过身来,对店主说:“去年你雇的那个伙计举不动这块石头,我亲眼看见他试过好几次。”
店主笑笑,说:“如果你这样结实,我想,我是可以雇用你的。”
“你能像雇用别的伙计那样,供给膳食,给我同样的工钱吗?”
“可以。”
“太好了。这样我就不必靠救济生活了。”小斯乔弗如释重负。
小斯乔弗学着店主的样子,把手向店主伸过去。
“再见。”他说。
“请到店里去一下。”店主说。
店主走到前头,打开去厨房的门,让小斯乔弗进去,然后对厨娘说:“给这个小伙子拿点吃的来。”
但小斯乔弗坚决地摇了摇头。
“你不饿呀?”店主问。
“饿。”小伙子回答。他的声音有点颤抖,他早已是饥肠辘辘。但他挺直腰杆说:“那样一来,就该是施舍了,我绝不接受。”
店主想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小伙子跟前,拍了拍他的脑袋,向厨娘做了个手势,要她把饭菜端过来。
“客人来的时候,你一定见过你父亲招待客人喝杯酒,或者喝杯咖啡,是吗?”
“是的。”小斯乔弗回答。
“好,我没说错吧?我们得招待我们的客人,如果客人不接受,那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所以你瞧,你必须跟我一同用餐,因为你是我的客人。”
“那么,我想,我就必须吃饭了。”小伙子叹了口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