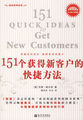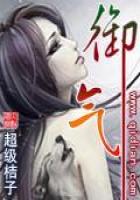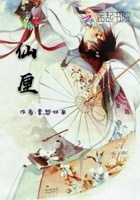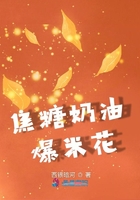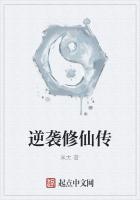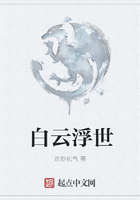4.2.2 银行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
银行作为债权人时,它和经营者一样是收益的固定求偿者,在风险决策时二者的态度可能一致。而且,在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债权没有经营决策权和对经理人的监督权,经营者很愿意与银行合作。而银行持股后,与银行的这些好处将部分消失,银行可直接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监督经营者的行为,并对之的道德风险行为即时采取措施,对经营者有威慑作用。这样,无疑增加了对经营者的约束,而可能受到经营者的不合作抵制。此外,银行作为股东与经营者存在收益方面的冲突。杨松(2004)[100]根据企业损益表角度,假定企业的总收入为I(扣除折旧),其中S为股东的报酬,C为债权人报酬,H为经理人报酬,W为工人报酬,P为外购原材料和劳务的固定合约支付额,T为政府税收,股东剩余收益为:S=I- P -W-H- C-T。一般地,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获取具有一定的固定合约支付特性,比如债权人的报酬C为合约约定的常量,员工报酬W因固定工资占有重要比重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固定支付。这时股东剩余索取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管理者报酬,存在此消彼涨的问题,即利益协调主要发生在股东利益与管理者利益之间。因而银行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存在收益方面的冲突。
4.2.3 银行股东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的冲突
银行持股后,增加了其自身利益的保护,但对其他债权人而言,可能会造成矛盾和冲突。第一,银行作为股东后,可以通过在公司派驻董事,代表股东利益决策时可以采取行动把损失转稼给其他债权人。第二,银行可以通过在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获取比其他债权人更多的信息,因而在公司破产前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甚至利用其债务优先对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失。在美国用降低债务优先级别等限制银行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银行可能期望保持其优先贷款人的地位而避免困境公司其他贷款人的诉讼,银行便有动机与公司保持距离型关系。第三,银行在决策时,可能偏向采取对其他债权人不利的风险决策。银行作为股东后,虽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但银行作为股东和债权人的双重身份,它只能根据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既不代表所有股东的利益,也不代表所有债权人的利益。由于股权和债权是不同的支付结构,股权追求高回报可以接受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决策,而作为获得固定回报的债权人将规避高风险投资项目,而是进行稳健投资。当银行股东的代表进入董事会后,在决策时,银行很可能接受其他债权人不愿接受的风险投资项目,对其他债权人利益形成潜在的损害。
4.3 银行持股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
银行持股后,对现有的股权结构将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机制称为银行持股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股权结构作为融资结构的一个层次对公司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股权结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公司的股份由哪些股东所持有;二是指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重有多大。前者说明股份持有者的特性,是法人股还是个人股,是内部管理者持股还是外部投资者持股,是股权结构质的体现;而后者则说明股权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是股权结构量的体现。因此银行作为股东后,不但改变股权结构质的规定,也将改变股权结构量的比例,进而影响对管理者的监督效率。
4.3.1 银行的机构股东性质
按照《金融与投资术语词典》的定义,“机构投资者是交易大宗证券的组织,例如共同投资基金、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工会基金、公司利润分享计划和大学捐赠基金。”银行持股后就成为机构投资股东,由于其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高,又存在规模报酬的特性,从而促使银行与其他机构投资股东一样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第一,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高,促使银行机构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股东所持股份较多,因而交易规模较大,这就使得交易成本因素比较突出,尤其是其中的市场执行成本⑨。[101]据估计,在美国等成熟资本市场,市场执行成本占总成本的60%-80%。中国股票市场大盘股价格呆滞,较活跃的大多是流通盘不大的股票,其执行成本只会高于成熟资本市场。高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将抑制着银行机构投资股东的投机性。另外,尽管机构投资股东能够进行多样化的投资用以分散风险,其分散的也只能是非系统性风险,整个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仍包含其中。一旦投资者信心不足,买涨不买跌的股市准则使得机构投资股东可能被“套牢”。因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股份较多,即使是股价的小幅下跌,其承受的损失也会较大,机构投资股东不容易抛出股票,这也促使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第二,参与公司治理的报酬规模性,促使银行机构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股东“套牢”之后,必然“开口说话”,即积极行动、参与公司治理。这种选择,是与治理所获的报酬规模性分不开的,可以从下述两个效应得到说明。
① 股数效应模型
假设银行只将其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购买A上市公司的股份,那么它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时所获得的每股增量收益函数为:
(4.1)
其中:P"和P——银行采取积极投资、参与管理方式的公司在治理前与治理后的每股市价;
C/S——银行采取以上积极方式时,每股所分担的平均治理成本,并假定C相对于金融中介所持股份数来说是一个常数;
S——银行所持有的该公司股份总数;
Y——银行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时所获得的每股增量收益。
从函数关系式4.1中可知,随着银行持有该公司股份数量S的增加,每股股份所分担的平均治理成本C/S越来越小,显然公司的每股增量收益Y越来越大,从而银行会更有动力参与公司治理。
② 公司数效应模型
假设银行将其有限的金融资源用于购买若干上市公司的股份,那么它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时所获得的总增量收益函数为:
(4.2)
其中: 和——银行采取积极投资、参与管理方式的公司在治理前与治理后所持有的第i种股票市价;
——银行采取积极参与治理第i家公司所付出的总治理成本,C"则表示因公司治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共享性而节约的总治理成本,并随着银行持有股份的公司数i的增加而不断地增加。因此,是银行采取为参与治理这i家公司所付出的净治理成本;
——银行所持有的第i种股票数量;
——银行积极地参与公司治理时所获得的总增量收益。
从函数关系式4.2中可知,随着银行持有股份公司数量i的增加,其所负担的净治理成本越来越小,显然参与治理的总增量收益越来越大,因而银行会更有动力参与公司治理。
4.3.2 银行是机构股东和债权人的统一
银行股东与其他股东最大的区别是:机构股东和债权人的统一。这使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转移到银行内部,多重角色使银行参与公司治理变得更为复杂。这也是很多学者对银行持股质疑的重要原因。作为机构股东和债权人的银行有时会在两种角色中处于冲突和矛盾的境地。因为股权和债权是不同的支付结构,股权追求高回报可以接受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决策,而作为获得固定回报的债权人将规避高风险投资项目,而是进行稳健投资。当银行股东的代表进入董事会后,在决策时将面临作为股东的信托人的信托责任与自己作为债权人的银行雇员的责任之间的冲突。这将给银行积极干预公司管理者带来了潜在的成本,特别是在公司处于财务困境时,矛盾和冲突更为明显。然而许多证据并不支持利益冲突的说法,而且认为银行持股是合理有效的。
① 银行是同一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
银行作为同一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可能引起潜在的利益冲突。这一潜在冲突是美国1933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修订的主原因之一。格拉斯-斯蒂格尔的辩词之一就是利益冲突的讨论,利益冲突可能对银行客户不利。然而,有的学者认为利益冲突可能存在,但不一定给其他投资者带来不利。Kroszner and Rajan (1994) [102]发现银行分支机构担保发行的证券优于由独立的投资银行担保发行的证券,认为潜在利益冲突是存在的,但得到了市场的纠正。Puri(1996) [102]认为在银行承兑的情况下,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和投资者遭受了银行潜在利益冲突之苦。Dietl(1998)[103]还认为,在一个全能银行的系统,即允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并存,全能银行渐渐地流行并排挤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说明银行持股与作为债权人双重身份没有利益冲突。
② 银行是不同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
如果一家银行是财务困境公司的债权人又是这家公司直接竞争对手的股东。这种情形可能引起两种问题。一方面,银行可能强迫公司破产,而从竞争者的股票收益获得正的收益。换句话说,他们在正常情况下会挽救的公司,而如果竞争对手的持股收益超过贷款损失,他们就可能强迫公司破产。许多证据表明,银行基于他们的评估正常要求公司破产,也被认为是利益冲突的表现,而可能被控告。如1999年11月德国第二大建筑公司菲利普·赫兹曼AG的重组事件。据报道该公司损失了约24亿德国马克(约12亿美元)。为了掩盖这一损失,避免破产,公司请求债权人重组债务。银行在只有联邦政府1亿德国马克的担保下,再对公司融资3亿德国马克来挽救公司这一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谈判的过程中,许多许多银行被指出企业阻止任何可能的协议,是因为赫兹曼破产似乎对他们更有利。在提到的银行中有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 AG)和德瑞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德国商业银行发现他自己暴露于公众监督之下,因为它既是储蓄银行(housebank)又是当时赫兹曼AG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豪赫蒂夫股份公司Hochtief AG 的股东。其他银行指控德国商业银行企图让赫兹曼AG破产,以便豪赫蒂夫股份公司在低价收购它,一项请求被德国商业银行和豪赫蒂夫股份公司两家驳回。德瑞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也拥有赫兹曼AG的两家竞争对手Dyckerhoff AG和Bilfinger berger AG的股票。Rauterkus, Andreas Heribert(2002) [104]以德国1990年~1999年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19个公众商业公司为样本(其中9家成功重组了其债务,10家被清算),研究表明银行作为股东并非导致显著的利益冲突。
4.3.3 银行持股对股权集中度的影响
银行持股份额较一般公众投资者多得多,是大股东之一,集中度高,对整个公司而言可以形成较集中的股权结构。就股权结构集中度而言,股权结构可包括三种股权结构形态:集中型股权结构,分散型股权结构和阶梯型股权结构。从目前银行持股的经验来看,一般形成的是阶梯型的股权结构。德国、日本银行持股都是如此。即股权相对集中于一定数量股东的手中,股权分布呈现从高到低的阶梯形态,即第一大股东拥有相对优势的股份,成为核心股东,其他股东地位依次下降。这种股权结构既相对集中又不至于形成垄断,既有一定的分散度,又不至于过度分散。各个股东以其持股水平为依据,决定其行使权利的努力程度,由于各股东持股差距适当,能够实现各股东适度参与,形成对大股东的权力制约。同时,在股票市场不发达,股权流动性差的情况下,股权相对集中,不仅可以提高股东直接监控公司经营的动力和效率,而且有利于保持企业经营发展的稳定和持续性。⑩[105]因此,银行持股后对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有积极意义。即通过形成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
4.4 银行持股与我国银行全能化经营
银行持股是关于我国金融系统改革,特别是关于拓展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今后业务应该思考的重要方面,或者面临的问题。杰拉德·克里根(2002)11认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不是选择何种模式,而是通过何种方法来实现这种模式。他说的这种模式就是综合经营的模式。本节在分析国际银行综合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历程以及制度背景,提出我国银行综合化的选择及制度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