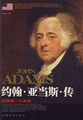“我父亲说:给她治病的钱都可以打一个金娃娃”
******的长女邓林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一出生就被寄养在农民家中,邓林自小身体就十分虚弱。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为了自己的健康成长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我出生于1941年,正是日本侵华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出生之后,因为父母要行军打仗,不可能带我,就把我送到一个贫农家抚养。那个贫农没吃没喝,所以我也没吃没喝。由于条件不好,营养严重缺乏,我身体很不好。到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太可怜了,就把我接回来,说那时候我脸上爬满了苍蝇,坐在椅子上都没有力气拿手赶苍蝇,特别可怜。
我回来的时候是1943年,因为战争还很艰苦,后来又把我送到延安去了,慢慢身体有点儿恢复。但是因为身体底子不好,我从2岁起嘴里就长肿瘤,还发过几次高烧,说不清是什么病。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就把我送到上海医院里做了切除肿瘤的手术。
1952年,父亲到中央任职,全家搬到北京。我因为从小身体不好,长大了就不断生病,父亲他们只要找到好医生,就想办法给我治病。我做过无数次手术,父母为此费了不少心。叔叔、阿姨们见了我都说,邓林可吃了不少苦。然后我父亲说:“给她治病的钱都可以打一个金娃娃。”
由于我身体不好,经常休学治病,耽误功课,父母对我未来的职业选择,也倾注了很多心血。50年代,革命是要报国,怎么才能报国呢?就是学科技,学理工。可是我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业。父母就根据我的特点,琢磨我今后怎样有个谋生的手段。我特别喜欢唱歌,他们就送我到音乐学院附中学理论。又因为我经常跟母亲说,看同学画国画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觉得我喜欢画画,就给我请了一个老师学国画,每星期去一次。结果我正业不怎么样,副业特别好,画画进步很快。母亲一看我画画还可以,又把我转到美院附中。这样既适应了我的身体条件,又充分发挥了我的特长。后来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成为一个画家,都是源于我父母为我所做的选择和安排。
“我唯一的罪状就是因为我父亲”
1967年8月,“**********”进入全面发动阶段,******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物开始遭到批判。******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但事实上已经被停止和剥夺了职权。随着“**********”愈演愈烈,******及其全家的处境变得愈加险恶。
“**********”的时候,我、朴方、****我们三个大点的孩子都被关起来了。我在学校被关了半年,我唯一的罪状就是因为我父亲。被关着的时候,造反派一天到晚就让我写揭发材料,揭发我父亲,可我哪有可写的?我们那时候都还是孩子,父母的事我们也不清楚,尤其是大的政治上的事我们更是不知道。万幸的是那时候我没有挨打,只是把我关起来,让我每天扫厕所。整个美术学院的女厕所都是我负责打扫。关起来之后也没有自由,就只能待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地板上都是臭虫,晚上睡觉要先抓一个小时臭虫,好不容易躺两分钟,臭虫又来了,你又得起来抓,咬得你没办法睡觉。这样关了我5个月,从8月初,一直关到12月底。那时候在牛棚里待着的时候,我有一阵子确实觉得非常难受。我这个人也不奢求政治上有多大的前途,但是那时候就感觉整个人生没有丝毫希望,觉得活下去真没意思,想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当时确实有过这种念头。但是我转念一想,就觉得不行,我不能死。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我死了,我弟弟妹妹的材料上就得写上他们的姐姐是叛党畏罪自杀。我一下子痛快了,可是我弟弟妹妹一辈子就得背着这个,他们这一辈子会多难过,所以我不能死。
“我觉得他们一下子老多了”
1969年10月,****“一号通令”下达,被隔离监禁在中南海家中两年的******和妻子卓琳将被转移至江西。经过批准,在河北宣化下乡劳动的长女邓林赶回家中为父母送行。
这是我们被赶出中南海两年之后第一次见面。因为一开始连里也没跟我说是什么事情,所以我从宣化回来的路上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下了火车就直奔中南海,西门的警卫跟我说你回家去吧,我才赶紧回家。结果一看父亲母亲都在,才明白让我回来是帮他们收拾行李,送他们。那时候,毛毛和飞飞已经下放到陕西和山西的农村插队,朴方正躺在医院里,楠楠也跟着北大的学生去了陕西劳动,他们都不可能回来,只有我独自面对即将远行的父亲母亲和奶奶。当然,到了家里看见父亲母亲,我特别高兴,也挺伤心的,我觉得他们一下子老多了,比我们1966年离开的时候老了很多。难以想象,在被监禁的这两年里他们是怎么度过的。
后来就让我们坐上了一辆吉普车,窗户上的帘子都被放了下来。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不想说话,因为都无话可说。从那时候我就离开了我的父亲母亲。我们那时候的离开和现在大家说爸爸妈妈再见了,不是一个感觉。那时候就是生离死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也不知道每个人的前途到底是什么。有人说,父母天生就是和子女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的感觉呢,不是这样,父母子女天生是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把我们分开,而这种分开甚至是各自不知道前路如何的。
“我父亲第一句话就说天气太热,要不要先洗个澡”
从1969年到1973年,******和卓琳在江西一共待了三年多的时间。这期间,在******的多次要求下,分散在各地的子女们得以来到江西与父母短暂相会。
我第一次去江西探亲是在1970年,那时候是夏天,天气特别热。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下了火车就跑到省革委去找人,是他们把我送到了我父亲住的地方。那时候第一次见到父亲母亲我是挺激动的,父母也很激动。因为他们对我们这些子女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根本不知道大家都怎么样了,所以父母对我们的状况特别关切。我一进家门,母亲就问我吃饭了没有,赶紧给我弄吃的。父亲第一句话就说天气太热,要不要先洗个澡。久别重逢后的见面,父母对我的关切,见面时的欣喜,真是无法言表,我当时也很感动。
其实那时候我妹妹毛毛写了一首词,她写的是“如塞外花开冰雪开”。因为那时候我妹妹在延安,所以她说“塞外花开冰雪开”,就是描述当时她去江西第一次见到父母时候的感觉。我曾经画过一幅画,叫《松青依旧》。“松青依旧”也是从毛毛的诗里截下来的。她去江西第一次见到父母,觉得父母就像青松,和以前是一样的,松青依旧。对于“**********”,说老实话摔跟头谁也不想,但是摔一个跟头,使得一个人对人生、对生活、对社会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都提升了一次。对于我父亲,他想的比我们要多得多。他想的是中国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中国必须走一条崭新的道路,必须国强民富。所以基于他对祖国的大爱,对人民的大爱,他不管个人安危,不管个人恩怨,最后走上改革开放这条路,他真的是非常英勇,非常顽强不屈的。
我第二次去江西探亲是秋天,那一次去的时间比较长,跟我父母一起住了差不多小半年。那是1972年底的时候,政治空气已经比较松一点儿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才开始互相照相。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跟我父亲照相属于具有反攻倒算性质,是在记“变天账”。有人问我说那时候你们家怎么不多照一点儿照片,就是因为不敢照,在那种政治氛围底下我们是不敢照照片的。但到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照相了,所以就有好多照片是我们跟父亲母亲在一起的。
“这些问题对我个人来说是大事,但对国家来说,是小而又小的事情。”
在“**********”中,谪居江西的******曾给中央写了数封信,除了申明有关的政治问题外,但凡有所要求每次都是为了他的孩子们。其中,为了邓林的工作和婚姻问题,******曾特意写信给中央,希望能得到妥善解决。
我父亲那时候找一切可以的机会,都要给毛主席写信,为我小弟弟飞飞、小妹妹毛毛上学的事情,为朴方治病的事情,为我的婚姻问题,他都要表达出他的愿望,给毛主席写信,希望中央能帮助解决他儿女们的问题。
这些方面都体现出我父母对于子女全心全意的爱,他会向中央去说每一个子女的难处,每一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像我因为从小身体条件不好,嘴又开过刀、做过手术,所以从婚姻角度看,我的优势非常少。尤其是“**********”以后,我的婚姻问题是老大难问题。我父母心里很着急,担心女儿嫁不出去。所以我父亲就给中央写信,特别提出来,希望中央能帮助解决我的工作和婚姻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个人来说是大事,但对国家来说,是小而又小的事情。但我父亲不顾忌其他,在自己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为此给毛主席写信。我后来听说了这件事当然非常感动,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父亲。像我弟弟、妹妹也是。因为我父亲很重视教育,他觉得孩子不能不上学,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小女儿小儿子能从农村回来,能有个学校读。我父亲对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事情,他都会倾注自己的心血去做。
我父亲平常也不说什么,不说什么豪言壮语,也不会说很温情的话。但是他个人的感情,你可以从他的一言一行,主要是从他的行动中感觉到,感觉到他作为父亲对子女的这种深沉的爱。他想尽办法来解决子女的问题,只要有可能,就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只要有一丝机会,他就会去努力。所以我们作为子女非常感谢我们的父母,感谢他们在自己也非常困难的时候,还能想着我们,想着为我们创造一个好的未来。
“我想要把和父母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珍贵时光都留下来”
1998年,邓林出版了自己的摄影集《******——女儿眼中的父亲》,其中收录了1980年至1993年这13年里邓林为父亲和家人拍摄的百余张照片,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女儿心中、眼中、镜头中的父亲。
父母和子女在一起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因为社会的变动,因为“**********”,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全家被迫好几次散落各地。所以当我们又得以重新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是非常珍贵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萌发了要给老爷子照相的想法。我想要把和父母在一起共同度过的珍贵时光都留下来,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很自觉地去找各种机会、抓住机会,给我父亲拍照。其实我父亲这个人他不爱照相,但有时候我们偷拍他他也发现不了。有好多人曾经问我这些照片里有没有他知道的,当然有他知道的,在这些照片里还有我主动设计的场面。其中我自己最满意的一张,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排排坐”。那一次是我陪老爷子在院子里散步,孙子们在旁边玩。我忽然间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如果让老爷子这么伟大的人物和孙子辈们一块儿坐在地上,和他以前的形象相比反差还是很鲜明的。我就是想从艺术角度追求这种反差。另外就是他和孩子们的关系,因为老爷子特别喜欢小孩,所以他和孩子们亲密无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情趣的。但是因为我知道老爷子不爱照相,所以特别紧张,就斗胆问他:“你能坐在那儿跟萌萌、羊羊照张相吗?”结果没想到他居然同意了,所以我特别高兴地给他们照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唯一的遗憾就是小孩的脚丫子没有照上,这是构图上很大的缺陷,但是我觉得那张照片是我自己主动设计完成的,对于我来说我是挺高兴的。
我父亲特别喜欢孩子,所以只要是和孩子们照相,他听任孩子们的摆布。我拍的有一张照片是羊羊和爷爷在一起。那时候羊羊要和爷爷照相,她就把自己的玩具小猴子也当作一个成员,让爷爷牵着小猴子的一只爪子,她自己牵着另一只,一起合影。这种时候,爷爷就很高兴地听任孙子们摆布。
冬天我父亲出门散步,不爱戴帽子,不爱戴围巾,下身只穿两条单裤:一条布衬裤,一条涤卡裤。上身一件衬衣、一件毛衣、一件中山装。有的时候天特别冷,他也就只添一件大衣。谁要劝他多穿一件衣服,他就会说没那个福气。
他很喜欢下雪,一看见大雪纷飞,他就会高兴地说:“今年的庄稼又该有个好收成了!”我相册里也有一张在大雪天拍的照片。那时候大概是11或12月,北京刚下了一场大雪。我们把院子里的雪扫掉以后,老爷子出来散步。刚好羊羊和萌萌也在外头,他们正在堆雪人,拿两个煤球当眼睛,插一根胡萝卜当鼻子,再把一个水桶扣在雪人头上当帽子,萌萌还在雪人的左右两边各插了一把木剑,弄得雪人威风凛凛。老爷子散步的时候看见了,就站在那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们。我赶忙就说,爷爷跟他们一块儿照张相吧。老爷子挺高兴的,所以就拍了那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