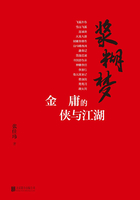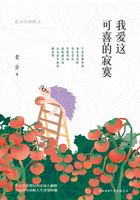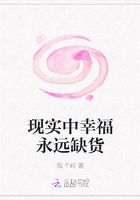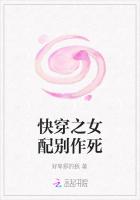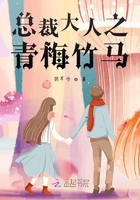红红的棺材停在屋中,鼓手歌师领着披麻执杖的孝子绕棺击鼓而歌,这便是屈原故里秭归的转丧鼓。
“天地开张啊,(是)日吉时良啊”,咚咚咚,匡咚咚,一阵急徐相间的鼓点和一串重重的锣音过后,歌手亮开嗓子嘹亮而悠长地唱这么一句,转丧鼓就这么开场了。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舞台,歌师、鼓手、亡者亲眷以及吊丧者共同表演着一场悲戚而精彩的祭奠戏。
转丧鼓之唱是富有魅力的,“开路歌”是转丧鼓的开场歌,唱罢开路歌,歌师便按照唱本娓娓唱来,或唱书,或唱杂歌、田歌、颂歌,或即兴作歌,就像一个民歌大联唱。唱法灵活多变,有歌师专唱,歌师领唱,客人轮唱,对唱和盘唱多种形式,唱腔也有高腔、平腔之分,长声、短声之别。
转丧鼓之高腔如喊号子,平腔如哭如诉,长声悠扬婉转,短声平稳急促。而和唱、轮唱、对唱、盘唱等唱法的不断变幻,又渲染出转丧鼓哀与乐,悲与欢相交融的氛围。和唱,称作帮腔,歌师唱两句,而前去吊丧的人就齐声重复一句;领唱,则是歌师唱一句,参加吊丧的人唱一句;对唱,是绕棺而歌的歌师与守灵中的一人或众人的对歌。
甲:姐儿住在对门包,
乙:郎吹笛子姐吹箫,
甲:郎吹笛子嘟起个嘴,
乙:姐吹箫来闪起个腰。
盘歌,则是一问一答,歌师以唱发问,或一人答唱或众人答唱。
正月里什么花人人所爱,什么人手挽手同下山来?
正月里迎春花人人所爱,梁山伯祝英台同下山来
……
转丧鼓就这样把单调的唱变幻得多姿多彩。
转丧鼓之鼓也有讲究,往往鼓锣相配。唱开路歌前,先打开场锣鼓,一夜转丧鼓结束时,打一通煞鼓,均有固定的乐谱。鼓点节奏急徐相间,急如骤雨,徐如慢步,在击法上,时而鼓面,时而鼓边。鼓手就利用节奏、力度和鼓的部位的变化,在小巧的腰鼓上击出无限美妙。除了开场鼓和煞鼓,鼓,可以说是唱的伴奏,唱的过渡,往往唱声完,乐声接,乐声落,唱声起,鼓声与唱声循环进行、交替交融。歌师所唱,一般是手抄或心记下来的唱本,很多是极富魅力的民歌,有些是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铺排,如《唱古人》、《杨家将》,这些历史人物故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形式传唱,不仅能带来人们欣赏民歌的美感,而且还有教化作用。而像《相伴亡者上九霄》、《劝哭歌》等,歌里表现出来的超脱的生死观,对生死的达观态度,既是对死者亲卷的慰藉,更表现出一种慷慨高昂的审美格调。
天理循环无差错,水流东海难回转。
善谋会算是诸葛,五丈原上把星落。
三国谋勇英雄多,年年征战动干戈。
至今存世无半个,个个都在睡山坡。
看来犹如水上波,大胆陪兄把歌唱。
相伴亡者上九霄。
而一些田歌、情歌的“插科”,却又增添了悲戚冷清的灵堂里的谐趣、热闹气氛,在悲哀中创造出一种欢快意味,这不是既可以化解亡者亲眷的哀情,又表现出一种喜在悲中的审美形态么?
屈原故里转丧鼓源远流长,是悠远楚风巴俗的流韵。《楚辞礼魂》这首送神曲里就有“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的景象的描绘,而在《东皇太一》这首记录楚国先民节日祭神的诗章里,更有“日吉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的句子,转丧鼓开路歌由此衍变而来。传说屈原镇一带原本时兴坐丧鼓,歌师坐在灵柩边击鼓而唱,因为屈原死后,故乡人民为他举办丧礼时,觉得坐着打丧鼓对屈原大夫不敬,于是改坐丧鼓为转丧鼓。
“人死众家丧,一打丧鼓二帮忙。”转丧鼓也是屈原故里淳厚民风的展示。无论哪一家死了人,乡邻都要前去吊丧、助丧,有的就以接唱歌师的唱句、帮腔,或单独唱几支歌作为祭礼,“打不起豆腐赶不起情,唱一个歌儿赶人情,唱得好来你们听,唱得不好陪亡人”(《唱个歌儿赶人情》)。转丧鼓流露出屈原故里的浓浓乡情。
屈原故里转丧鼓就这样在歌与乐的交融中,在歌师、鼓手和乡邻或庄或谐、或悲或喜的连续歌唱中,打发了悲戚冷清的长夜,让生者和死者在这特殊的丧吊活动中实现了生离死别之苦的超脱,人们也从中得到了一种民间艺术的审美愉悦。
199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