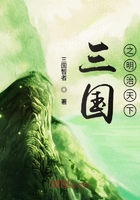吴有土靠在沙发上,父亲后边说的那句话,他没有告诉刘素素。莎莎长得细皮嫩肉的,眼睛又黑又亮,红唇皓齿,十个手指头都像姜芽似的,看那样子,连衣服都没自己洗过,完全是属于那种养尊处优的人。她都没受过风吹日晒,还会受过什么伤害?一个人长得跟老树根似的,这都跟他所受的磨难有关。农村的孩子,一边上学一边还得帮家里干活,很多孩子手上都带着伤巴,这里正在城市化,那些孩子都得带着伤巴进入城市。由于父亲,在他5岁时,就让他回到农村老家,他多少年就在农村呆着。吴有土是吃番薯长大的,莎莎是吃牛奶长大的。吴有土心里还有点不平衡,父亲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一句知冷知热的话。父母最疼老小,这可以理解,可你也别把莎莎宠得没样儿。
刘素素翻开一个电话本,在里边查一个个饭店酒家的电话。
刘素素拨电话:喂,是爱乐酒家吗?有没有一位从菲律宾来的描里莎小姐住到你们那去?
又拨一个电话:喂,是帝豪吗?住在你们那儿有一个菲律宾的描里莎小姐吗?
再拨一个电话:喂,是不是南苑?我找今天刚来的菲律宾的描里莎小姐,她有没有在你们那儿登记住宿?
刘素素也无可奈何地把电话放下了,自言自语:你这妹妹,真的也怪怪的,她要走也得跟你这个当哥的说一声啊!
描里莎带着王威廉去了书店又去了图书馆,她发现在在书店书架上有一排装帧精美的华侨名人的传记。在图书馆,她问管理员:你们这儿有没有关于华侨的书?
管理员说:有,你要哪一本?
描里莎说:我就先查一下书目。
没人知道她究竟在找什么书,反正,他们俩是两手空空回到他们住的饭店。
描里莎累了,她先洗澡。
描里莎穿着浴衣走了出来,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
王威廉说:莎,我觉得你好傻。
描里莎说:怎么,你喜欢我傻,傻得可爱?
王威廉说:NO,我是说,要是老这样,你可斗不过你哥,这回算是白回来了。你到书店,图书馆转什么?国内的书有什么好看的?值得你去翻它?你怎么不懂得轻重缓急?人家要拆你们家的祖屋了。
描里莎说:那我能怎样?
王威廉说:你太被动,你应该让你哥知道你的厉害,知道拆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得让他掂量掂量。
描里莎说:那我还能跟我哥打架?
王威廉说:你的脑子怎么不够用了?等拆掉了,你哭都来不及了。
描里莎说:没那么简单,惹急了,我把我老爸搬出来。
描里莎说着,把毛巾扔了过去,刚好就蒙在王威廉的脸上。王威廉跳起来就追描里莎,描里莎跑,一下就让王威廉挤到墙角了,描里莎挣出来要跳到床上,王威廉就势一扑,把她扑倒了。描里莎不再动换,王威廉搂着她亲。
第二天,吴有土到宾馆陪张鹄和庄紫玉喝早茶,他埋怨说:所有的宾馆饭店都不会做面线糊,面线糊只有街边上的好吃。我又不能领你们去街边上吃。
庄紫玉说:我可不怕。张先生是大人物,我是小小小小的。
张鹄打断她的话说:我总是自己半夜偷偷去吃。你们知道它味道为什么那么好?光大骨汤是不行的。我们总说味道好鲜,鲜字是一个鱼字旁,一个羊字旁,要用鱼虾和肉两种汤来调,虾和墨鱼都很提味。吃面线糊不加大肠头也差点事。
吴有土玩笑了:这么说,都可以开张记面线糊啦。
张鹄哈哈笑了:做饭是一门艺术,我是蛮有幸趣的。吴县长,你知道街边哪一摊的面线糊最好吃?不知道吧?我看,你县太爷敢不敢去吃?好,晚上我带你们去。
吃完早茶,吴有土说:车我都安排好了,兵分三路。我让办公室的小林和小李分别陪你们下去。我今天先不陪你们,我妹妹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得想办法找到她。
庄紫玉说:你不要着急,挺大的一个人,走不丢的。
张鹄说:她是个记者,没准也结交一些朋友,会不会让朋友给接走了?我这个人就主张放宽心。
吴有土说:我倒也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可我老爸那里我没法交代。我老婆也是个心里搁不住事的人,昨天着急了一宿。
一大片房子上都写着“拆”字,吴有土家的祖屋是写着“拆”字而又擦掉的,他就觉得显得有点扎眼,总有一些人在那儿指指点点地议论。
吴有土让司机把车开到他的祖屋门口,他下了车,拿着一把锁走向大门,这时他感觉他的后背上都是眼睛,他的耳朵也特别敏感。
仿佛有人说:这栋房子不是要拆吗?怎么又不拆了?
仿佛有人说:有个番仔婆到这儿来闹过。
仿佛有人说:错啦。那是吴副县长的祖屋,他不带头拆行吗?可真要拆,他这县长不白当了?于是,让番仔婆一闹,把一出戏做圆了。
吴有土不敢再听,他也不敢违逆他父亲的话,急匆匆的走过去,把那把锁给挂上了。他没有去看那两扇油漆斑驳的门,转身低头就直奔他的小车。
庄紫玉坐着的小车,开到一个村子边上。
庄紫玉说:就把车停在边上,这段路我要下来走一走。
小李陪着她。
小李说:村子里有了这水泥路,太棒了!
庄紫玉说:还是太乱,怎么能把沙子石头都堆到路上来呢?这车又不好走了。
房子旁边有些人蹲在那儿吃饭,他们一只手托两个碗,大碗里是番薯,也有米饭,小碗里是豆豉,熬点鱼肉也是有的。但他们还有这个习惯,端出来蹲在房子墙根那边吃饭,见庄紫玉走过来,有认识的也打一声招呼。有一个邋遢女人站在一段矮墙的后边,也往这边看,庄紫玉走过去,她突然跨过矮墙。
那女人冲庄紫玉大声喊:嘿!喊你呢!你不就是那个有钱的女人吗?你是女人,我也是女人,你干嘛非得算计到我头上来了?那女人一边气虎虎地喊着,一边就追了过来,你倒是停下来跟我说说呀!
小李回头看到那个女人,说:你想干什么?
那个女人说:我就想问问那个有钱的女人,她是女人,我也是女人,她怎么就不容我啦?
小李推了那个女人一把,说:有事你找村干部说去,别跟人家胡搅蛮缠。
那个女人站着不动了,小李招呼司机把车子开过来,让庄紫玉上车。
庄紫玉说:那个女人好厉害,我还真有点怕她呢!
小李问:都为什么?
庄紫玉说:就为铺这路,拆掉她两个猪圈,我一个猪圈赔她几百块钱,她钱也拿了,可见面还追我。以前我有防备,我来看这条路的时候,总拿把阳伞挡着我的脸,别让她认出我来。
小李说: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太对不起您了,捐钱修路,可好些乡里人太愚昧了。
庄紫玉说:这不算什么,我慢慢地也就习惯了。这是我住过的村子,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教过几十年书,我盼望它能够一天一天好起来。像她这么又喊又叫的人毕竟是少。我一看这村道,下雨天不再泥泞了,什么时候车都可以开进开出了。我心里就高兴了。
小李说:应该跟村干部说说,这也不能不管。
车往回开的时候,又经过那段矮墙,那个女人还站在那里。
那个女人还是喊:嘿!我说那个有钱的女人,你怎么就不敢下来?你拆了我的猪圈,我把猪养到屋顶上去呀!你是女人,我也是女人……
县政府送张鹄的车开到村口的时候,村子里开始放鞭炮了,有人一边放鞭炮一边给他领道。到祠堂门口,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者都出来迎他。
张鹄跟领他的一头头苍苍白发走进祠堂,所有人都站在他的后边。他抬头一看,大厅里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茶具和果品。桌子边上摆着几把电镀折叠椅,四周都摆着不刷油漆的高脚长条椅。张鹄知道,那电镀折叠椅是让他坐的,村子里的人敬重他。他坐了其中的一把,让其他人坐,所有人都自动地退到两边,坐到那些高脚长条椅上去,谁也不坐跟他一样的电镀折叠椅。他发现所有人都向他点头,向他笑,谁也不说话。有一个人在忙着沏茶,把第一杯茶用双手端着送到他跟前。他特别注意了那双手,手是那么粗,那么大,茶盅是那么小。他接过来喝了。于是那个人端走了茶盘,把一杯杯茶递给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者。茶喝过了,他们开始说话。
老者很客气:回来啦?
张鹄也客气:回来啦。
老者说:坐飞机?
张鹄说:坐飞机。
老者问:住宾馆?
张鹄说:住宾馆。
老者问:吃得惯?
张鹄说:吃得惯。
老者还问:睡得好?
张鹄说:睡得好。
所有的老者都笑了笑,张鹄向四面都点点头。终于有一个老者把一条长条椅往他身边拉了拉,坐到他跟前。
老者说:咱们村,咱们张姓出洋的算起来也有几位。老者慢慢地掰着手指头:可是,大粒的,大个的,就只有你一个。这当然是你的本事,全村人都很尊重你。而你呢?可也得记住,你吃的是咱祖宗的风水。得记住,你虽然是大粒的,你也姓张。咱姓张的到哪里都姓张,一个张字不能做两个字写。我和你父亲同辈同岁,属大龙。有用的人先走了,留下我这没用的人。我是老朽了。我的话呢,听,你就放在心里,不听,你让它从这耳朵进去从那耳朵出去。
张鹄不明白:我……
另一个老者说:你是个极有天份的人。他的话你听懂了吗?我把话说白了吧,你不是要回来办学校吗?咱姓张的胳膊不能往外拐。学校只能办在咱们村的地头上,不能办在别的村的地头上。否则,你就不算咱姓张的人。要不……他先张着没牙的嘴笑了:说句笑话,咱村里的狗都会咬你。
那天晚上,吴有土、张鹄、庄紫玉在宾馆会面时,三个人都有点垂头丧气。
庄紫玉关心地问:你妹妹呢?还没找到?
吴有土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些事都由我来解决。
隔天上午,那个邋遢女人还站在那矮墙的后边,东张西望。路的那一头出现两把小阳伞,两把阳伞从邋遢女人跟前过去,但从邋遢女人这边看不清那两个人的脸。有个女人远远地走过来了,邋遢女人一直盯着她,可到近处,邋遢女人认错了人,只好把脸转开了,反过来,那个陌生女人奇怪地看着邋遢女人。一会儿,那两个打阳伞的人又转回来了,可这回阳伞还是倾向这一边,邋遢女人还是看不清他们的脸。
到村口,吴有土副县长和庄紫玉把阳伞合上了,两个人上了车。
吴有土说:很对不起,我同样无能为力,让你这样来看你修的路。
庄紫玉说:别这么说,我觉得这样挺好。兴师动众,前呼后拥地我倒不习惯。说来可笑,自己修的路,跟自己养的孩子一样,老想再看看,亲自再走一走。
吴有土说:这是人之常情,可这还是乡下,人都理解你还得有个过程。
隔天下午,车开到赤土埔上,吴副县长和张鹄下了车,那片赤土埔离一个村子近离一个村子远。
张鹄说:远处的那个村子是我们村,近处这村子跟我们不是一个姓,这个村子姓李,这片赤土埔是他们村的。要是学校建在我们村边,得占用大片的耕地。可建在这片赤土埔上,村里的人却认为是建在别的村了。
吴有土说:这不也跟你们村挨着呢吗?房子一盖,其实都连起来了。
张鹄说:乡里人不这么想,只是说,是姓张还是姓李。
吴有土说:他们还会叫狗来咬你?
张鹄说:但他们心里会结一个死疙瘩,还有,他们还会没完没了地来找我。他们会让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当说客,把人说晕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