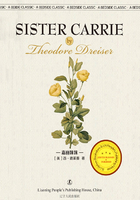杀头就留个碗大的疤。一苇发现,石头将军脖子上,那个疤让人家摸得挺光滑。她当然知道,不会有那根针,也没有那段红线。但她还是绕着他走了一圈,细细地在他的全身找个遍。她想找找有没有留下一个针扎的眼儿什么的,石头有些风化了,眼儿当然有,可哪一个是那个在户仔扎的呢?
一苇拿出她的照相机,她从几个角度选镜头,她得好好地照几张石头将军。后来,她又把镜头推近了,拍几个特写镜头。她推得很近很近,她是在拍那个针扎的眼儿吗?
一苇正照着,突然觉得后脖根冷冷的,回过头去,却看到那个老头。拉车老头,又黑又丑又老,他用两条阴冷的目光看着她。见她回过头来,老头浑身抖了一下,咧了咧嘴:“小姐,噢,我说人客,日头很毒咧,你不到这树荫底下躲一躲?”
一苇讨厌他那目光,只是回看他一眼,没答他的话。她还是绕着石头将军转:那石头将军被打掉头壳,还站着,他干么不倒下呢?只有像一苇这样调皮的女子才会提这样的问题,谁也不往这达想。但一苇却固执地想这个问题,认为他给人砍掉头壳就应该躺着,站着就不对,或者说站着还得有站着的原因。凭着他腰上别着一根针,就要判他死刑。那当然,他站了这么久,为什么没人想过为什么?也许他是在等一苇,知道到这一年这一月这一日,有一个番仔婆、一个在户仔会到这达来找他,于是有了机会,让她替他想这个为什么。人们向这个世界提出一百个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得到回答,其他九十九个问题,都被埋没了,埋没在人们自己的遗忘中了。如果有一个人去寻找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世界就会吓一大跳。石头将军显得矮墩墩的,他的头壳没有了,双脚又埋在溪沙里。
不知为什么,一苇一直没法拂去拉车老头刚刚从溪岸上,射来的那两条阴冷的目光,这叫她浑身不自在。现在她选取另一个角度重拍石头将军,石头将军背光的部分阴影更重了,日头更毒了,一苇的脸庞和胳膊都疼痛起来,但她没有马上离开。这时,她突然发现,从这个角度看,石头将军是倾的斜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站得那么稳。如果有一次更大的山洪,他也可能被冲倒。如果他在一苇来以前,就给冲倒,那么她也就不会再提这么个古怪的问题,就不会有人来寻找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所有的人都承认头一个问题的答案后边那个句号。
一苇终于爬到溪岸上来,躲到木麻黄下边的浓荫里边。从大海那边吹来的风轻轻地抚摸她刚刚被日头灼痛了的脸庞和手臂,她的胸脯起伏。在树荫下歇了一会,她的第一个感觉不是口渴,而是她必须去方便一下。可是她现在在一条小溪岸上,身边就一个拉车老头,离她好远是那几个洗衫裤的在户仔。
一苇不知该怎么办,对谁说呢?除了老头还有谁:“我得上厕所。”
老头像听人家说梦话,一个在户仔要办那种事,告诉他干什么?他也注意了她的那条拉链,番罗罗,可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他得告诉她厕所在哪达。可村子里,哪有她说的那种厕所,他给很多番客拉过车,没有一个肯去蹲村子里的屎坑。想了半天,突然想起,老榕树那边有一个带围墙的,就说:“那边有,我拉你去。”
一苇知道他要拉她上哪达。她摇了摇头。
老头可犯难了:“那,还得送你上镇上去,到侨联去?”
一苇指了指附近一片甘蔗林:“我上里边行不?”
老头犹豫了:“可是你还是个在户仔呢,你是小姐呢,懂不懂?”
一苇点了点头:“这没关系。不过,你得给我看着。”
老头的黑脸臊红了:“你那样……我给看着?”他四下里看了看,说:“那倒也行,可在我们这达,这事说出去不好听。当然,我老了倒也不怕,可这不是光彩的事,我可是要向你讨插花啦!”
一苇那张好看的脸这回又皱了一下:“插什么花?”
老头笑了:“这插花是闽南话,说让你听得懂那就是小费。”
一苇有点不耐烦了:“你要多少小费?”
老头慢吞吞地:“少的呢,给二角也行,要是大手面,有给八角的。”
一苇没理他,自己走到那边甘蔗林里边去了。不知为什么,她又想起了石头将军。当她离开他时,她发现他是倾斜的,他真的是个采花大盗吗?当她从甘蔗林钻出来时,拉车老头发现,她的嘴里含着一朵野花。
老头见她走上了溪岸,殷勤地说:“没有谁吓着你吧?”
一苇当时也许是有口无心,谁知道呢?她说:“有呀,就是他。”她指了指石头将军,他现在双手抱剑,剑尖杵着沙子。
老头的脸色突然难看起来,他掏出烟包,卷烟,有些烟沫子掉地上了:“在户仔人,莫做得这么乱散说。”早先很多在户仔都喜欢去摸摸石头将军,有的还去抱抱他。出事后,石头将军的头壳也掉了,就没有一个在户仔再去碰他了。今天,真是鬼使神差,他怎么把一个番仔婆给拉这达来呢?她怎么就对这石头将军感兴趣,没完没了地为一个无头将军照相?刚刚当她用手去摸那石头将军时,他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这到底是怎么啦?难道他让人砍了头还能显圣,还能勾在户仔的魂?要是那样,得往他身上泼黑狗血呢!黑狗血能镇那些妖孽鬼怪。但一般乡里人都不这么办,这招太损,它会使挨泼的鬼魂永世不得超生。这是乡里人的侧隐之心,可这番仔婆,她是怎么啦?站在那达还盯着他看,一个无头石将军有什么好看的呢?
一苇回头看老头,发现他仿佛一下缩小一圈,故意和他找话说:“刚刚那个,是你的某。那你的孩子呢?你有几个孩子?”
老头看看一苇,一个很水的在户仔,不要尽说一些无边无沿的,他愿意跟她拉家常:“就两个,头大的打捕,二的是个在户仔。”
一苇又故意往下问:“男孩多大,女孩多大?”
老头咂着烟:“大的十八,小的十七。”
一苇和老头的对话很成功,她原先想问他,他的某是不是原配,下边就是结发妻子哪达去了?但那不好问,她绕了一个大弯,现在又拐回来了:“那,看你的年龄,你结婚不早。”
老头只是笑笑,却不往下说了。他抬头看看天,又看看地,有几片乌阴在地上走:“我说,人客,咱这节上哪达去?”
一苇抬头看看天,云把日光吞噬了,吞了日头的白云镶着一圈银光闪闪的边儿。她站着不动:“不忙,我不要你跑很多路,其实我就在这附近走走。”
老头已经坐到车上,只好又下来。
一苇想从他的嘴里把话掏出来:“你们那节,结婚都早。”
老头摇了摇头:“穷。”他只说一个字,他想把话定在这达。
一苇还说:“像你这样的,有的都当了阿公(爷爷)了。”
老头的嘴给撬开了:“原先,我也可以当阿公了。可,某跟人跑了,那在户人生成不错,白净,好看不能吃。”老头莫名其妙地笑笑:“歹货。”
一苇像给烫了一下,她看看老头,老头脸上还挂着二十几年前的冷酷。
一苇把脸别开了,她不想跟他再说下去。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只会忏悔,把所有的过失揽到自己身上;一种人只会仇恨,把一切过失都推到别人身上。
二十几年前,其实是他以所谓“借”的方式,把她给典出去了。但他可以解释,当时房子倒塌,手头没钱,这就可以做理由。他不会反省,而后就都是她的不是,跟人把肚子弄大了,当然是歹货。逼得有人断指,弄得他没脸做人,只好出走,当然死是流言。他还活着,可她就这样跟人走了。他当然就可以恨她,恨她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她被“借”出去,她感到委屈,可她体谅他。他们的房子,那幢带蚝壳的土屋,让台风刮塌了一角。他把妻“借”出去,是迫于无奈,假事真办也是事出有因。办事那一天入洞房,番客不能自持,要来搂她。她就骗他,说她已经带身(怀孕)。这成了最好的防护,番客就没有动她。很快地,她就发现,自己是真的带身了,可是已经无法解释清楚。后来听说他出走了,想逃到番去,结果死在国境线上,她就只是哭,她还能干什么呢?再后来,番客的老母病故了,她是可以回到他的土屋去的,可是人去屋空,而那时她又是番客法律上的妻子。番客也是万般无奈,就把她带到菲律宾去。那时,她也有心要跟他,但到了菲律宾她就发现不可能,那里还有另一个她,两个人见面后如胶如漆。于是她陷入一种真正的困境,既不属于这个男人,也不属于那个男人,不属于这片国土,也不属于那片国土,这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的人生悲剧。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她有过委屈,有过怨恨,可她的心还在茫茫大海的那一边,心里铭刻的还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当她知道他还活着,她就只有自责,但她和所有的人一样,赶上一段无可奈何的岁月,有家难回,有国难奔。十八年后,她遇到她,她和她成了忘年交,她劝她换一种活法,但她不能。于是,有了这回替她回来寻找他的生活故事。但她一方面替她寻找他,一方面却认为这种人不值得寻找,一个连妻子都能典出去的男人还算什么男人呢,还那么老那么黑那么丑,而且一点儿责任心也没有。他二十几年来活得挺踏实,重新娶妻生子,至今还咒她是歹货。她是在寻找,但她早就认定她找不着,她找不着那个她心心念念的打捕。现在她更坚信,就是找到也不是,他不应该是,她只是想实现一下这个过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