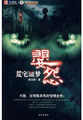“骚货!”那人冲我吼了一声。
“为什么这种事老让我碰上?”我问希尔弗曼医生。“我衣着简朴,出门都穿高领。我从不喷洒香水、佩带首饰,我的鞋子难看得要命,我所用的一切都破旧不堪。我甚至从不美甲,不仅头发分叉,脸上,就这儿,还长着痘痘。”我抬起下巴,指了指。“我这副样子已经和泼妇差不多了,怎么他们还来骚扰我。”
“你这种情况很好理解,你长得非常漂亮,可惜没钱没势。”
希尔弗曼医生耸了耸肩,看来无论他还是我对此都无能为力。
“如果你有钱,那就另当别论了。你出门不必挤公车,住的地方也更加安全高档。你想想,如果你穿得漂漂亮亮,贵气十足,男人自然就会认为你是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对你礼敬有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好像谁都能从你这儿揩点油。”
“你说的有道理!我这就去印钞票!”我怔怔地看着他说道。
“我只是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看得出来,你挣扎在社会底层,你的所有外在条件也告诉他们你软弱可欺,毫无防御能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这就让一小撮人视你为囊中猎物,可以任他们随便处置。话虽然不中听,但确是事实。这也是为什么上至名流富商、下至街头混混都会认为你比较容易得手的原因。虽然长得漂亮通常会让男人们望而却步,但因为你的贫困大大削弱了美貌的震慑力,这就让不自信的男人觉得有机可乘。”他点了点头,继而说道,“所以他们找上了你。”
他说我处境贫困。这话真让人尴尬,我不由羞愧地低下头。
“你应该知道自己长相出众,足以让许多男人自惭形秽,是吧?”
对,我知道。我抬起头,略带戒备地看着他。
“问题是,”我说,“这种事还不好跟人说。我不见得去问别人我该怎么办。要是跟人坦言我知道自己长得好看,那无疑就是在找骂,他们一定会对我更加刻薄。
我很快低下头。刚才说自己漂亮。他会怎么看我?他会不会嗤之以鼻,说我根本不漂亮,好让我有点自知之明?他会怪我虚荣、自恋吗?他应该不至于对我出言不逊,先不论钱多钱少,我毕竟付费给他,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话题总让我觉得不太自在。
不过,我还是抬头继续说道,“如果我说自己漂亮,那就是自以为是。可如果我装傻充愣,他们又会恨我故作姿态。这就好像你跟人抱怨说钱多得没地放一样让人讨厌。那我到底应该怎么说呢?长得好只会引火上身,而且还不能向人求助,也不能开口抱怨,我只好闭上嘴巴,默默承受。”
我垂着头。所有一切都让我厌倦。之前我从未向任何人谈论过我的相貌。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回应,只能等待着他泼来一盆凉水。
“我想,别人把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强加到了你的身上。”
“没错。在他们眼中,我不是蠢货就是恶魔。漂亮的女人要么愚蠢要么恶毒。”
希尔弗曼医生不无同情的摇了摇头。“你并不恶毒,更不傻。”
“还有,他们动不动就叫你贱货。你要么是愚蠢的贱货,要么就是恶毒的贱货。”这个话题一旦谈开了,也就不再让人感到局促不安,长久以来憋的一肚子苦水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这些人坏起来没个底。你若是遭人羞辱,不会有人替你做主,他们一心只想落井下石。而且,他们还全都认为自己心地善良,因为让漂亮女孩吃点苦头,在他们看来那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漂亮女孩出洋相。”我忍不住对着空气挥了一拳。“确实如此!他们以此为乐。如果你遇到了什么好事,那真是羡慕嫉妒恨齐上阵。有时,他们还要让你尝尝乐极生悲的滋味。这还不算,还有那些你永远也发现不了的背后使坏、恶意中伤。”
“你这番话要是让那些人听到了,他们一定会暴跳如雷,群起反击。”他并非向我证实,而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们可能还会列出种种理由,辩称他们的所作所为全都事出有因,证明你压根就是咎由自取。”
“我真搞不懂,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每个人还那么巴望天生丽质、容貌出众。一旦如愿,那他们岂不就成了污言秽语的受害者。”我叹了口气。“但是,不管是人们自认为有多善良,或是自认为对待别人有多友善,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没有人会对漂亮女孩怜香惜玉,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灾难降临,还是亲人辞世,一副好皮囊已是上苍对你最大的眷顾,足以抵消你一生中所有的不幸。因此,如果一个漂亮女孩遭遇不测,他们就会像打败了死敌那样欢天喜地。”
我拔着指甲边的肉刺。“我的长相的确让我得了些便宜,但那大多是些恭维话,让我更容易进出酒吧之类的场所。当我情绪失控,行为失当时,也可以帮我侥幸脱险。只要长得漂亮,没人在意我是否疯狂。但是,你知道的,其实我只希望我可以正常一点。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结交各种各样的男人,可弱水三千,我只想取一瓢饮。所以,长相无法弥补你所失去的东西。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如果好好利用这张脸,我想我可以得到更多:美貌可以当作对付其他女孩的武器,或是靠它傍个糖心爹地,或者把男人哄得团团转,让他们乖乖奉上昂贵的礼物,再或者索性钻到钱眼里嫁个大款,但是我希望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辛苦挣来的,是我理所应得的。我想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内心真正向往的东西。我没有必要打败其他女孩,这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成就感。我想要的,只是一个爱我和我爱的人,他眼里只有我,我心里也只有他。当然,我也渴望获得同性的友谊。
希尔弗曼医生飞快地做着记录,然后瞥了一眼手表。“也许换个地方,在那儿你的长相没那么扎眼,说不定你就能过的舒坦些。我不是随口说说。你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云集了俊男美女的环境,比方说当模特。如果你从事模特,也许就能如鱼得水。你并不缺少这样的机会,我说得不错吧?到那时,你身边尽是些和你姿色相当的女孩子,你不过是诸多漂亮女孩中的一个,而不再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光是在车厢坐着就会招蜂引蝶惹来一身麻烦。当然,做了模特,钱也就自然不成问题了。”
“我不能去当模特。”
“为什么不能?”
我看了他一眼。我们曾经好几次谈论过这个话题。我根本不想当模特,更不想参与那些你死我活的竞争。干这个行当可能会连着好几个礼拜都接不到活儿,我无法承受这种朝不保夕、患得患失的日子,因为在经济上我没有任何退路。而且,那些人还会当着你的面对你的缺陷说三道四、大肆批评,仿若你是一具没有感知的行尸走肉,至少我是这样听说的。而我,无论面对批评还是拒绝,都脆弱得不堪一击;遭遇任何一种都会让我抑郁到崩溃;双管齐下的话,那无疑就是在逼我自杀。我可不想自掘坟墓,自寻死路。
最重要的是,自由职业并不适合我。我需要明确的工作范围。我需要有安全感,需要有一股力量可以日复一日地催我从床上爬起来。我需要知道,我有份工作,有医疗保险。工作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即便工资微乎其微,少到只有做模特的六十分之一,但这份工作却是我赖以生存的全部。
“我不想当模特。我做不好。那些人会把我生吞活剥,我也不喜欢他们。”
“明白了。”
“那就别再提了。”
“好说。”
“你,还有那几个在密歇根大街上发名片的混混,都别再挑唆我去当模特。”
“他们是他们,我只能为自己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