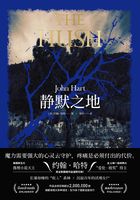“这周是外婆的事。她从监狱给我打来电话,除了我,她也没别的人可打,我只好去接她,顺便给她去送钱。”我瘫坐在椅子上,脑袋耷拉到胸前,无精打采,垂头丧气。
“但你不会开车啊。”希尔弗曼医生说。
“是啊,你不提醒我也知道。我是坐通勤列车去的那儿。而后我俩又乘坐同一趟列车回的家。‘相亲相爱’的祖孙俩。”
“她蹲监狱,是因为……”
“老太太在公车上多说了两句。”
“她说了些……”
“诅咒犹太人的话。她的癖好就是喜欢去墓地溜达,看看那儿有没有她什么熟人。如果别人先她而去,她那高兴劲就像是赢了全世界。这一次,她想去埃文斯顿墓地逛逛,看看哪些熟人又驾鹤西去了;在去的车上,她与坐在旁边的乘客闲聊,就是那时开始了诅咒。她随心所欲地将犹太人骂了够。”
我别有所指地顿了一下。“她坐的是途经德文和百老汇的车。”
希尔弗曼医生点了点头。
“你能够想象吗?从世界民族欢聚一堂的德文郡到铺天盖地全是外国人的百老汇,我亲爱的外婆这一路上都在诅咒犹太人?”我身体向前移动了下,注视着他的双眼,食指不住地敲打着额头。
他又一次点了点头。嘴角有点抽搐。
“你,应该可以想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车上有个犹太人——”
“不是一个,是他妈的一车,”我愤愤地说。“他们开始群殴我那六十三岁的外婆。把她打得鼻青脸肿,还有人说要告她。”
“谁先动的手?”
“当然是他们。反正我外婆是这么指天赌咒的。她说一群人追着她打。”
“那你觉得?”
“我告诉过她永远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永远不要。一点好处也没有。”
“你如何看待这件事?”希尔弗曼医生抹了一下嘴,像是要擦去一个已经成形的笑容,但他的眼神出卖了他,那笑意正生机勃勃地在那里打转。
“我觉得我是她一手拉扯大的。我觉得我遗传了她的全部基因。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更像样一点的榜样。”
我开始不住地抠扯椅子扶手上的衬布。“我怕哪一天我老了,也会和她一样不幸。”我抬起头来。“这个念头让我终日不得安宁。”
泪水夺眶而出,我心烦意乱,根本没有注意到他递给我的纸巾,只是用手背胡乱擦了擦眼睛。
我只觉得怒火中烧,想要杀人。为了控制自己,我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抠扯椅子扶手上的衬布。一根线被扯断了,我把它抻开,不停地拨弄、揉搓,又把手指套了进去。相信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能把整张椅子都拆成一堆碎片。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帮我成为一个正常人?”我转向他,两眼喷火,指责与埋怨写满一脸。“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们明知道外婆这个样子,还把我扔给她?为什么他们从不来看我?嗯?也从不打电话给我?甚至从没打个电话问声好?他们就这么把我扔给她,不管我的死活,任由我自生自灭。”
我愤愤不平,拳头一下接着一下砸在椅子扶手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没有一个人在乎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连一点点关心都不肯施舍?”
他没有吭声,静静等着,好让我尽情地发泄。
我扫了一眼钟表,意识到时间快到了。没有等他赶我,我便径直起身,头也不回,就这样甩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