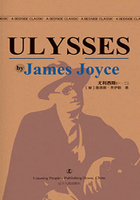在接触到涉及战争题材的诗歌以前,我先试译17世纪英国诗人理查德·勒弗莱斯的一首小诗在下面:
奔赴战场,告别露卡丝塔
亲爱的,别责怪我冷酷无情,
说我竟离弃了这座尼姑庵—
你贞洁的酥胸,宁静的心灵——
却拿起武器到疆场去效命。真的啊,我现在追求新的女性——
那战场上首次遇到的敌人。
我用更强烈的信念去拥抱
那宝剑,那骏马和那银盾。可是我这种模样用情不专,
你一定也同样地崇仰称赞。
亲爱的,我若是不更爱荣誉,
我哪能如此真诚地将你爱恋。这诗之所以感人至深,因为它说出了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一个普通战士告别爱人时英雄志胜过儿女情的心理状态,可谓泪痕血点结缀而成。这种心情在中外诗歌中都有广泛和普遍的表现。以西欧而论,这诗比较正统地继承了古希腊、罗马人的英雄主义。古希腊的斯巴达人素以忠勇卫国著称,连妇女都有尚武精神。斯巴达战士的母亲在送子出征时,要把盾牌交给儿子说:“提回来这面盾牌,否则就躺在它上面回家。”意思是说或者胜利了持盾归来,或者阵亡睡在盾上被抬回,总之是不能投降敌人的。
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征战频繁。恩格斯论及荷马时代的战争时说过:“古代一个部落反对另一部落的战争已开始蜕变为陆上和海上的有系统的掠夺,以期掳得家畜、奴隶、财宝,把这种战争变成正常的职业。”公元前12—前11世纪之交的特洛伊战争,生动地重现在荷马的《伊利亚特》长诗中,这是最早以战争为题材的诗作。荷马本人并未参与这场战争,也许由于时代久远,也许更由于作战双方都是希腊人的祖先,他对作战的双方似乎缺乏鲜明的敌我观念。希腊人或是特洛伊人谁胜谁负,并不是作者最关心的事情。双方战斗非常激烈时,诗人的态度超然观望,却诙谐风趣地叙述众天神把两方将领游戏般摆弄的故事。荷马史诗突出地歌颂了英雄主义。双方将领高大的形象和优良的品质才是作者浓墨重彩勾勒的对象。我们仿佛看到希腊的阿喀琉斯作战时的骁勇,对待朋友的真诚,使敌人丧胆的武艺和更难得的在战场上对敌人所施的人道主义;我们也仿佛见到特洛伊悲剧性的英雄赫克托耳保卫祖国的勇敢行动,也好像听到他诀别妻儿的悲壮言语,他那公而忘家、身先士卒的牺牲精神受到后入的敬重和推崇。古希腊人的民族素质和性格特征都写得表里相衬,恢宏深厚。在荷马笔下,勇武、道德、情操、忠贞等观念是至高无上的,不论对待作战哪一方面的将领,都应该用这样的尺度去衡量。
这样的英雄主义影响后世,多次反映在西方诗歌中。如中世纪法国的《罗兰之歌》里的罗兰就是一个典型的英雄形象。他和那些古希腊将领们有类似的道德品质:他誓忠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和“可爱的法兰西”,坚强不屈抵御侵略者,建立了功勋,可惜最后中了敌人奸计,在战场阵亡。他的形象的意义因对他死前的心理和行动的描写而比荷马史诗中的将领们更加深化了,我们试读:
罗兰感到死攫住全身,
寒冷从头上直透进心尖。
他急忙跑到一株青松下,
在一片草地上将身子卧倒。
把宝剑和号角藏在身下面,
掉头望着那异教的国土,
好让查理和他的大军
看见时夸赞死者的英勇:
“伯爵虽死仍不忘杀敌……”
于是他开始忏悔罪愆,
把手套伸向上帝祈祷!罗兰的号角本是准备吹起来向查理一世求援的,可是他太高傲自信了,没有想到敌人会耍阴谋,等他带的部队全被歼灭,他才吹号角求援,但已来不及了。罗兰心知必死,面朝着敌人西班牙的国土,思量许多往事,泪水滔滔,最后他捶捶胸膛,向上帝忏悔,然后躺在青松下,头枕着查理大帝赠送给他、又被敌人的血染红了的那柄宝剑,倒在草地上死去。这是一段多么可歌可泣的文字。敌我对峙,作者的爱憎分明,这一点颇有偏重。与荷马等量齐观地评价双方将领的态度不同。
再看俄罗斯古代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1185—1187)。这是一部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作品,它的内容常为俄国的文学、绘画和戏剧所采用。马克思于1856年3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论及这部史诗说:“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明显。”伊戈尔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在他的无比英勇。他率领亲属和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去征伐为克里米亚的突厥游牧民族——波洛维茨人所占领的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这是一次失败的远征,他被俘,最后他逃出波洛维茨人的囚禁,返回祖国。他虽然是个失败者,但他那勇敢的心是“用坚硬的钢铸成,是在无畏的大胆里炼成”。他与战士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般的融洽。“为保卫俄罗斯国家,他充满着战斗精神,率领起自己勇敢的队伍,奔向波洛维茨的国土。”作战前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诗中对于战场上的描写也极其雄壮苍凉:啊,俄罗斯的国土!
你已落在岗丘的那边了!幽暗的长夜降临了。
晚霞失去了光辉,
大雾遮没了原野。
夜莺的啼啭入睡了,
寒鸦的噪语已经苏醒。
俄罗斯人以红色的盾牌遮断了辽阔的原野,
为自己寻求荣誉,为王公寻求光荣。辽阔的大自然、宁寂的静态陪衬着战士们威武刚毅、奋然前行的动态,集中而凝练地渲染了临战的气氛,是一段精彩的激扬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