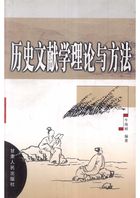日本占领广州后,我第一阶段的战地报道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我一到香港,合众社就把我解雇了。在香港,我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帮助她宣传并争取全世界支持中国的事业。
这个变动成为我一生中的分水岭。香港是英国100年前在鸦片战争中从中国夺得的一块“直辖殖民地”,它表面上显得很平静,不同于战火纷飞的中国内地。它的建筑物大多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冒出来的钢筋混凝土和大玻璃窗所形成的“丛林”。行政机关和金融机构的房子都是砖石结构,代表着不列颠老大帝国的威严和财力。但即使是这些建筑物也只有四五层高。
山坡上耸立着一座座供殖民地官员和中国富豪居住的孟加拉式平房,周围种着繁茂的亚热带植物,有高大的榕树,也有开红花的攀缘灌木丛。沿着港湾是主要的商业大街,使人恍如置身于伦敦。有许多狭窄的街道从这些商业大街辐射开来,那里挤满了小店铺,还有货郎和民间艺人沿街叫卖或做生意,像华南许多城市世世代代的景象一样。在这些繁华表象的后面是贫民窟和棚户区,那里是辛勤劳作的贫苦大众的栖息之地。
香港辖区内的居民95%是中国人,然而他们却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连外国人,甚至普通的英国人—如果不属于文官或军队系统,也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这里没有民选的机构,一切权威来自英国任命的总督。不过,这里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和许多战时难民)的政治倾向倒是反映了内地的民意。总之,香港的殖民地体制同中国内地的生死搏斗相互依存着。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香港是惟一剩下来的中国同外界联系的通道。
为什么合众社把我解雇,而不是派往别的地方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合众社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会逐渐消沉下来,所以它减少了派驻在中国战线的记者,而派驻在日本的记者则没有减少,它估计重要的新闻将出在那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日本的报纸是合众社在亚洲的主要订户。而且合众社远东的最高主管—东京分社经理迈尔斯·沃恩据说购买了大量日本债券。要裁员的话,还有谁比我更适合成为被裁对象呢?我“太亲华”了,不适宜在日本占领区工作。同时,解雇我代价比较小,因为我是在当地雇用的,没有订立雇用合同,所以我无权提出关于解雇费、遣返旅费以及美国本国雇员所享受的其他许多优惠的要求。
对我来说,同合众社分手实际上不是工作的终结而是工作的开始。因为宋庆龄很快就请我参加了设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我的任务是编辑它的英文出版物。虽然这是无报酬的义务工作,却成为我留在香港的主要因素。此后不久,我在当地的一家日报谋得一份差事,借以糊口。
为什么宋庆龄不在别处,而是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这是因为遭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内地受到了双重封锁。一重封锁是由于日本侵略者控制了海岸线。另一重正在发展的封锁是蒋介石政府禁止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供应物资,甚至医疗用品也不让供应,同时压制报道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种种胜利和成就。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打破这两种封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至于被不公正地剥夺通向外界并使外界听到它的声音的权利。而香港—当时仍能同世界大部分地区联系—则是发挥这一作用的最好“窗口”。宋庆龄跟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赴港并协助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其目的是加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宋庆龄是一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忠诚奉献的革命家。现在回想起来,应当说,宋庆龄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她深深认识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团结抗战并战胜侵略者,是首要的大事。没有这一点,就不能够实现孙中山的理想与事业,更谈不上继续前进和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团结起来,武装抗日,她的观点与此完全一致,并坚决支持这一主张。在整个抗日斗争中,她是一位热心和忠诚的积极分子,一个辉煌的标志。她无畏而不懈地参加民族救亡运动,对全国广大爱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她积极投入并领导了救国运动,并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努力争取国共团结共建民族大业。在她身上,坚定不移的原则精神同争取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是融为一体的。她一方面坚决反对反动势力与投降主义,一方面深切热爱爱国战士和人民群众。同时,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一起贯穿于宋庆龄的政治生活与活动之中。她帮助中国人民提高国际主义觉悟,并且帮助国外有识之士了解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与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性。在动员最广泛的国际人士支援中国人民进行奋斗的工作中,她孜孜不倦,不屈不挠。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在世界各地众多的社会阶层中广泛地结交朋友。她不仅朋友遍天下,而且开创了多种渠道,以利于运送物资来支援中国人民的斗争。更可贵的是,她从来不爱出头露面。她自己清醒地认识到并且提醒别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她总是想方设法,宣扬人民的最深切利益和他们的愿望。这是她在中国与世界的社会舆论中获得崇高威望的“秘密”之一。
宋庆龄由于她的经历、她的坚定的原则性和磁石般的个人魅力,不可替代地成为她在香港开创的这一事业的支柱和灵魂。她作为孙中山夫人、作为中国共和革命创始领袖的遗孀,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同样的,她以对中国团结进步的爱国事业的一贯忠诚、纯洁的思想、不受腐蚀的廉洁正直的品德而闻名于世。她的热诚使她能广交中外朋友并能团结不同观点的人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她堪称世界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同时,她又非常谦虚,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时一点也不感到拘束。
我们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人数不多,但却充满朝气。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我们大家把她当作慈母一般看待。30岁的廖承志作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驻香港的代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他成员都是二三十岁的人。我的年龄最小,刚过23岁。在宋庆龄和这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色各样的志愿人员,在她的威信的感召下,他们随时听从她的召唤。
保卫中国同盟和它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得到了国外的广泛赞助,特别是在它成立的头两年更是如此。宋庆龄请她的弟弟宋子文担任“保盟”的第一任会长。宋子文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是蒋介石的内弟。在美国,“援助中国委员会”是通过“保盟”送交捐款的,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是罗斯福总统的母亲。
宋庆龄处理同“保盟”同事们的关系,非常民主。虽然她是全国和全世界的名人,但她平等待人。不论什么工作,包括在办公室用打字机打信和救济物资的打包托运,她都跟大伙儿一起干。在她主持的会议上,大家不论在她发言之前还是之后,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是由于大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即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中国籍的成员把自己为祖国的生存而战看成是世界人民反压迫和反侵略斗争的一部分,而外国籍的成员则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援引一件小事,作为反映宋庆龄风度的一个插曲。事情虽小,但我觉得颇有意义,让我永志不忘。
在香港,我同唐纳德·艾伦同住一个小公寓。艾伦是一名教师,也是20多岁,他志愿为帮助“保盟”、“工合”和其他反法西斯事业做些事情。有一次,我们请宋庆龄来我们住处共进由我们亲自动手做的午餐,她欣然答应,我们高兴极了。但接着,我们慌张起来,因为我们发现没有桌布,于是只好临时用一条干净的床罩代替。席间,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论“保盟”和别的事情。饭后,她表示感谢,接着又逗趣地问道:“你们中间哪一位睡在这条床罩下面?告诉我,我才走。”我们在欢乐的笑声中送走了她。她这位世界名人、大无畏战士就是这样同年轻人有说有笑、和谐相处的。
在1939年至1940年,“保盟”的工作发展很快,它同国外的许多进步的援华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些援华组织是由同情中国的外国人和华侨组成的—对这些外国人和华侨来说,宋庆龄代表着原则和正义。捐款和救济物资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海员们也在他们的同伴中募集捐款,送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并把我们的宣传品成捆地带去散发。每一笔捐赠的现款和物资,不管数额大小,宋庆龄都在收据上签名。
那时向中国大陆运输物资还是有可能的。货车队和救护车是通过当时法国控制的越南进入中国的。敌后游击区的战地医院是按照白求恩大夫所定的模式建立的。经反法西斯的“国际和平运动”批准,这些医院被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为了照顾孤儿和父母上前线的儿童,建立了许多托儿所和幼儿园。“保盟”有关这些儿童的宣传,不是用伤感和怜悯的语调,而是充满健康向上的气势—必须帮助这些孩子成长为他们父辈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建设者。
在国民党地区的援助计划,包括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在国民党地区和共产党地区,都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活动。“工合”运动把工人(特别是来自敌占区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自主、自管、自养的生产单位,为许多地区生产日用必需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有的也生产军需品,如军毯。在游击区还生产一些武器。这些合作社是由一个国际团体组织的,其成员有中国的爱国人士和外国友人。在外国友人中,包括斯诺夫妇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斯诺夫妇为“工合”运动做了大量国际宣传工作。路易·艾黎则在基层进行了不倦的工作。宋庆龄赞扬合作社这种经济形式,认为它体现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因而同意担任在香港设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主持了它的许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