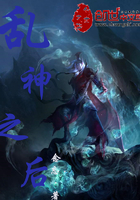现在回想起来,在日军登陆前后,广州群众的士气一直是高昂的。甚至在敌人进入广州一两天前,还举行了盛大的动员大会,高级官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事实上,跟听众不一样,这些官员正准备赶快溜之大吉,在城内或在周围地区已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人民群众一时陷入了混乱。后来,他们的爱国心主要表现在不愿意生活在日本的铁蹄下,纷纷离开了广州。他们的行动之迅速彻底,是我在别处没有见到过的。
后来,广州周围的武装抗日活动逐渐形成,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和相关的游击队。
在广州郊区没有从上而下照着模子组织起来的武装抗日活动,是由于当地军阀官员狼狈逃窜的结果。
在我写的《人民之战》一书中,对广州的陷落曾有这样的分析:
当中国向全世界显示了她的力量,而她的弱点几乎被遗忘的时候,另一个大城市像北平和天津一样,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就失守了。像北方的许多城市丧失一样,广州的迅速陷落也是由于国内分裂和对外妥协的时代留下的弱点所致。
不错,广东是采取了措施来组织和武装群众。根据官方数字,该省有30万人获得了枪支并接受了军训。可是,这支巨大的力量没有列入保卫华南的计划。为唤醒民众而热心进行的政治工作是很成功的,但却没有同抗击侵略者的战备工作有效地联系起来。结果,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该省薄弱的驻军无法保卫广州。民兵是有的,但没有人来指挥。广东当局动员了人民群众,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却把他们置之于脑后。不过,组织和训练群众的工作并非毫无意义,精力没有白费。这样的工作绝对不会是没有效果的。今天,民兵成了广东广泛开展的抗日游击活动的骨干力量。广东人民比他们的领导人更看重自己的力量,他们对自己的战斗力更有信心。
广州市的撤退工作安排得非常好,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的。几天之内,一座60万人的城市(正常人口是百万以上)就变成了一片砖瓦的废墟。据估计,日军进城的那一天(1938年10月21日),偌大的广州市顶多只有一万人。广州人宁愿离开自己的家园,也不愿向侵略者屈膝。在日本人占领几个月后,还没有迹象表明大批人将返回自己的家。这充分证明了广州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宁可过艰苦奋斗的生活,也不愿当亡国奴;他们坚信,日本人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战斗将继续下去。
从广州和武汉撤退后,中日战争的战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武汉过去一直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联系着北方、南方和西部诸省。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南京陷落后成了全国的军事、政治、贸易中心。而在武汉陷落后,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取代它的地位。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抗战,是摆在全国面前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南京和广州、武汉陷落之间的那段时间表明,正规战的优势在日本人方面的话,那么,它也表明,中国军队可以成功地打牵制战,有时还可以发动有效的反攻。中国战斗力量的主力仍然完整无损,而且由于充实以新武器和实施新的训练方法而得到加强。最重要的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到处发动游击战,证明他们有能力阻止日本人对任何已占领的省份实行有效的控制。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从实质上看来并没有被击溃,而游击运动对日本在占领区的控制又构成了严重挑战。内地的交通运输、工业生产以及同海外联系的新路线空前地发展起来。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战线虽然还不够十分强大,然而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要求继续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就是战争爆发15个月后中国向世界展现的图景,尽管她的一些大城市陷落了。
下面,我讲一讲当时我亲自观察到的广州市的某些情况,当然不可能很全面。
1938年10月27日至31日,我和美国自由投稿的摄影工作者雷伊·斯科特试图走出这个沦陷的城市前往香港,但是,未能成功,不得不返回。回到沙面英国租界内的旅馆后,我给合众社发了一条新闻稿。当时根据一项尚有效的协议,还能通过停泊在珠江口的美国军舰上的电台发送稿件。我在这篇稿件中写道:
我们在“无人区”过了四天,刚刚返回。我目睹了日军在一个荒芜的港口登陆的情况。接着来了三架日本飞机,追着我们轰炸了45分钟。我步行和乘船一共走了80英里。这使我有可能讲述一下广州沦陷后珠江三角洲的某些情况。
斯科特和我曾经试图经过一条小溪和小路出境,以便把首批关于日本占领情况的图片带出去。但是,日本人对三角洲的水路严密封锁,飞机不断进行侦察,还有武装舰艇巡逻,每个陆上据点都有上百人把守。
不过,他们对陆地的渗透并不很远。广州周围20英里的半径范围内实际上是无人地带,中国当局已经撤离,而日本人还没有占领。
在我们经过的十几个村庄中,人们都在热烈地讨论着两个问题:第一,日本人来了,怎么办;第二,如何对付蜂拥而来的难民。
距离广州不远的佛山郊区,布满一条一英里长街道的武装民兵把小股日军赶回了火车站。
解决难民问题的典型做法是:给他们一顿饭,把他们送走。
穿着蓝色制服的村自卫队员背着武装带,挎着步枪或手枪,检查来往行人和保卫家园。这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很有效率,但是,同外界完全隔绝,又缺乏协调。距离广州只有10英里的一些村庄的居民不相信日本人真的进了广州城。甚至那些在附近的佛山打退过日军的人也坚持认为,他们打退的只是打着日本旗帜的汉奸。
这个地区似乎没有中国军队。只是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分布很广的组织。那里有数十名沉默寡言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对我们的所见所闻很感兴趣,似乎在计划把农村地区分散的抗日力量组织起来并加以领导。但他们似乎也怀疑广州城是否那么快就已被日军占领,路过的难民都是在日军进城前逃出来的,所以也不能对此加以证实。
途中,日本飞机在我们租用的舢板船附近扔了几颗炸弹,他们似乎对任何移动的东西都疑神疑鬼。有一次,日本的巡逻艇在离我们只有10码远的地方开过,没有发现在草席船棚下蹲着的我们这两个外国人。
我们随身带着两支白朗宁45式手枪,这是美国军舰在斯科特的请求下借给我们的防身用品。如果我们想用这些武器对付日本人,那我们就该倒霉了。
最后,由于困难重重,我们不得不溜回广州,在沙面英国租界内的维多利亚饭店这个安全避难所栖身。从那里,我作为旅客登上了美孚石油公司的汽艇前往香港。
我随身带了两个大洋铁桶,里面装着在广州出版的全套《救亡日报》,这是报社编辑托付给我的,他们也到香港后,我就送还给了他们。这就是我对广州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次效劳。
说到广州沦陷前十分高涨的群众爱国热情时,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宋庆龄的两次广州之行,因为她不仅使全城受到鼓舞,而且我同她的会见成为我自己以后整个生涯和活动的分水岭。
我在广州停留期间,具有高度原则性、受人尊敬而气质高贵、风度优雅的宋庆龄两次来到广州。她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遗孀。她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亲临广州,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她在中国的两个重要时期都曾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过。一次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以后,继续努力保持革命的势头;另一次是准备进行1924~1927年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大革命的时候。
她于1938年8月访问广州时,我没有见到她。但是,我通过合众社发表了她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明确地表达了她的一些主要观点。她说:
12年来我第一次重返广州,为的是亲自看看广州人民抵抗日本野蛮轰炸的英勇精神。中国的力量蕴藏于人民之中。日本在中国发动的战争是全面的侵略战争—不分军民,所以我们惟一有效的对策是进行全民抗战。
没有全民总动员,中国是无法取胜的。但是,甚至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年以后,这一点仍然没有被充分了解。许多官员倾向于更多地依靠外国的力量……当国际局势似乎变得不利于我们时(如德国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满洲国”,还谣传英国和日本进行谈判),他们便绝望地说,一切都完了。当有迹象表明,日本将入侵华南,从而同英国发生矛盾,或者日本在中苏边界向苏联挑衅时,他们便说:“外国现在一定要进行干预了,我们得救了。”这是一种半殖民地弱国的心态,他们只能仰仗别国才能生存下来。这表明,他们对自己人民的力量缺乏信心。其实,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而且必将—挽救中国……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自己的人力物力,将决定我们的胜败。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得到外援。我们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援助,都深表感谢。
对于美国人民,我要说几句话:你们是同情中国的。但是,在前线杀死我们战士的子弹和落在广州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的炸弹是用美国的废铁制造的。日本的经济依赖着美国。这些事实应当向美国人民说清楚。
她接着像有先见之明似地说道:
今天,日本的飞机是用你们的石油飞来轰炸我们的。明天,日本的飞机将飞临菲律宾和夏威夷的上空。你们正在建立一支海军来对付外来的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正是不计后果的美国商界帮助造成的。
她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此,美国人民打算怎么办呢?在宋庆龄发表这次谈话两年半之后就发生了珍珠港事变。
我第一次同宋庆龄见面,是在她最后一次访问广州的时候。那是9月18日,即日本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国耻纪念日。“九一八”七年以后的广州,在这一天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人民群众的勇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日本飞机从海岸到广州,只需要一刻钟的时间。然而,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打着火把在夜晚的街道上游行示威。
苗条端庄、容光焕发的宋庆龄神态自若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她的名声早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亲眼目睹她的风采,这还是第一次。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后来的24小时内,我们就见面交谈了。宋庆龄认识一批中外人士,她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谴责日本野蛮轰炸的行径。她邀请我们组成了她在香港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部。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动员外国友人提供医药等方面的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武装抗日斗争,特别是极为有效的游击战。游击战士们从敌人手中收复了许多领土。由于我报道了广州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我也被吸收到“保盟”广州分部中。在此之前,她已知道我经常给《中国呼声》写稿。《中国呼声》是她在上海主办的英文版爱国杂志。
大约一天以后,宋庆龄欢送印度国大党医疗队上前线,她邀请我参加了这一活动。这个医疗队是尼赫鲁组织的,宋庆龄同尼赫鲁保持着友好的通信联系。在这个医疗队中,有年轻勇敢的柯棣华大夫。柯棣华接替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工作,后来也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保盟”广州分部还来不及正式开始工作,广州就沦陷了。但是,我同宋庆龄、同保卫中国同盟和她的其他事业的工作关系持续了40多年,并且成为我以后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最后,我应她的要求,在她身后撰写了她的传记。1981年,在临终前夕,她被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不过,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这里,我们还是回到1938年底,在广州陷落以后,我便前往香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