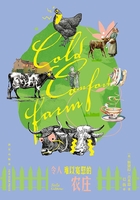冷血的阿拉伯人来了,他们蔑视死亡,经商以外的时间里一门心思研究天文学、代数和他们的内室。随他们一道而来的,是他们同父异母的私生弟弟—索马里人,他们鲁莽、好口角、节欲而贪婪,为了弥补自身血统的不纯而成为狂热的穆斯林,比血统纯正的哥哥更忠诚于先知的戒律。斯瓦西里人与他们为伍,自己本身是奴隶且有奴隶之心,冷酷、下流、鬼祟、很有眼色又满嘴段子,随着年纪渐长变得肥胖。
在北部,他们遇到了本土的高地猛禽。马赛人来了,沉默不语,像是高瘦的黑影,带着长矛和沉重的盾牌,决不信任双手染血、正准备贩卖他们兄弟的陌生人。
这些不同种类的鸟儿一定也曾共聚一堂热烈讨论过。法拉告诉我,在往日,索马里人还没有把自己的女人从索马里兰带来之前,在这个国家的诸多部落之中,他们的青年只允许和马赛族的女人通婚。这无论怎么看都是奇怪的结合,因为索马里人是虔诚的民族,而马赛人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对土地以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索马里人很爱干净,对个人的沐浴和卫生不厌其烦,而马赛人是脏兮兮的民族。而且,索马里人最重视他们新娘的童贞,但年轻的马赛女孩把贞操看得十分轻率。法拉马上给我解释。他说,马赛人从没做过奴隶,他们没法被奴役,甚至不能被关进监狱里。如果被丢进监狱,他们不出三个月就会死在里面,所以这个国家的英国律法对马赛人没有监禁处罚,只能让他们交罚款。马赛人这种在束缚下完全不能存活的个性使他们卓尔不群,与移民者的贵族阶级平起平坐。
所有的猛禽都焦灼地盯着土地上温和的啮齿动物。索马里人在这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索马里人不善于自律,非常易怒,不管走到哪里,如果只有他们自己人,一定会因为部落的道德体制大动干戈。但他们是不错的二把手,阿拉伯资本家们自己待在蒙巴萨时,可能常常让索马里人负责冒险的任务和艰难的运输,因此他们与土著的关系极其类似于牧羊犬和羊群的关系。他们不知疲倦地盯着羊群,露出尖牙。它们会不会在到达海岸前死掉?会不会逃跑?索马里人的金钱意识和价值观念都十分敏锐,他们会为了报酬而放弃吃饭睡觉,远征回来后都累得皮包骨头。
这种习惯还留存在他们的血液里。农场上蔓延西班牙流感时,法拉自己也病得很重,但他跟着我到处去给佃户们派药,嘱咐他们吃药,自己一路烧得直抖。他听说煤油对这种病很有效,就给农场买来了煤油。他的弟弟阿卜杜赖那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感冒也很严重,法拉很担心他,但那只是心之所系,是不足挂齿的琐事。责任、面包和声誉都关乎农场劳工之身,于是垂死的牧羊犬忠于职守。法拉对土著圈子里的事情也极有洞见,尽管我不知道他从哪得来的见闻,因为他除了和基库尤的大头人来往,其他人一概不入他的眼。
羊群本身是隐忍的一族,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自身缺乏力量,又没有人撑腰。它们依靠无比顺从的天性经受命运,现在仍是如此。它们不会像马赛人一样死于束缚,或是像索马里人一样,每当觉得自己被伤害、欺骗或怠慢时,就对着命运破口大骂。它们带着镣铐与外国的神交上了朋友。同样地,它们也对自己与迫害者之间的关系持有一种独特的自我感觉。它们意识到,折磨它们的人把利益和威望系在它们身上:它们才是追逐和贸易的焦点,它们是商品。沿着血泪长路,羊群在黑暗懵懂的心里为“断尾”的自己创造出了一套哲学:既看不起牧羊人,也看不起牧羊犬。“你们没日没夜地不得休息,”它们说,“你们伸着滚烫的舌头乱跑,气喘吁吁,夜里你们也得保持清醒,所以白天眼睛就会更加干燥,这都是为了我们。你们为了我们才在这里,你们因为我们而存在,反之则不然。”农场上的基库尤人有时对法拉态度无礼,就像小羊羔会在牧羊犬面前跳跃,只是为了让它跳起来追自己。
法拉和奇南朱伊在这里相遇—牧羊犬和老公羊的相遇。法拉站得笔挺,戴着他的红蓝头巾,穿着黑色阿拉伯刺绣马甲和丝质长袍,深思熟虑,像你在世界其他地方见过的得体绅士。奇南朱伊整个人瘫在石凳上,除了肩上披着猴皮斗篷,全身赤裸。一个老土著,非洲高原上的一抔土。他们恭敬相待,尽管在没有直接往来时,他们依照某种礼节,都假装看不到对方。
你很容易想象这两个人在一百年以前、或者更久以前,展开的一场奴隶交易的对话。奴隶们是奇南朱伊想除掉的部落不良分子。法拉会一直暗自谋划着向这位老头人—一块大肥肉—猛扑过去,把他塞进自己的麻袋里。而奇南朱伊会一丝不差地读出法拉的想法,整场谈话中,他都会背负着形势的压力和恐慌而沉重的心情。因为他才是核心,他就是商品本身。
解决走火意外的大会和谐开场。农场的人都很高兴见到奇南朱伊。最老的佃农起立和他交谈了几句,然后走回来坐在草地上。两三个集会外围的老妇人尖声问候我:“您好,洁丽爱!”“洁丽爱”是个基库尤名字,农场的老妇人都这么叫我,小孩子也跟着叫,但年轻人和老头子们从来不叫我“洁丽爱”。卡尼奴出席了会议,他坐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间,像个有生命的稻草人,眼睛炯炯有神。瓦伊纳伊纳和他的母亲一起过来,坐得离大家稍远。
我缓慢有力地宣布,卡尼奴和瓦伊纳伊纳之间的争端已经解决了,决议都已经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奇南朱伊过来做证,卡尼奴要交给瓦伊纳伊纳一头带雌犊的母牛,然后这件事从此了结,因为我忍无可忍了。
卡尼奴和瓦伊纳伊纳事先已经被告知了决议,我命令卡尼奴准备好母牛和小犊。瓦伊纳伊纳的行为则更加鬼祟,光天化日之下,他就像只爬上地面的鼹鼠,看起来那么软弱。
我读完决议后,告诉卡尼奴把母牛牵过来。卡尼奴站起身,朝他的两个小儿子上下挥动了几次双臂,他们正牵着牛等在仆人的草棚背后。人群让开一条路,母牛和牛犊被慢慢地领到中间。
就在那一瞬间,会议的气氛陡变,就像一道闪电从地平线上蹿升,迅速直击天顶。
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比一头带着雌犊的母牛更能让基库尤人感兴趣和重视的了。杀戮、巫术、性爱或是白人世界里的奇迹,统统在他们对牲畜熊熊燃烧的热情熔炉前蒸发不见,这热情有种石器时代的气息,像你用燧石打着的火。
瓦伊纳伊纳的母亲仰天长啸,朝母牛颤巍巍地舞动着干瘪的胳膊和手指。瓦伊纳伊纳加入她,讲话结结巴巴、断断续续,好像有其他人在通过他发声,他的声音提得极高。他不接受这头母牛,因为她是卡尼奴牛群里最老的,现在身边这头牛犊肯定是她能生养的最后一头了。
卡尼奴的族人大声喝断他的讲话,愤怒而磕磕巴巴地列出这头母牛的特征,你感到背后藏着一种极大的苦涩和对死亡的蔑视。
当讨论的主题是一头母牛和牛犊时,农场上的人无法自抑去保持沉默。在场的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老人们互相抓着胳膊,吐出最后一口粗气来称赞或谴责这头母牛。他们的老伴们也尖着嗓子跟着吵,就像在轮唱。年轻人压低声音互相口出恶言。两三分钟内,我家的空地就像女巫的大锅一样炸了起来。
我看向法拉,他也看回我,好像在做梦。我能看出,他的宝剑已经出鞘,马上就要在争执中见血了。索马里人本身养牛,也是牛贩子。卡尼奴看了我最后一眼,像一个终于被冲走的溺水者。我观察了一下母牛,她是头弯角灰牛,耐心地站在自己挑起的飓风风眼里。当所有手指都指向她时,她开始舔她的小牛。不知何故,我觉得她确实有老牛的样子。
最后我把目光转回奇南朱伊。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看母牛,反正我看着他的时候,他一点都没回避。他纹丝不动,像堆在我家的一块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同情心的死物。他侧面朝向尖叫的人群,我意识到,这轮廓多么吻合国王的形象啊。让自己瞬间石化是土著的本能。我认为,无论奇南朱伊开口或挪动都会火上浇油,他似乎是在坐等着他们平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
渐渐地,狂怒平息了,人们不再扯着嗓子喊,开始用日常语调谈话,最后他们一个个地安静下来。瓦伊纳伊纳的母亲以为没有人在看她时,拄着拐杖往前踱了几步,更仔细地检查母牛。法拉变回了文明人,带着一丝坏笑。
一切都平息后,我们让涉案的双方到磨石桌前来,用拇指蘸一点马车润滑油,然后把指纹按在协议文件上。瓦伊纳伊纳不情愿地照做了,把拇指按在纸上时还在呜咽,好像纸烫着了他。协议如下:
以下协议订于恩贡农场,日期是九月二十六日,双方为:贝姆的瓦伊纳伊纳和穆图莱的卡尼奴。头人奇南朱伊在场见证。
协议申明,卡尼奴应交付给瓦伊纳伊纳一头带雌犊的母牛。这头母牛和雌犊都应交给瓦伊纳伊纳的儿子旺阳盖里,此人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卡尼奴的儿子卡贝罗无意中用猎枪打伤。母牛和牛犊都应成为旺阳盖里的财产。
母牛和雌犊交付后,这起“绍乌里”就此解决。此后不准任何人再次谈论或提及。
恩贡农场,九月二十六日。
瓦伊纳伊纳的指纹。卡尼奴的指纹。
我在此听到文件宣读。
头人奇南朱伊的指纹。
我见证母牛和雌犊移交给瓦伊纳伊纳。
布里克森男爵夫人。
[2]《摩西五经》里关于铜蛇的说法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穿越荒野时,因为丧失信心诅咒上帝和摩西,上帝大怒,派出毒蛇来咬这些有叛乱之心的人,最后吩咐摩西造出一条铜蛇,挂在柱子上,悔改的人可以观望这条铜蛇,被毒蛇咬伤的地方就会康复,得到救赎。所以铜蛇也被看作伟大的力量象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