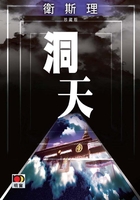大头人奇南朱伊住在农场东北九英里以外,就在法国教会旁的基库尤保留地里,他统治着超过十万个基库尤人。这是一位狡猾的老人,有着良好的风度和了不起的过人之处,但他并不是生来就是头人,而是许多年前被英国人指定的—英国人和这一区基库尤人的合法统治者合不来。奇南朱伊是我的朋友,而且帮过我许多次。我几次骑马路过他的村寨,那里和其他基库尤人的村寨一样脏,一样爬满苍蝇,但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村寨都大得多。因为奇南朱伊作为一名头人,对结婚这件事乐此不疲,村寨里满是他各个年龄段的妻子,从拄着拐杖、老掉牙的干瘪老太婆,到满月脸、小鹿眼的苗条小丫头,她们的手臂和长腿上都套着闪亮的铜圈。
他的孩子聚成一团团,像苍蝇一样到处都是。他的儿子们都是挺拔的年轻人,满头装饰,来来去去,惹是生非。有一次,奇南朱伊告诉我,他那个时候有五十五个儿子是莫兰武士。
有时老头人会披着华美的皮草斗篷,步行来我的农场,他由两三个白发苍苍的顾问和几个武士儿子陪伴着来友情拜访,或是从政务中忙里偷闲,过来转转。我帮他把游廊上的椅子搬到草坪上,他会在那里度过整个下午,抽着我拿给他的雪茄,他的顾问和保镖蹲在草坪四周。我的仆人和佃农听到他抵达的消息,都会聚集过来,讲些农场上有意思的事情逗他开心,整群人在高树下,像在参加某种政治俱乐部。在这些集会里,奇南朱伊有他特别的应对方式:当他觉得讨论扯得太久时,就会靠在椅子里,雪茄的火苗还亮着,他闭上眼睛,把呼吸拉得深沉、缓慢,变成有规律的低鼾—一种官方意义的、形式主义的睡眠,他一定是在自己的国务委员会里练就这种功夫的。我有时也搬把椅子出去和他聊天,这时奇南朱伊就会把其他人支开,表明他现在要认真听政了。我熟悉他的时候,他已经较以往改变了很多,生活让他磨去了不少棱角。当他私底下敞开心胸地和我聊天时,就会展现出许多原创性的思想,以及丰富、勇敢、富于想象力的精神。他仔细思考过生命这件事,并对它持有强烈的个人观点。
几年前发生过一件事,增进了我和奇南朱伊之间的友谊。
一天他来到我家,我正在和一个准备北上的朋友吃午餐,所以一直没时间招呼这位基库尤头人,直到朋友离开。奇南朱伊等我时,应该会期盼能喝点什么,他在太阳底下走了这么长的路,但当时家里没剩什么喝的了,什么都装不满一杯,于是客人和我把家里剩下的各种烈酒都倒在了一起。我想,我把它弄得越烈,奇南朱伊就能被晾得越久。我亲自把酒给他端了过去,没想到,奇南朱伊向我微动嘴唇,温柔一笑,然后给了我一个我从未从男人那里见过的深情眼神,接着他仰头举杯,一饮而尽。
半小时后,我的朋友已经开车离开,仆人们进来说:“奇南朱伊死了。”刹那间,我觉得悲剧和丑闻腾地在我面前升起,像墓地的鬼影一样。我出去看他。
他躺在厨房阴影里的地上,脸上的表情一片空白,嘴唇和手指都发蓝,冰冷。那情形就像你打死了一头大象:拜你所赐,一个曾在地球上行走的威严有力的生灵,它对万事万物都有独到见解,此生却再也不能踏上大地了。他看起来也很掉价,因为基库尤人往他身上泼了水,扒掉了他的猴皮大斗篷。他赤身裸体,像一只被砍下头颅作为战利品的动物。
我打算让法拉去喊医生,但我们没办法发动汽车,奇南朱伊的仆人也一直央求我们稍等片刻再行动。
一个小时以后,我心情沉重地再次出去和他们谈话,仆人们撞见我说:“奇南朱伊回家了。”听情形是他突然坐了起来,披上身边的斗篷,带着身边的随从一言不发地走上九英里回家了。
我相信,经过这一次,奇南朱伊觉得我是为了取悦他而铤而走险的,甚至不惜以下犯上,因为白人不允许给土著酒喝。这之后他也来过农场,也和我们一起抽雪茄,却再也没提过喝酒这件事。如果他开口,我会给他喝的,但我知道他不会再提了。
现在我派人送信去奇南朱伊的村寨,向他解释整起枪击事件。我要求他来一趟农场,为我解决这件事。我建议我们把卡尼奴提到的母牛和牛犊都交给瓦伊纳伊纳,然后让这件事就此了结。我期盼着奇南朱伊的到来,作为一个朋友,他具备人们最为看重的特质—有用。
因为这封信,一起搁浅很久的案件终于乘风起航,戏剧般地结束了。
一个下午,我骑马从外面回家,看到一部轿车以吓人的速度迎面驶来,两轮着地在车道上打了个转。那是一辆镀了很多镍的猩红色轿车。我认得,这是内罗毕美国领事的车,我还在想到底是什么风把领事以这种速度刮到我家来了。当我在屋后下马时,法拉过来告诉我,头人奇南朱伊到了。他是坐自己的车来的,车前一天才从美国领事那里买来,他不肯下车,想让我看到他坐在里面的样子。
我看到奇南朱伊笔挺地坐在车里,像尊神像一样纹丝不动。他披着一件蓝猴皮大斗篷,戴一顶颅顶帽,基库尤人用羊肚来制作这种帽子。他身材一直很好,身高肩阔,全身没有一丝赘肉。瘦长的脸庞神情骄傲,棱角分明,有着北美印第安人的斜额头。他有个大鼻子,这个鼻子太抢眼了,以至于看起来像是这个人的中心,好像整个威严形象就是为了顶着这个大鼻子到处跑。它像是大象的鼻子,既大胆好奇又极端敏感而谨慎,紧张地准备进攻,同时做好防守。最后,奇南朱伊本人就像一头大象,虽然看起来不够聪明,但具有伟大高贵的头脑。
我在恭维汽车的时候,奇南朱伊并没有开腔搭话,也没有扭捏,他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于是我看到他的侧面,像枚敲在奖章上的头像。我绕到车的正前方,他又转过头来,把他的帝王侧影对着我。他可能真的在幻想卢比硬币上的国王头像吧。他的一个年轻的儿子充当司机,车身烧得滚烫。膜拜仪式结束后,我邀请奇南朱伊走下汽车。他威严地披上大斗篷,屈尊下车,一步踏进了两千年前的基库尤司法体制。
我家西墙那里有一张石凳,石凳前是张整块磨石做成的桌子。这块石头有个悲剧的历史:它是那两个被谋杀的印度人磨坊里的上层磨石。凶杀案过后,没人敢接手磨坊,它空置了好长时间,我就把石头带回家里当桌面用—它让我想起丹麦。印度磨工们告诉过我,他们的磨石是从孟买走海路运来的,因为非洲的石头硬度不够,不能用来碾磨。石头正面刻了图案,上面有几块棕色的斑点,我的仆人们坚持认为那是印度人的血,永远都擦不掉了。在一定意义上,磨石桌子是农场的核心,因为我过去常坐在桌旁处理与土著有关的所有事务。在磨石后面的石凳上,我和丹尼斯·芬奇·哈顿曾在一个新年夜里看过新月、金星和木星在空中聚在一起,上演“双星拱月”,那种灿烂光景让你难以置信,我这辈子再也没有见过。
我现在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奇南朱伊在我左边的长凳上。法拉站在我右手边,警觉地盯着围在附近的基库尤人,以及听到奇南朱伊到来的消息从农场上陆续赶来的人。
法拉对待这个国家土著的态度很别具一格。和马赛人的服饰与面部表情一样,这种态度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也不是几天形成的,它是数个世纪延续下来的产物。造就这种态度的力量同样打造了伟大的石头建筑,但这种建筑很久之前就碎成尘埃了。
你刚踏足这个国家,从蒙巴萨上岸时,看到浅灰色的猴面包树之间散布着各种废墟,有灰色的石头房屋、唤礼塔和水井—顺便提一句,猴面包树看上去不像地球上的植物,而像是多孔的化石,巨型的乌贼化石。同样的废墟在沿岸地区一路都是,在塔卡翁加、基利菲和拉穆都有。它们是古代贩卖象牙和奴隶的阿拉伯商人们留下的城镇遗址。
商人的单桅木船通晓非洲所有的航线,沿着蓝色之路前往桑给巴尔的中央市场。阿拉丁曾送给苏丹四百个戴满珠宝的黑奴;苏丹王妃趁丈夫出猎与她的黑人情人大摆筵席,玩乐尽兴,然后被处死。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商人们就已经熟悉桑给巴尔。
随着这些大商人变得富有,他们很可能把闺房妻妾也接到蒙巴萨和基利菲来,当商人们派出远征队北上探索高地时,她们就待在印度洋岸边白色碎浪的长滩上和繁花似锦的凤凰木旁的别墅里。
商人们的财富就来自于这个狂野坚硬的国家,来自烧焦的干旱平原和绵延的未知旱地,来自沿河生长的宽大荆棘树和黑土中强烈散发香气的小野花。就在这里,在非洲屋脊以上,漫步着笨重、睿智、雄伟的象牙主人。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只想独处。但他被黑皮肤小个子的旺德罗波族人射出毒箭跟踪、射杀,被阿拉伯人加重枪口的镶银长枪打死,被诱捕后丢进深坑,一切都只为他光滑的浅棕色长牙。桑给巴尔人在静候。
同样在这里,森林里的一小块土壤被一个热爱和平的羞涩民族清理、焚烧,然后种上了番薯和玉米,他们不善战斗或是发明创造,只想静静独处。他们和象牙一样,也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大大小小的猛禽在这里聚集:
所有啃噬人肉的可悲鸟类都聚集了……
有些只剩了一颗秃头,
有些抹着它们淡棕色的鸟喙离开了绞架,
其他的鸟儿,抓着断裂的桅杆离开了黑色的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