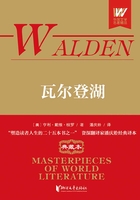但是,呀!谁敢,当生命的末日来临,或死和丧礼把我们的荣名定谳,谁敢称谁幸运?
——奥维德
每个学童都知道关于克罗伊斯国王的故事:他被居鲁士俘虏和判处死刑。临刑的时候,他喊道:“啊,梭伦,梭伦!”居鲁士听到这话,究诘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解释道:他不幸而证实了从前梭伦给他的警告:一个人,无论命运怎样笑颜相向,非等到他生命的末日过去了,才能称为幸福;因为人世变幻无常,只要轻轻一动,便可以面目全非,前后迥异。所以阿格西劳斯回答那些欣羡波斯王那么年轻便大权在握的人道:“不错;但是,普里阿摩斯在这样的年纪命运亦不差。”我们可以看见马其顿的国王,那伟大的亚历山大的后裔,变为罗马的木匠;西西里的暴君变为哥林多的教师。一个统率大兵、征服了半个世界的霸主成了埃及的叫化子般的乞怜者;苟延了五六个月的时间,那伟大的庞培的损失有多么大!
我们父辈的时候,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米兰的第十代公爵,在他治下全意大利曾经威震全球了多时,终于囚死洛什城;而且死前还受了十年牢狱之灾,那才是他一生中最倒霉的日子。最美丽的皇后,基督教中最伟大的国王的遗孀,不是刚死于刽子手的刀下不久么?这样的例子何止千百个?因为,正如狂风暴雨怒殛我们的高楼的骄矜和傲岸,似乎上天亦有神灵嫉恶这下界的显赫。
唉!毫无怜恤的那冥冥的权威
把人世玩弄和摧毁,一样地踹碎
元老的赫赫的杖和凶暴的椎。
——卢克莱修
似乎命运有意窥伺我们生命的末日,把它积年累月建就的一旦推翻,以表示它的权威而使我们跟着拉贝里乌斯叫道:
为什么我要多活这一天!
我们可以把梭伦的格言这样看:他不过是一位哲学家,命运的宠辱于他本无所谓幸与不幸,显赫和权力亦不过是道德的偶然附属品。我猜想他瞩目必定较远,意思是指我们生命的幸福,既然要倚赖一颗禀赋优良的心灵的知足与宁静,和一个秩序井然的灵魂的坚决与镇定,不宜诉诸任何人,除非我们已经看见他表演最后的,也是最难的一幕,其余都有装腔作势的可能,或者这种连篇累牍的哲理的名言也只是一副面具,或者厄运并不曾探触到我们的要害,因而让我们有保持我们那副宁静的面孔的工夫。但是在这最后一幕,死和我们各表演了一场,也就不能再有所掩饰,我们要说真话,要把坛底所有良好的及清白的通通摆出来。
于是至诚的声音从心底溅射出来;
面具卸了,真态毕露。
——卢克莱修
所以我们毕生的行为应该受我们最后这一刻的检验和点化,那是主要的日子,是其余的日子的审判官;正如一位古人说的,审判我们过去的一切时光。我把我研究的果实交付给死亡去实验。那时候才清楚我的话毕竟是发自内心。
我看见好些人由他们的死而获得终身的荣枯。西庇阿,庞培的岳父,临死把他毕生的恶名完全洗刷净。伊巴密浓达,人家问他三人中最看重哪一位,卡布里亚斯,伊菲克拉特斯还是他,他答道:“要到我们死时才能决定。”真的,如果我们评价伊巴密浓达时不把他死时的光荣与伟大考虑进去,我们必定会把他的价值抹煞掉不少。
上帝照他的意旨成全事物;但与我同时有三个我所认识的对于生命无论什么罪孽都是最卑鄙最可咒骂的人,他们皆得善终,而且事事都安排得极为周到。
有许多死勇敢而且运气。我曾经看见死把一个人的非常超升的进步线在最红的当儿剪断,他的末日是那么绚烂。据我的私见,死者的野心和勇敢再不能企求什么比它就这样中断生命更高尚的了。他用不着走路便达到了他所想到达的目的地,比他所向往、所希冀的都更光荣、更显赫。由于他的坠落,他预先取得了他毕生所企求的权力与荣誉。
我评判他人的生命时,常常体察他死时的情景;至于研究我自己生命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希望我可得以善终,就是说,安然而目不声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