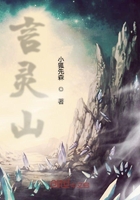在这里,非典,不是SARS,而是非典型。什么样的女人是非典型女人?据说不愿或没有机会相夫教子的女人,还有不会嗲的女人,都属“非典女人”。若是两者占全了,就要被称作“绝对非典”了。
有位作家说女人分两种,花一样的女人,和树一样的女人,那么典型女人便是花,非典女人就是树了。花一样的女人当然柔美,但常常躲不过风雨,贫贱时不是把自己的男人踢出家门,就是要夹着小包裹投奔豪宅名车了;树一样的女人不免粗糙,可在男人困顿、失败时,竟肯赚钱养家,撑起枝干遮风挡雨,堪称可歌可泣。
于是女人有了难题:当典型,还是当非典?做树,还是做花?典型不等于典范,但是花样的女人总能多赚几分怜爱,更何况大多数女人的名字叫脆弱,弱女人很容易找到同类。非典型绝不像病毒那么可怕,不过树样的女人常常寻不到可以仰视的另一棵树,不免孤独了些。
花样女人对树样女人的随意伸展颇有微词,树样女人也不敢恭维花样女人的拖泥带水,总之,彼此间少了自然的和谐。其实,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只要是真真切切地做着自己,又何必厚此薄彼呢。
或许女人没有选择,为树为花,全出于天性。无论造物主扮演着多么不可一世的角色,总不能把花变成树,或把树变成花吧。当然,造物主在雕塑个性时偶尔也会错位,这样世间便有了像花又像树的既典型又非典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