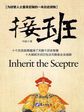然而,给我致命一击的还不是妻子的背叛。我回厂里后,销售科的唐科长已经被免职了。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我始料不及的。新换上来的两个胡科长,一个大胡,一个小胡。大胡是正科长,是原来的厂党委办公室主任,人老成稳重,绝不像唐科长那样不拘小节;小胡是副科长,过去在车间里当装配工,后来在供销科当了两年的供销员,企业改革,供销科一分为二,提拔为供应科的副科长。小胡比我小两岁,少年得志,企业深化改革又提拔为正科级的销售科副科长。大胡科长在家坐阵,人很随和,对下属是否遵守上下班时间,是否在上班时间到别的科室去吹牛聊天,到市场买菜,公出是否游山玩水,他一概不闻不问,但对一些细节问题却很注重,甚至耿耿于怀。我和刘南北后来在哈尔滨南北农机企业联合体订货会上,又签到几千台柴油机的购销合同没有引起他太大的兴趣,引起他关注的是开完了订货会,你邰勇夫为什么与刘南北兵分两路,没有一道回厂?还有你邰勇夫为什么给北大荒垦区的客户拍加急电报,除了业务上的事还加了句:“请向某某处长致意。”我一再说明那某某处长是我老同学,现在是直接管那家客户的上级领导。大胡科长说:“这就更不应该了,给客户拍电报是公事,给老同学致意是私事,公私不能兼顾,这是原则问题,要注意影响。”
小胡科长由副科级的副科长提升为正科级的副科长,与我和刘南北较上了劲,张口闭口:“你们外省组没一个行的。”刘南北听了没有任何反应,像没听见一样,我听了马上反驳: “外省组一个也不行,那两三万台柴油机的合同是你订的?”
那天,为了准备参加全国农机产品订货会,厂里召开销售工作会议。赵厂长在会上提到我,说:“邰勇夫在销售科干了3个月,尚无成绩,再给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再无成绩,就调离销售科。”
我气坏了,这是怎么回事?赵厂长也会突然信口开河?按我以往的脾气,当时就会站起来大声抗议,但我忍了。几天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刘南北安慰我:“小邰,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我说:“不行!我要把我们外省组3个月的工作写份总结,汇报给厂长、书记、工会主席、总工程师、销售科长,咱们不能不明不白的,有成绩就是有成绩!”
刘南北说:“有了成绩都是领导的,以后引以为戒,别再玩命干就是了。”
全国农机订货会赵厂长亲自出马,销售科、供应科、配套科、计划科几乎倾巢而出,还从车间里临时抽去几名全厂最漂亮的女工,内燃机厂一支前所未有的浩浩荡荡的销售大军开拔了。销售科的大胡科长仍在家坐阵。我这位负责外省业务的推销员出人意料地留在厂里。我整日翻弄着一大堆来自全国各地邀我在全国订货会上面谈的电报、信函而坐立不安。刘南北这次去了,但他的任务不是在订货会上拉业务,而是为这支由赵厂长率队的销售大军做后勤,比如排队订火车票,找宾馆订房间。临走时,他哀哀地望着我:“我劝你一句,工作别太积极了,适可而止。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有什么路子可得,其实我们能得到什么呢?连句表扬的话都没有!”
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这样清闲,上班没人管也没人问,装模作样地看会报纸、喝杯茶,消磨一会儿时间,然后就上四楼和搞技术的伙伴们闲聊天。四楼的科室,在我来此工作一年的时间里,已经调整了三次:研究所、工艺科,二者合一为技术科,然后又一分为二为设计科、工艺科。据说这是由于企业改革上边要求不断深化,不断地推陈出新……工艺科现在有6名老工程师。杨工,1966年昆明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搞热处理工艺的,每天趴在桌子上看武侠小说。陈工,1965年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大专生,搞冲模夹具的,每天趴在桌子上鼾声如雷。卓工,1964年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搞金属切削加工工艺的,每天唯有卓工忙,忙什么呢?在办公室桌上不断地调整姿势,全神贯注地搞与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毫不相干的篆刻。据说卓工搞篆刻很有成绩,曾获得过全市篆刻比赛特等奖。最惹人发笑的是徐工,1962年毕业的老中专生,一身肥肉,体态臃肿高大,屁股底下的椅子被他压得“咯吱咯吱”直响,随时都有可能散架,他一不喝茶,二不看报,三不打盹儿,整日坐在那里无休止地左右轮换着挠两只肥胖的胳膊,那挠痒痒的动作特轻且特慢,我相信那绝对像隔靴搔痒般不会有任何感觉。从贵州大山沟里的军工企业调来的总工艺师兼工艺科科长的关工,因为推广工艺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得罪了一大批散漫成性、懒惰成性的人。向厂长打他小报告的人与日俱增。现在他工艺科长的职给免了,只挂了个总工艺师的空衔,和我一样整日无所事事,下了班就玩麻将,晚上在外边挑灯夜战,而且选在人来人往的厂大门口,一战就是大半夜。逢人就说:“你知道姜太公吗?姜太公钓鱼用直钩,意不在钓鱼!”
赵厂长率队的销售大军风尘仆仆,凯旋而归,全厂上下都以为他们战绩赫赫。可一打听,此次订货会仅订了40台柴油机!其中有20台是天天嘀咕“外省组没一个行的”那位小胡科长拉的业务。但这20台要凭电报发货,如果没有电报,那么就永远也不要发货,实际上是个空合同!
我的冷板凳坐不住了,我要找赵厂长谈,如果全国农机订货会让我去,绝不止20台,而是2000台,20000台!我有满腔热忱,我有把万马牌柴油机铺天盖地推销到全中国每个角落的雄心壮志。3个月,一个夏天的奔波,我已经为内燃机厂建立了一个布满全国的销售网络,到这样一个关键的收网捕鱼的时刻,你把我邰勇夫冷落了,吃亏的是企业,不是我个人!
星期天,我第一次找到赵厂长家。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已经找厂党委书记谈过了,把我这一个夏天的奔波做了全面细致入微的汇报。李书记平易近人,在厂党委书记办公室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李书记面部表情十分丰富,随着我的叙述,时而同情,时而惋惜,时而愤愤不平,时而又为之喜悦,时而由衷地赞美。我每讲一句话,他都郑重其事地“嗯”一声,点一下头。我感动了,越谈越激动,最后要彻底敞开心扉,把自己家庭的苦恼、妻子的背叛一股脑讲了出来。我停顿了一下,想喝点茶水润润干渴的嗓子再讲,这时我才发现李书记仍在那里垂着头,有节奏地“嗯”点一下头,“嗯”点一下头……
我吃惊地喊了一声:“李书记!你没事吧?”李书记如梦方醒,嘴里淌出一溜人在酣睡时才能淌出来的口水,“啊,你讲你讲,我听着呢!”
……
我叩开赵厂长家的门,心里面想着的是过去在大学读书时一位老同学讲的话:“你光好好干,不行,要会干!”怎么算是会干呢?我是不是应该买点礼物?总之要学会讨领导喜欢,不然将一事无成,也许一辈子受排挤。赵厂长没在家,接待我的是赵厂长的爱人李老师。李老师刚从市场买回一只活鸡,要杀了中午吃。但有些缩手缩脚,一手拿菜刀,一手提着鸡不知怎么下手。我主动请缨:“李老师,让我来吧!”
李老师有点不信任:“你行吗?要留鸡血的。”
“您放心,保证您满意。”
我抢过李老师手中的菜刀和鸡,一只手握住鸡翅膀,空出中指和食指捏住鸡冠子,另一只手把鸡脖子上的毛拔掉,对准预备好的小碗,顺手一刀,把鸡腿往上一提,鲜红的鸡血像小喷泉似的注入小碗……
李老师满意地笑了:“挺内行!坐下歇会儿吧,老赵一会儿就回来,中午在这儿吃饭。”其实这技艺也是结婚成家后让吴春芳给训练出来的。
赵厂长回来了,见我在这儿,意想不到地欣喜。拉住我的手,握了又握。几个跟踪而来找厂长的,还没来得及说话,赵厂长便向他们挥手道:“今天我要与这位邰勇夫同志——咱们内燃机厂的金牌推销员认真地讨论问题,至关重要,请你们改天到厂里找我好了。”来人都被赶走了,李老师把防盗门也关上了,笑着对我说:“这下好了,谁也不会来干扰了,你们好好谈谈吧。”
我流露出一脸的委屈和愤怒!赵厂长为我泡了一杯茶,削了一只苹果,关切地说:“你的苦衷,我都知道了,不就是老婆跑了吗?你还年轻,好姑娘有的是,要找一个能够理解你的,要有知识、有修养。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说:“不,这些我能够忍受,使我不能够忍受的是,上次厂里开销售工作会议,您凭什么说我邰勇夫干了3个月没有成绩吗?这也罢,这次全国农机订货会,厂里去了30多人,连管仓库的师傅都去了,唯独我这位负责外省业务的主管推销员冷落在厂里,我不明白,难道我们的国营企业是真的干得多不如干得少,干得少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蛋吗?”我说这些是有所指的,厂试验室有两位试验工,一位姓黄一位姓占,姓黄的师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姓占的师傅每天梳着大背头,西装领带,身上还喷着香水,来试验室往凳子上垫张当日的报纸,坐下来跷着二郎腿抽烟喝茶。两个人后来的命运却颠了个个儿。任劳任怨的黄师傅气不过偷了些零配件出去卖,关进了拘留所,吊儿郎当每天啥也不干的占师傅进了供应科做采购,据说去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采购零配件,包吃包住包女人还有巨额回扣。
赵厂长笑了,十分抱歉地说:“这事是误会了,都怪我没能及时和你谈。咱们厂扭亏为盈、转败为胜这要归功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及现场办公,咱们要做无名英雄。两个胡对你的意见特别大,千方百计要把你从销售科排挤出去,做了几次工作,都没做通。那么好,就叫两个胡试试看,这次全国订货会一败涂地,连我这位厂长都丢了面子。明年的生产任务全靠你和刘南北这一个夏天拉到的合同了。这次全国农机订货会上,有40多家客户来找你邰勇夫,要厂里马上发货执行合同,各车间现在已经加班加点了。你这3个月为内燃机厂立了一大功,我召开全厂大会,对你要特别嘉奖!”
我心头一热,脸上的委屈、愤怒烟消云散,眼里涌出了泪水:“赵厂长,有您这样一句话,我就满足了。你让我继续从事推销,就是对我最大的嘉奖!我想到广东、福建沿海去考察一下那里的市场,还有,我想与广州、深圳所有经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公司和各国驻华的商务办事处取得联系,通过他们扩大出口。”
赵厂长面有难色:“我想,你能不能等一等,先忍耐一下,两个胡……”
我有些冲动了:“赵厂长,我真不理解,两个胡不过刚来销售科当科长,为什么对我也抱有那么大成见?”
赵厂长说:“这难讲,讲不清,就像是一个怪圈!你知道我们厂的关工吧?是我引进的高级工程师,也像你一样,很热情,也很能干。我任命他当总工艺师兼工艺科长,我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使你们这些有理想、有抱负的同志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行不通啊,这企业散漫惯了,已经形成了一种沉重的惰性,关工现在四处碰壁,很好的愿望就是实现不了。有人还跑到市里面告我的黑状,说我吃了老关的贿赂才把他调到厂里的。我恐怕也干不下去了。”
“为什么?”我吃惊至极。
赵厂长苦苦地笑了:“这也是说不清的,如果有人要整你,可以小事化大,如果有人要保你,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就在我与赵厂长谈话的第二天,市里来了工作组,宣布赵厂长有经济问题,停职审查,厂长暂时由刚调来不久的邓副厂长代理。我仍想着为内燃机厂继续奔波。夏天过去了,收获的季节伴随着秋天来了,怎么能坐在厂里呢?我写了一份《开发沿海及东南亚市场的设想》交给了代理厂长。代理厂长对我挺有好感,认真地看了我的设想,说:“我知道你邰勇夫,3个月签了两万多台柴油机的合同,明年的生产任务都是你拉的。赵厂长对你很欣赏,我也如此。不过,我要跟李书记商量商量,给你个挑大梁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我几乎忘记了妻子对我的伤害,下了班兴冲冲地跑回父母家,向爸妈报喜:“爸、妈,内燃机厂的代理厂长说了,准备要我挑大梁呢!”
爸妈看我从来也不戴帽子,怎么买了顶帽子戴着呢?摘下来一看,吓了一跳,头上缠着染着血的绷带!妈问:“这是咋整的?”
我想撒谎:“是……房上的油……”我想说又是房上的油瓶子掉下来把头砸了,我的心里一阵难过、屈辱、愤怒。我说:“是春芳,春芳那个混蛋!”
妈问:“又打架了?”
“不是打架,你们不要为这事难过,是我出差时,她勾引上了一个小流氓!”
妈急了:“到底咋回事,说清楚点。我们也好去找她爹妈说说!”
我靠在沙发上,讲了中秋节那个不幸的夜晚。全家人都怔住了,爸灰白着脸,不知怎样应付这事才好。妈气红了眼睛:“哎……我这儿子,中秋节,这都半个多月了,你才回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