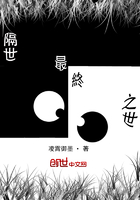张氏赞许着说道:“官人想得可真周全!天热难耐,老员外年事已高,行走多有不便,难得尔等一片忠孝之心!”
老员外、夫人各自上了滑竿,四人轮班,抬起便走,下山的脚步飞快。老夫人更是舒展着一路挂在脸上的愁容,笑道:“不曾想,逃难路上,托吾儿等福气,在这深山老林里,还能坐上花轿。”
话一说出口,逗得一行人笑声不断。张氏打趣道:“老夫人都这样一把年纪,莫非还想坐一回花轿吗?”
“那敢情好,等你为老身寻得返老还童的仙丹,老身吃了一夜间摇身一变,还少时女儿身,再风风光光坐上一回大红花轿,又有何妨。”
老员外一听,明知是戏言,却也没好气地答话:“美得你,天地间,哪有这等好事,真是痴人说梦!”
说笑间,眼瞧着,就要到了山脚,老夫人用力敲打着竹椅的扶手,喊道:“快停停!快停停!”
一路尾随其后的张氏忙问:“老夫人可是哪里不舒服吗?”
“咳,人老了,肚子不装货。这一路陡坡,尿都颠出来了。”
张氏吩咐道:“快放下,老夫人三急。”
两人下肩,没等放稳,老夫人便小脚一蹬跳了下来,更顾不得身边左右汉子们众目睽睽,撩起衣裙,蹲在路旁。众人一看这架势,都背过身去,只听见一阵急促的流水声……起身后,老夫人爽身之余,嘴里还自娱道:“可憋死老身喽。”
老员外一听,没好气地说道:“真行,大活人竟让一泡尿憋成这等模样。”
大官人笑道:“这有么子稀奇,好人让尿憋死的多了去了,老夫人还知道喊一句,没把尿撒到裤裆里就是儿等的福分喽。”
山脚下,一条小溪把两山隔开,一座廊桥横跨两山之间。老员外一见这廊桥,也不知从哪来了精神头:“快放下!快放下!老爷我下来自己走,瞧瞧这风雨桥。”
大官人见老员外执意要下来,说了句:“莫急,瞧着没几步路,可是要走到跟前,要几步路咧!一会到了那里,自然会陪你过去。何况,你没听二官人禀报吗,一房人都在那里候着等您用膳呢。您自己走,可没抬着走快,一会儿赶到那,再看也不迟。”
老员外不再坚持,坐在竹椅上,晃悠着,摇着脑袋,吟起了叶颙的《题幽居》:
隔溪春色两三花,近水楼台四五家。
浊酒不妨留客醉,好山长是被云遮。
松根净扫弹琴石,柳下常维钓月槎。
路狭不容车马到,只骑黄犊访烟霞。
众人听后个个叫好,抬杠的人喘着粗气:“老爷今儿个触景生情,何不再吟一曲,让我等粗人解解乏。”
老员外正欲开口,张氏却已捷足先登,吟道:
“翠薇深处无人住,寺在深山何处斜。”(赵秉文《折桂令》)
老员外见张氏竟在这般时节开口和自己对吟,心想,你这小女子竟敢与老夫对吟诗词歌赋,也太不自量了,随接口道:“梦魂不识天涯路。”
没等老员外背出下一句,张氏便接口道:“愿做杨花片片飞。”
老员外一听,咳嗽起来。大官人知道这一定是张氏接口激怒了老员外,便对着张氏没好气地说道:“你累不累啊,这大热天的,不说话留着口水变尿不好?”
张氏立马明白大官人的用意,讨好似的问道:“老爷,刚才吟的可是胡天游的《杨花令》?”
“正是,你不是记下了吗?”
“这不是你教妾身记下的吗?”
“何时?”
“哦,大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那夜在书房练笔写联,只记得上句,还是老爷进来提示亲手书出下句。”
“哦,记起了,记起了。”
张氏偷眼,瞧瞧这会的老员外已被自己捧得云里雾里喽。他虽然笑得合不拢嘴,心里却在苦思冥想:“这小蹄子,说的是真有那么回事吗?”
大官人看了一眼张氏,从鼻子哼了一句,讽刺道:“妇道人家就是有才也要收敛一些,能成为唐婉李清照的女子又能有几人。”
老员外这会却理直气壮地帮起张氏来:“你一介武夫,斗大的字都认不得三五个,论诗词歌赋,她可做你先生。”
张氏忙插嘴说:“老爷高抬妾身了,担待不起,担待不起咧。”
说话间,不知不觉,一行人已快到廊桥边了,先行下山的伍氏见自家屋里落在后头的一行人被二官人接了回来,已快到茶亭,便冲着在桥上歇息的众人喊道:“快来迎迎,山上的人都下来了。”
听到喊声,众人都聚拢过来,汉子们抢先跑过去接担,下人们过去扶住老人,彭氏、伍氏、环儿则一并跑到老员外、夫人面前请安。
老员外只是随便应了几句,自己不顾一路颠簸朝廊桥走去。上了桥就背着手、低着头,细细观察起来。这廊桥有如天工造物,只见两座石狮护守桥头。廊柱粗大,雕工精美。一块黑底金字大牌匾高悬正中——“飞凌渡”。楹门大柱上左侧是——“迎过往歇小足窥天地”,右侧是——“送香茗解饥渴醉清风”。横梁吊板上彩绘八仙,更是栩栩如生。老员外信步向里走,功德碑上记录着捐银及工匠们的姓氏。
可还没等他细读,大官人就走过来喊道:“老爷,该用膳了,众人都候着呢,还得赶路。”
老员外有几分不悦,应道:“落难之人,无须再讲么子礼数,尔等只管用膳就是,有给老夫留上一口,你等先去吃就是了。”
“那怎么使得,老爷您瞧这日头都已偏西,也是该吃东西的时候了,不填饱肚子,怎么有力气赶路?就是照您的吩咐,去南岳进香,也还得走一些日子咧。”
“你不提起我都忘了,刚刚看了指路碑,不要几多路程,就进郴州府了。”
“就是到了郴州府,老爷要瞧名胜还不多了去了,何苦在这穷乡僻壤误了行程,还是一同用膳的好。”
张氏耐不住环儿的软磨硬泡,只好陪着她同几个小厮一起顺桥头的护坡下到了溪水边。那潺潺的流水波浪翻滚,清澈见底,游鱼穿梭戏水,环儿一见,便大呼小叫:“快拿个家伙来啰,好多的鱼啰!”
老员外与大官人站在桥上见此情景,心想:“这孩子,家境都落到这等田地,还有如此雅兴,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老员外想到此处,叹了口气,再也无心赏这廊桥美景,独自一人向桥下茶亭走去。
星夜兼程,傍晚时分,进入郴州城下。四处都是逃难的人群,乞讨者无数,一见大官人等一行人的穿着打扮,便一拥而上。大官人以为这帮人又是来抢,忙拿起一根扁担,欲护着众人及财物。
那帮乞丐并不哄抢,只是乞求道:“官人,行行好,给点吃的。”
老员外见此情景,叹息道:“哎,哪有吃食周济啊,我等也是落难之人,自己还不知道向何处找吃食呢。这般世道,上吊的心都有。”
两位官人护着老员外及众人进了城。这不进城还好,一进城乞讨的人更多,围着讨,赶都赶不开。张氏扯过大官人,私语了几句道:“这时节千万散不得东西。那是一丁点东西都给不得,这满街巷都是落难逃荒之人、饥饿的人,食人肉的心都有。我等得赶紧找个落脚之地,差家人换上一些陈旧的衣服才是,要不然虽尔等也是落难之身,别个会误认为是官家、富商非打劫不可。”
大官人回道:“这般道理谁人不知,刚刚踏上这方土地,人生地不熟,南北都未分清,又遇这兵荒马乱,眼看天色已晚,城中千家闭户,谁知哪家是客店呢?”只好领众家人顺街乱闯,心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前有我大官人开路,后有二官人守着,中间还有一群强壮的汉子照应着老少,如不遇强敌,只是一帮乞讨也奈何不得我。
正想着,彭氏向前赶了几步,喊住大官人,说老员外和夫人叫他停一下有话要说。大官人驻足,等在路旁。老员外跟上来,说道:“这么走也不是个法子,你也得差人去打听打听,按理说这么大个州府总会有城隍庙,差人四处打探看在何处,去哪里歇息歇息也好过夜。这满街乞丐一行人也开不得火。星夜兼程,车马劳顿,哪还走得动夜路。”
大官人听罢老员外的吩咐,借着月色,环顾四周,寻思着找一个问道的主。可是月光下,除了屋檐下躺着身着破衣烂衫的乞丐,没见一个像样的人。如此这般景象,大官人站在那里没了主意。一直在后面收尾的赛虎公见人群不往前走了,赶到前头想看个究竟,见兄长正站在那东张西望,催促道:“黑灯瞎火的停在这做么子?要快些领着大家找个火铺歇息才是。”
张氏一听,二官人在跟大官人说话,也凑了上来,问道:“出了么子事吗?为何停着不走?”
大官人叹了口气:“见鬼,偌大个州府没见个明白人,想打听道都不见一个合适的人问。”
“我当是何事停下不走嘞,是要问路。瞧,这不到处都是人嘛,我向前问不就是了。”
赛虎公鼻子一哼:“随便找一厮打听不就是了吗,何须叹气。”
“吾兄有所不知,你看屋檐下一个个都是乞讨之人,如若有歇脚避风之地怎会躺在这路旁屋檐之下,岂不早就寻了去?”
张氏没等大官人把话说完,早已明白了一切,径直向屋檐下一半躺在台阶上的老者走去,见面施礼后,道:“请问老人家,这左右可有火铺落脚吗?”
老者起身坐起,上下打量着眼前彬彬有礼问路的妇人,停顿片刻,向前指了指道:“行一街口,有一布幌即是客栈,只怕早已客满,妇人不妨也去瞧瞧。”
谢过老者,张氏回来告知大官人:“前面没多远就有一家客栈。”
“那还等么子,去就是啦!”
“可能冇得客房。”
“先去再说,到那无论怎样都得想法子给老爷夫人号下一间歇息,其余人等找一僻静之处生火煮饭即可。”
一干人听说前面不远处有歇火铺,都兴奋不已,不觉加快了脚步,环儿更是高兴得一蹦老高,嚷道:“有歇火铺就能痛痛快快洗个澡,爽爽身子。”
彭氏见女儿高声大叫,骂道:“闺女家不知廉耻,乱叫么子,老大不小,疯疯癫癫,也不怕人笑话。”
“这有么子,是要洗澡的嘛。”
“你还敢顶嘴,看我不扯烂你这张臭嘴。”说着扬起巴掌就要打人。
环儿见势不妙,一转身躲到了伍氏身后,娇滴滴地哀求道:“婶娘,快救环儿。”
伍氏护着环儿,劝道:“好了好了,今儿个,婶娘保下了。她还是个小丫头,当妈的别和她一般见识。”
“还孩子呢,都是你们惯的,若不是这兵荒马乱,夏家早就把她迎了去,这会怕都是孩子他娘了。要是别人家知道,她是如此不懂规矩,怕也不会要她了啰。”
环儿并不示弱,见彭氏如此贬自己,回道:“正好我还瞧不上夏家那堆肉咧,逃难出来,我因祸得福,这会可是自由身,说不定还能另嫁一户好人家。”
伍氏劝道:“快别贫嘴了,都落到这份田地哪里还能寻得好人家,你这傻丫头做梦呢!”
“这正是天黑,要是躺在床上恰好是有梦的时辰,只可惜,游走在这马路上,有梦也没法做啰。”一席话弄得彭氏再不言语,伍氏被逗得在一旁呵呵笑着。
一行人走着刚转过一条街巷,迎面一对晃灯照得门庭通亮,灯笼上大字写着“客栈”。走近一瞧,大门紧闭。大官人叩响门环,半晌,门才吱吱地开着一条缝,一个店小二模样的小厮从门缝里探出脑袋,说了句:“本店客满,另寻别处去吧。”说完,头一缩,门咣当一声关上了,哗啦一声上了门闩。
大官人气不过,再一次用力敲响门环,那厮不耐烦地在里面喊道:“敲死呀敲,说过了客满。”又吱扭一声,把门开了一条缝,伸出脑袋:“我说客官,求您别敲了行不行,小店客满。”
这会大官人哪里会理会这厮说么子,上前一步伸手抓住那厮胸襟,一脚踹开一侧大门,道:“你这厮好生无礼,我等乃投宿之客,既是无房,你也得好生言语。今夜你是有房得开,冇房也得开,要不然我非点把火烧了你这店家不成。”
这厮也不讨饶,大喊:“快来人,有强盗。”说时迟那时快,从院子角落里立马奔出了七八个手持棍棒的彪形护院大汉,冲到门庭挥棍照着大官人抡棒就打。大官人见这架势,大喊一句:“且慢!我等是投宿之客,并不想在宝地惹是生非,你等真想动粗,且指不定谁能胜,倒不如把你家主人喊出来,了了此事。”
“何处逃来的野汉,深夜在此闯我门庭,莫不是打劫不成?!”一嘹亮的怒斥之声从店内传来,却并不知是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