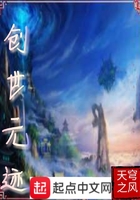一弯明月悄悄地爬上了山顶,月光洒在银色的河滩上,江水波光粼粼,乌篷船倒映在江面上,和着远山的轮廓在月色下朦朦胧胧,山脚下渔火点点。
张氏虽端着碗,心却早被月色下江岸沙滩的美景吸引住了,忘记了饥肠辘辘。大官人手端着一碗鱼汤,见夫人沉醉在美景之中,不忍心搅了她的心境,也不由自主地抬头向夜空中望了一眼,招呼道:“快喝鱼汤吧,都凉了,先喝几口暖暖身子,再美的夜色也是当不得饭的哦。快吃东西,趁热!”
张氏应着:“好嘞,你也瞧瞧,这夜色真的很美。我好久都冇有看到这美丽的夜晚嘞!”
“这有么子,‘一年一日各不同,日出日落月下宫’,老古人早就说了。”
“可不是吗?天工造物真是一点儿没错。哪个画师能画出今晚这夜色之美,刻尽这山水之妙?”
两人会意地看了一眼,舒心地吁了口气。大官人将长辫往身后一甩,又把目光转向了美妙的夜景。
伴着晚风,远处江边上不时传来一阵阵爽朗的嬉笑声,打破了这月下沙滩的宁静。张氏随声寻去,见环儿正与家中的杂役周继在江边上追逐,不时地发出一阵阵浪笑。
大官人见状正欲上前,却被张氏一把拉住。张氏喊着:“环儿,快过来,天黑,别摔倒了。”
“来了!”环儿应着,径直地跑了过来。
一到跟前张氏就笑着骂道:“你这疯丫头,都怪你爹心软,没让你娘给你裹小脚,看把你疯的,就差没长两翅膀了,都是大小姐了,也没个廉耻。”
环儿撒娇地搂着张氏的腰,哼哼唧唧地在张氏的耳边轻声说道:“环儿在江边看水中月影,那后生在背后甩石头,把那江中的月亮打碎了,我恼了,他还追我,对我说‘水中月’是看不得的,还说妹子看了就想着用手去捧,不知不觉就被那月亮带到水里给龙王爷去做媳妇了,那月亮是来给龙王爷勾女孩子的魂的。”
张氏顺着环儿的话,忍住笑一本正经地说:“可不是吗?今天多亏那后生甩石头打碎了江中月影,掀起涟漪,要不然环儿的魂早被勾走了,说不定已成为龙王爷家的三媳妇了。”
环儿惊讶地问道:“二姨娘,真有这事儿?”
“那可不?二姨娘还会唬你不成。还不快去谢谢那救了你的英雄去。”
“上哪儿谢去啊?他早就让你和爹爹吓跑了,这会儿还不知道上哪个冇人的地方收魂去了呢。”
张氏笑着在环儿的脑上重重地敲了一指头:“鬼丫头,你还能寻不见人?你心里那点儿鬼把戏瞒得住别人,还能瞒得过二姨娘?”
环儿这会儿不再争辩,只是一只手捂着胸口,一只手摆弄衣边儿,胸脯一起一伏,嘴里均匀地喘着粗气,低着头靠在张氏的身上。
就着月色,张氏清楚地看到了环儿那娇羞潮红的脸,见环儿不作声,扯了扯她的手催促道:“夜深了,别站着了,到船上找个地方挤挤睡去吧。”
这时环儿才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抓住张氏的手嗲声嗲气地说:“二姨娘,我今晚就跟着你挤一夜好了。早些是跟着老妈子睡,可是自她走后,我每晚都睡不着,常常做噩梦,吓死人了。”
“傻妹子,那船舱这么小,你跟我上哪儿挤去咯?我还不知道哪儿能容得下我倒一会儿呢。”
“我不管,反正就是要和你挤在一起。”
大官人始终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见女儿如此黏着张氏,没好气儿地说道:“去,找你娘去,我和你二姨娘还有事儿,快去,懂事儿些。”
轰走了环儿,大官人若有所思地对张氏说道:“看来环儿和周继那后生已经扯不清了,这可如何是好?这大男大女的要是不经意间弄到了一起,岂不是干柴烈火?又是和自家的伙计,要真把肚皮弄大了可怎么收场?哎——真是‘女大不中留’啊。看来得赶紧把这不知深浅的后生打发了才好。免得他们在一起招惹是非,败了府上一世清白的好名声。”
张氏则没好气儿地答道:“这都么子时候了,还当府上是名门望族呢,都破落到如此境地了,还讲么子门当户对呀。按我说,这要是缘就要成全,俗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现在家道败落,老爷你也别再揭老皇历了。只要环儿有心,周继有意,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兴许,周继还能挑起家族兴旺这杆大旗呢。”
“瞧你这话儿,说得可不在理上,是不是因为环儿不是你亲生的,怕以后她不为你哭灵,你便如此为自己积攒人缘、留后手?门当户对是我府上祖辈留下来的规矩,环儿是府上的大小姐,下嫁给一个杂役伙计的儿子为妻,这在府上可是从来冇有过的事,这可是前后几辈人里的头一桩,我可容不得。”
“好了好了,此刻老爷大可不必把话说得那么死,我也冇要你立马就给个么子说法,这会儿要我看老爷您要装作么子事儿都不晓得,让她们随缘好了。你要是急着给她们按个么子规矩想拆散她们,别到时候弄出点儿什么事儿,环儿的个性你是知道的,到那时候可是冇得么子后悔药吃的哦。”
“就你能,知道得多,再怎么说环儿也是我养的妹子啊,你也太能操心了不。”
“好好好,老爷能这么想我也就冇么子说的了。老爷只要心中还知道环儿是你的血脉我就冇么子话讲了。”
一阵寒风袭来,泊在一起的两条船相互撞击摩擦发出吱吱的声响。寒风掀起了浪花拍打堤岸,吹起篝火呼呼长啸,火星四溅飞向天际在空中曼舞。大官人抬头看了看天,只见夜空中浮云缭绕,繁星点点。“你快去到那火堆旁喊一声,夜深了,起风了,让众人都回船里挤挤睡觉去吧。过会儿风吹熄了篝火,后半夜会更冷。”
张氏正要去喊,突然有人说道:“不碍事的,船里太窄躺不下这么多人,就在这儿守着火堆眯一会儿算了。”
转过身子,只见众人有的抄着衣服抱着膀子,有的伸手烤着火,有的抬头望着夜空,都是一脸愁容。大官人再做劝说,也无人作声。急得大官人在沙滩上来回踱步,跳着脚骂娘。
“看来这是要散伙了,是二官人吵着要分家啊,嫌弃我这兄长冇能力,带着一帮人寻不着一方求生的宝地。”
有人见大官人提起了二官人,还说要分家,便跑上船去推醒熟睡中的赛虎公,将外面沙洲上的事儿添油加醋地传话给他,最后还补上一句:“我们这帮伙计,跟谁都是跟,只不过是想早点找个落脚之地,早点儿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们深知二官人待我们不薄,想着借今夜停船的机会,发难成全二官人的美意,早些散伙各奔东西罢了。俗话已说在那了,‘世上无不散之筵席’。”
二官人听说伙计们都是为了自己在沙洲上忍受这隆冬寒夜之苦,找理由与大官人分道扬镳,感动之余不禁火冒三丈。心想,这般情节我本不知情,也并没有私下授意让下人们没事找事儿,可是你身为兄长却将脏水泼到我这个蒙在鼓里的兄弟身上,也太不地道了吧。今夜我非要找大官人理论理论,就算你是兄长也不能欺负人。
二官人是行武之人,多重性,点火就着,这不还没见人就被下人的几句话给激怒了。下人见火候到了,又添了一把柴道:“二官人,在这节骨眼上,您可要给我们这帮在你房下多年的伙计做主啊!大官人的脾气您是知道的,饿急了的狮子是不认人的。”
“我就不信这个邪,你也不想想他房下就几个女客和老妇,每走一步都要你们这些人帮着才能挪动。大房里,强壮一点儿的也就是印祥、印科两兄弟,这会儿又加上大老爷病入膏肓,他哪儿还有力气跟我们这帮壮劳力争雌雄。今天我非让他听我的不成,这家是非分不可了。”
话一说完,他率先爬出船舱,一个飞身跳下船,脚一沾地就嚷道:“兄长,我在舱里都听你骂了很久了,昨日吃了晚饭,我就爬到舱里睡下了,外面发生了么子事儿我是一概不知。这帮伙计找你寻事儿,你怎好怪罪于我呢?更何况启程前闹分家我只是看到家境每况愈下,想着分开一帮人好为你减轻负担,少一些累赘,兄长不领情,也就冇再理论个么子,事后我也冇再提起过。可是,今夜你无根无据又怪罪于我就太不应该了吧,难道我辅助于你也有罪过不成?看来,我这个好人是做不得,要是今夜你不给我个‘一二’, 又将兄弟骂了个狗血喷头,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念你我兄弟情分,我也只好领着我房下的伙计自谋生路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将来你屋里就是有千顷良田、万贯家财,那也是你屋里的造化,我就是落得个讨千家米,也不会登门求施一口饭吃。从此后,你我一刀两断、恩断义绝,与其说任你终日谩骂,倒不如了了这一世恩仇……”
二官人还在喋喋不休,大官人早已气得七窍生烟。张氏在一边使劲拉着大官人的手臂,小声地劝着:“由他把心里藏着的话都说出来。”
“就你心软,贱人!你还指望他那狗嘴里吐出象牙来吗?我早有所料,这兄弟啊,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空怀一身武艺,从师父那冇学到一点儿习武之人的德行。”
二官人本来好不容易静下来,候着大官人的答复,一听兄长竟敢说自己没一个好德行,火又点着了:“你德行好,读了那么多圣贤书,仁义礼智信,却还讨了一房小,还称自己是行善事,也不知可曾脸红不?”
这一说不打紧,张氏可忍不住了,上前一步,挡在大官人面前,一边儿怒不可遏地推着大官人,一边儿扭着头对二官人斥责道:“兄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自打进了这个家门,小心翼翼做人,凭心做事儿,孝敬公婆,善待妯娌,体贴叔侄,关爱下人,好像也冇哪点儿对不起你这个亲兄弟。而今在这逃难路上,你们兄弟两闹分家,还把我这个本来就倍感无助的弱女子搭上,可就是你的不是了。常言道,‘树下摘花叶也动’,尽管如你所说,我是妾身,可就是‘妾’,也是你家明媒正娶、拜了堂的,你这小叔子也得喊我嫂夫人。按礼数,长嫂当娘,你亲娘老夫人冇教好你,今夜我就要请家法了。按族规,绑你楼梯沉塘,这会儿你这不孝子要是不给我赔礼、还我清白,我虽是二房,也要搬动我家姐姐——你的长嫂,禀报大老爷,去讨个说法,我相信他们的良心不会像你似的被狗吃了去。他们要是不为我这背井离乡的弱女子做主,别看你是习武之人,也不过是一介武夫,妾身虽是半老徐娘,兔子急了也咬人,到那时指不定鹿死谁手,我定和你拼个鱼死网破,指不定谁胜谁负。你别以为小脚女人站不稳,我这个小脚女人不一定好欺,不信你就等着瞧。”
二官人听完张氏这样一席话,鼻子一哼,笑道:“不是我小瞧你,你这女流之辈竟敢在我这七尺男儿面前逞能,夸下海口,今夜我还给你留一丝颜面,常言道,‘好男不与女斗’,跟你交手我还怕弄脏了我的手呢,跟你理论我还真冇有这闲工夫,留点口水变尿还听得见一阵水哗哗。要说法还是找你家官人吧,是他先挑事儿骂我,我才找他理论,他要是不跟我说明白,这事儿冇完,随你怎么弄,我定奉陪到底,你让我走着瞧,我还让你走着瞧呢。”
火堆旁围坐着的下人们见事情闹大了,都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逃难途中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东家,看架势不论兄弟两谁占上风都对自己不利,早已阴一个阳一个地脚底抹油溜到船上去了。
下人中只有周继冇走,他从火堆旁站起身,不卑不亢地走到张氏与二官人之间,大声地劝道:“两位当家的官人,你们瞧瞧自己都说了些么子话啊,也不嫌丢人。我这个在两位官人家扛活挣饭吃的下人听了都替你们脸红。且不说你们现在家境今非昔比,就是念着令尊老员外重疾在身,也不应该再争了。这事不论谁让谁一步不就过去了吗,让一步还会死人吗?今夜你们要闹分家,依下人之见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们现如今这家还有么子分吗?可能要分的只有令尊大老爷与夫人归谁养老送终,还有我等这帮伙计跟着谁干活的事。实际上,跟谁干活不是问题,下力挣饭吃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不是你们俩能做得了主的事,还得伙计们说了算。大家看我说得在不在理上,我看东家们倒不如消消气、细想想,等寻到了落脚之地再作打算也不迟。”
大官人听完了周继这番话,茅塞顿开,心想:是啊,这会儿家中还有么子好分啊?要走人拍拍屁股行就是了,走不动的只有大老爷与老夫人,凭良心谁愿养老送终,谁请了去照料就是了。想到这儿,他连站在身边的张氏都冇商议,就对着二官人心平气和地说道:“赛虎吾弟,你既然熟虑已久,今夜我就成全了你的好事儿,明日一早念你我兄弟一场,就吃个团圆饭,你就自便吧。平日里我死攥着不放是做兄长的固执,不知兄弟早有鸿鹄之志啊。今夜听了周继一番话算是明白了,这家还用分吗?搁不下的只有亲情了,既无一锄地,又无一片瓦可带走,兄弟有前程可奔,我又何苦相留呢?留,岂不是误了兄弟大好前程?”
这样一席话真可谓一语惊人,出乎众人所料,二官人冇等大官人一席话说完就转身向寒风中漂泊不定的乌篷船走去。张氏望着他在月色中长长的背影,不觉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大官人不愧是读书人,遇事儿就是脑筋转得比常人快。可是转念又一想,不对啊,一样的事儿,前几次为什么就转不过弯来呢?看来今夜是周继这后生开口解了死结。原来这个下力挣饭吃的后生提醒了他,才使这寒夜风波在唇枪舌剑中鸣金收兵。
张氏从远处收回目光审视着站在咫尺之间的周继,这个在平日里自己连正眼都冇瞧过一眼的伙计,今夜竟能大义凛然站出来一语惊醒梦中人,实在是让人刮目相看不可小觑。月光下只见他个子不算太高,穿着一身早已辨不出颜色的棉袍,腰间束着一条长巾;粗大的发辫绕在脖子上,发梢搭在胸襟前,扎着长长的红绫;身材略显单薄,却也还结实;浓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月光下白净的脸庞透着几分书生气。张氏心想:难怪环儿总是找机会和他黏在一起,看来环儿眼力不错,周继的身上还真是有让妙龄女子动心的地方,也还真有那么股男子汉的气概。
没等张氏开口,大官人就问道:“后生,你干么子还不上船睡觉去?”
“哦,船上地方窄,都上去冇地方睡了,太挤了,天虽冷,我年轻有堆火儿烤着,在火边打个盹就过去了。再说了,就是挤到船舱里也未必就比这受冻的滋味强些。”
“哦,是这样,你是么子时间来我府上的,平日里怎么冇见过你这后生?”
“回大官人,我是跟着家父替老爷守竹山的,以前常年住在山里,很少来府上,即便是来府上也是一晃就走,大官人冇见过也在情理之中。”
“哦,你是竹园周老四的崽啊?!你爹熏竹笋可是一把好手啊,打他手上出来的笋,又熏得有肉,且色泽鲜亮。”
“冇错,大官人记性真好。”
“怎冇见你爹?”
“他在动身前将我交给了老妈子,说他不走要留在山坳里给老员外继续守着竹林。说是山坳里人员稀少,自己年纪大了也不要太多钱米,再苦也能糊口,就不拖累老员外了,再说躲在大山里乱兵也难以寻见,让我跟着你屋里寻条生路。若有朝一日老员外重返故里也好有个栖身之地,竹山也能变几两银子养家不是。”
“哦,是这样啊,难得你爹有这样一份一心奉主之心啊!我记得你爹还向我借过银角子,说是要送你去读私塾。你上学了吗?读了诗书吗?”
“哦,认识几个斗大的字,不成才,只是认得自己姓‘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