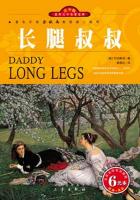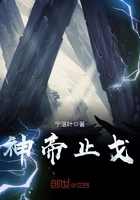大年初一早上聪莉早早地就醒了,外面远远近近都有炮声。她躺在被窝里,折过来倒过去就是不想起……枕头边搁着一身崭新的棉衣棉裤,上面放着新外罩。上身是爸爸从北京刚买回来的大红粗灯芯绒滚边卡腰褂子,下身是妈妈做的蓝涤卡布裤子。枕头底下还压着一双白色尼龙袜。这双袜子她不知道往脚上套过多少次了,但是直到今天才可以正式穿,一想到这里她就非常兴奋。靠床边的桌子上还放着她塑料底黑灯芯绒面的新棉鞋。这双鞋还没挨过地了……
她等着妈妈倒完尿盆捅好炉子收拾好家开始打扮了,就偷偷地看着妈妈用香水清洗自己的下身。聪莉是个爱穿戴爱打扮的女孩,她早就想和妈妈一样打扮自己了,只是不敢说。今天她看着妈妈的动作,又萌生了想试一试的想法。
妈妈的手臂均匀细微地摆动着,香味很快弥漫了整个屋子……妈妈快把自己的新衣服蹭到地下啦,她本能地用手一挡,惊动了妈妈。周武兰吃了一惊,她看着睁着大眼睛不知所措的女儿,突然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嘴唇动了动,难为情地说:“你咋还不起?”
“妈,我也想抹点香水。”聪莉指了指妈妈手中的香水瓶毫无羞意地说。
“咳,小孩子,你抹这干啥!长大再说。”
“不,我就想抹,要不我就不起。”
周武兰看着女儿,突然想起自己也是这么大在太原上学时,看到表姐仔细地梳妆打扮,好等着订了亲的表姐夫来叫她一块去看电影时的情景,当时自己也想把头发重新收拾一下,戴上白发卡,再往脸上扑点香粉,总要打扮得和表姐一样。表姐夫如果能准时来,她也一样高兴,在表姐夫跟前晃来晃去,等着让他说自己是如何如何漂亮的话;如果表姐夫不能准时来或不来,她虽然不和表姐一样骂人,但也愤愤不平无精打彩,心里空落落的。如今自己的女儿也长大了,眼看着她的身体一天天变软,她也觉着女儿已经有做女人的意识了。
聪莉的月经比别的女孩儿来得早,这也可能是她们家比别人家生活好的缘故吧。她的大腿开始发胀,有时还胀得生疼生疼,胸部也有了奶疙瘩和乳包。她不像别的女孩儿对自己身体的变化感到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她毫不在意在男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体。有时候爸爸晚上到南房来睡觉,她就硬要挤在父母中间。等她半夜起来撒尿,发觉自己已经到了父母的一边,她也不在意,把尿盆端到床上,当着爸爸的面一拽裤衩就尿。有时候周武兰觉着不好看就用身体遮挡一下女儿的身体,可是聪莉还偏偏要站起来才要拉起裤衩,弄得周武兰都很难为情。
此时周武兰已经给自己擦抹完站起身。她走到火炉跟前,清了清嗓子,一掀火盖,“啪”的一声将一口痰吐进火口里。她又重新回到床边,看着女儿直瞪瞪的大眼睛说:“来,我教你擦。”聪莉掀开被子,身体很快旋转了180°,把两条腿叉开,直冲着妈妈……武兰把香水倒在手心里,然后将手掌覆盖在女儿的阴道口,等把香水抹均匀后,就先从阴毛处擦起。她用姆指和食指由轻到重,从上到下的揉搓着……她很有耐心,一边揉一边若有所思,仿佛在抚摸和欣赏她极喜爱的白梅花一般。她手指慢慢移至聪莉的大腿间,好像想要把香水渗进女儿的皮肤里去似的。大约过了五分钟,她把手指滑到女儿的会阴部。就在此时她感到自己的阴部也逐渐粘湿起来,身体微微一颤。她怕女儿看出来,极麻利地擦了两下后,抽出了手掌。她对女儿说:“好了,以后就这样擦。慢一点,让香气均匀一些——快,起床吧。”
屋子里的香味渐渐浓了起来。聪莉懒懒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她回味着妈妈刚才给自己擦香水时的感觉。她一开始只是感到有一股凉意就和月经血一样,但是随着妈妈的揉捏,阴部由凉变热,身体也渐渐燥热起来……此时,她特别想把手伸到阴部去涂抹涂抹,去挠一挠。她让身体不停地扭动,以减轻自己的生痒。一阵热痒之后,她感到全身轻飘飘地,四肢舒展自如,无比舒服。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她第一次感到一个人一个女人还能如此享受到自己肉体的快乐。唉呀,这种感觉真是无法形容,怪不得妈妈要天天这样擦呢。从这以后她就经常用妈妈的香水擦抹身子,来享受今天妈妈用这种方式带给自己的快乐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还躺在那里胡思乱想,妈妈又极不耐烦的来催促她起床了:“懒鬼,还不快起床!快起床,咱们吃完饺子串串门,还要到你大舅家去。快起!”听到妈妈的叫声,聪莉才慢慢腾腾地穿好新衣服下了床。
就在周武兰母女俩收拾好床铺房间穿戴整齐准备要去北房吃饭的时候,周奇敲门进来了。他也是来催促妈妈和妹妹过去吃饭的。他一进门,一股浓烈的茉莉香味夹杂着煤烟和被褥热味扑面而来,他一下子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这是啥味儿了?这么呛!你们也不嫌难闻?”
“谁让你进来了!你不会出去。”聪莉看着哥哥半娇半嗔地说。
“你看你那样子,娇滴滴的,不知道从哪学来的。”
“妈——”聪莉望着妈妈,求援似地叫了一声。聪莉对周奇是既敬重又害怕。平时也和在爸爸跟前一样,她总想跟哥哥撒娇亲近,可是周奇偏偏对这个妹妹的亲热套近乎无动于衷,有时甚至很反感,常常还要教训她几句。
“妈,你也不管管她。现在都八点多了,她还不起床!爸爸早就把饺子给煮好咧,让我来叫你们了。”周奇显得有些激动。
“小奇,今天过年了,你不能少说几句。你妹妹大了,你不能总像小孩子一样训她。你看,她不是已经起床了嘛。妹妹对你挺好的,有时候买点吃的总想着你……你爸爸几点回来的?”周武兰突然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反正很晚咧——快走哇,俺爸爸还等的了。”他们母子仨人走进北房时,邹家斌已经在床上摆好了小桌,桌上放了三个盘子和两个洋瓷碗。一个盘子里是牛肉,一个盘子里是猪头肉,另一个盘子里是粉丝海带和黄豆调的凉菜,小碗里是扣肉,大碗里盛放着十来个刚刚炸好的油糕。菜碗旁边立着一瓶红葡萄酒。
“哪闹来的这么多肉?”周武兰看着冒着热气的钢盅锅说。
“昨天去慰问小刘老婆口来,回来在大食堂会餐。有的就没有吃,我就拿回来咧。保准干净,没问题。”邹家斌笑着说。
“够吃就行啦,拿回来干啥。”周武兰一下子从心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反感,心想:搞武斗有功啦,他愿意当炮灰……他不死,别人也要死一个。不值得!不如在家里跟老婆孩子在一起,现在老婆孩子没人管了……不过这些话她没有说出口。
“年轻人都喝醉了,剩下一桌子。老马的手艺,——唉,你不是认识老马么?老马做的肉谁不知道,连文震都说好。拿就拿回来咧……吃哇吃哇。”邹家斌有些认真起来了。
趁父母说话的当儿,兄妹俩早就吃开啦。聪莉夹着粉丝用手托着慢慢往嘴里吸。她爱吃粉丝。周奇想把一块肉整个都囫囵个地弄到自己碟子里,可是夹了半天他还是把红肉和肥肉给挑开了。他很沮丧,只好先把红肉吃了,然后再去夹那块粉嫩的肥肉。
“爸爸,你说的小刘就是去年让晋钢兵团打死的那个印刷厂的人哇?”周奇说。
“是了……老婆娃娃可可怜咧。过年连件新衣服都没有。”邹家斌点点头。
“我前几天还看见他老婆拾大字报了。里面藏的砖头,让人家收破烂的给看出来咧,都给她扔咧。”周奇好像是在说一件新闻,但语气很沉重。
“可笨了,她不会把大字报弄湿……”聪莉满不再乎地说。
“那也不行。收破烂的也能看出来。要我说,不如卖铁,大字报二分钱一斤,铁卖五分钱一斤,铜丝更贵,一毛二,你说啥钱多?”
周武兰把筚子上剩下的饺子倒进锅里,回到床边,看着兄妹俩还在争论,一边用筷子搛碗里已经坨了的饺子,一边说:
“你俩少吃点肉,多吃点饺子……不要说了,快吃饭。”
她没有多吃,心想着下午去了哥哥那里再吃罢。她对那碗金黄油脆的炸油糕连看都没有看一下……她对邹家斌说:“一会吃完,我和他俩去串门,你在家里等着。下午咱们去宾馆看我哥嫂去。”
邹家斌什么也没说。这是个实在人。他此刻只想睡觉,机关里和组织里的所有事他昨天喝酒的时候都推了,今天回来就是睡觉。这几天他跑了不少地方,代表省革委和红总站去看望各地的群众组织,慰问武斗死者的家属和受伤的人。
邹家斌早年家境很不错。父亲原先也种地,后来就把20多亩薄地放出去吃租子,自己去赶车粜货,做个小买卖。邹家斌在大同上中学的时候,正赶上晋察冀边区政府刚刚成立,经同学介绍他就在大同县政府里当了一名文书。由于他文笔不错,没有几个月就把他抽到边区政府里去搞宣传,又没过多久又入了党。当初他想自由恋爱,可是父亲给他说下一个当地很有名望的教书先生家的姑娘。那个女人也识几个字,两个人也能谈得来,婚后生活还和睦。42年整风,因为他家里和岳丈家的问题,把他审查了一次,可把他吓坏了。人本来就胆小老实,从此更是谨小慎微,从不多说过头的话做过头的事。后来调他到东北去工作……半年后老婆去找他,可是从此以后人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女人。有人说她是在北京车站被人拐卖了,也有人说她是在半路上被人害了……时间一长人们也就慢慢地把她忘了。解放后,邹家斌回到山西,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因为独身一人,工作勤奋,他又经常整理材料向上报送,当时已在省办公厅工作的周武翔很快就知道了他的情况,并把他介绍给了自己孀居的妹妹周武兰,不久两人就结婚了。因为家世和个人经历的缘故,他对武兰还是比较恭敬的,武兰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在机关里人缘也好,66年提升成了处长。文革开始后,他先是跟着形势走,自己很少表态,大字报也只是跟人签个名。后来在对旧省委的看法上有了分歧,红总站是倾向于肯定旧省委工作的,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个组织,也就是山西无产阶级红色革命造反总站的一员。这个组织在造反的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眼里是个保走资派的组织,他也就成了铁杆保皇派。他们的对立面是红联站。他是搞宣传出身的,在单位里职务较高,尽管为人比较老实稳重,工作没有魄力,大家还是推举他做了红总站的常委,让他当上了宣传部长。
他也当过军人,但在周武兰眼里,他这个军人跟杨忠奎腰直背挺大步流星的样子比起来那就显得委琐寒酸多了。解放后,给他家订了一个富农成份。这个黑包袱一直压得他抬不起头来,每次运动都和过关一样。现在他在群众组织里虽然是一名头头,但他也时时刻刻不敢忘记自己的家庭出身,做事谨小慎微。特别是涉及到处理两派之间的问题,更是务求周全,尽量不去刺激对方。就这样他还是免不了让红联站(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红色联络站)时不时地揪住自己家庭出身这根小辫子不放。红联站骂红总站是个大杂烩,说他们的头头里就有阶级异己分子……他一看到红联站的人贴大字报,尤其是听到他们的高音喇叭广播,就心惊肉跳,浑身打战……他的这种两难处境,也更加使得他孤癖多疑,轻易不出头露面。他的这个样子,与周武兰的个性格格不入。武兰嫌他窝囊,总看不起他。不过他不愿多管闲事不愿多抛头露面的想法倒和周武兰一致,因此周武兰也不多说他。这么些年,尽管两人不在同一个组织,观点也不相同,但他们还是维持着夫妻情份。
这个时候全家人都吃完了饭,就是扣肉剩下了,其它的都吃了个精光。周奇一搁下碗就出去放炮串门走了,邹家斌打着哈欠准备睡觉。聪莉帮着妈妈把碗筷收拾好后以,她们母女俩这才出了门。周武兰今天没有穿旗袍,而是在白色钻领毛衣外面穿了一件暗红底碎花锻面棉袄,下面是黑呢制服裤。这身打扮越发显得她大方端庄了。头发比平时稍微平整了些,脚上穿的是她嫂子从宾馆内部给她买的黑翻毛半腰皮鞋。
母女俩从东院走到西院。聪莉一路走一路念着各家门框上贴的对联:共产党英明伟大,毛主席万寿无疆。忆往昔翻身不忘共产党,看今朝幸福全靠毛主席……横批大都是欢度春节、喜迎九大、毛主席万岁等等之类的话。她们走过李豫生家门口,他家的对联是: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横批斗批改。聪莉问了问母亲有几个字该怎么念。李豫生的母亲李大大此时正在门外站着,她看见周武兰母女俩过来就打招呼。聪莉忙给李大大拜年。周武兰本不想去李家,但看见李大大已经把门帘掀起,就只好跟着女儿走了进去。
屋里此时已坐得满满的都是人了。李豫生正忙着给人抓糖递烟,见周武兰母女进来拜年,先是一怔,马上便笑着说:“周大姐,过年好……来让让,让大姐坐下。你喜欢吃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自己拿罢。这是从北京捎回来的杂拌糖。聪莉,来给你一块软糖,这张糖纸挺好看的……还不好意思,拿上罢,快。”聪莉一看李豫生递过来的是一块包着绿底黄花糖纸的奶糖,这糖纸她没有,也就赶紧接住装进了口袋。
“你是大忙人,这几天都忙什么呢?”周武兰问。
“瞎忙!给领导和慰问团的买东西,跟着剧团到处跑。初十以前天天有演出,我都得跟着。邹部长回来了罢,这两天可把他累坏了。本来到外地,我也得去,可是太原有演出,我走不开,也就没去。京剧团的人也不让我走。回去给邹部长拜个年。”李豫生说得很快,眼睛连眨都不眨地一直盯着周武兰。
“他愿跑,就让他跑罢。他还能干了啥。”周武兰说。“没出息,回来就睡。”
李豫生接着就是一阵哈哈哈的大笑。此时在座的客人有的已经在哼唱样板戏了。
李豫生是38年出生的。他老家在冀鲁豫交界处,祖父和父亲都是那一带有名的大地主。到他这辈几世单传也就剩下他这么一个独苗了。由于他的母亲是豫东人,所以长辈们给他取名就叫豫生。再加上他生长在那么一个特殊的环境里,所以一张嘴,晋冀鲁豫啥味都有。土改开始后不久他父亲就让打死了,他就由寡母拉扯成人。李豫生自幼乖巧聪明,学什么会什么。解放后,他压抑着自己,怀着恐惧和小心处世,又凭着聪明和刻苦考上了山西大学,63年分配到山西省劳动厅,当了一名机关干部。这些都与他的精明听话密不可分。不过在入党问题上,因为他是地主出身,一直未能如愿。这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升迁,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还是一个统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