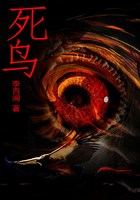“对啦!您看人家现在谁不是在找组织,谁不在积极向党靠拢?咱们的同学绝大部分都回去了。”
“那力量就大了,是吗?”周武兰脸上露出了点笑容。她拿出纸吐了一口痰。
“是嘛,您老让他在家里坐着等着……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不是行尸走肉吗……”
“……看你说的。这个邵率滨!”周武兰心事重重地笑了一下。
“那说了半天,您倒是同意了?”
“我说不过你……那就让他去吧。老让他在家里呆着也不是个长久……他嫌烦,我看见他一个大小伙子光在家里出来进去的也嫌烦……就这,就让他去吧……不过,邵率滨你可要带好他,不要让他参加武斗……”周武兰显然是勉强答应的,其实她是把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推给了周奇,让他去替自己完成。
“那太好了,我就知道周老师是个有大局有气识有肝胆的师长……这叫大义送亲。我代表组织和工宣队谢谢您。”
“你这小鬼,你先别谢谢我……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进步有出息。你问问他,你再问问小奇,你看他愿不愿意去?”
“看您说的,您都同意了,他能不愿意去……他准保听您的。”这时邵率滨端起杯子大口大口地喝起水来。
“妈,其实我不想去。我又不知道他们现在咋咧……再说,我去了,你咋办呀?”
“你去吧……这儿有你妹妹呢。你黑夜再回来。你跟工宣队领导说说,就说我妈身体不好不能来,就让我来了,添一份力量。你也要积极要求进步……你就说,我不参加武斗。有武斗就回来……这件事我还得瞒着你大舅。他不让你去,他就怕你也去搞武斗。你记住。”“妈,那我也不想去。我不想参加进去他们的歪没有水平的辩论……”周奇看起来也不知他是不想去还是不放心,总让人感觉他是犹犹豫豫的。
“你去吧。这么长时间,我也想通了。我不能老让你在家里呆着……你得了解了解外面的形势。这是运动嘛,你多少也得参加点。你一点也不参加,也不行,对你今后也不会有啥好处。”显然,这是周武兰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不过她现在的意识是不是真正的清醒,那谁也不知道。“……好在,学校还有军宣队工宣队,他们会为你们把握方向的。去吧,对你有好处。”
“妈,俺爸爸不在,你……”
“……我,你就不用考虑了……你早晨去,每天晚上回来就行了……”此时,周武兰都带有点催促的口气了。
“……那,那……”周奇突然又一次涨红了脸。他看起来若有所思,不过总算是答应了。
“那,那什么……你放心,我就让你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替我们说说话,别的啥也不让你干。”
“小奇,你要去我给你带点钱。”周武兰这句话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让听她说话的两个年轻人都感到有点惊讶。
“你给你魏老师买点水果罐头……就说我妈让我来看看你……你看我这样做行不行,邵司令?”
“行!”邵率滨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那行了……多会去?”
“今天就去。办公室都给你腾出来了。”
“下午……中午吃了饭去哇。”
“行。”
“唉,小邵,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周武兰就好像是突然想起来一件什么事情一样,一下子显得有些精神了。她站了起来。
“不了。不了。我还得赶回去。回去事还多着呢。”
“……你看,光顾说话了,也忘了问小邵吃饭了没有……小邵,中午就在我这儿吃吧。小奇,你去买两盒鱼罐头去,小邵爱吃鱼。咱们蒸大米吃……小奇,我给你两块钱,你去钟楼街口上那个店里去买……”
“不用了,周老师。我回食堂吃去……不是我不在您这儿吃,是工宣队有规定,所有护校师生一律不准外出。有事请假,一般的小事还不准你呢……”
“……是嘛……”这一说,周武兰倒给一下子怔住了。
邵率滨这时起身要走。他掏出了那只墨镜,很庄重地戴在了自己的眼睛上。“周老师,我今天是冒着危险来的……”他刚戴好,立刻就引出了周奇的笑声。两人互相捶打着同时大笑起来。
“周老师,您放心,我一定把您在家里的积极表现,您写思想汇报的事儿告诉给工宣队的领导……”邵率滨的那两只黑镜片闪着扑朔迷离的冷光。
周武兰看见他俩出了门还在笑,也不知道他俩在笑什么……她突然感到一阵心跳,也有一点紧张……她只是怔怔地看着儿子和邵率滨的背影……
……
秋天的后半夜,怎么说都让人觉得有点齿冷骨寒,况且又是刚刚下过一场连阴雨,这深夜两三点钟的气温就和泡在冷水里一样。这对刚刚过完夏天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为秋天做好准备的人们来说多多少少都有点措手不及。好像夏日就在昨天,大家还在院子里大门外胡同口乘夜纳凉。或独自摇扇品茶,或三三两两南北消息两派内幕家长里短……话多兴浓,越谈越精神……直至夜深人稀,方才打个呵欠,各自散去……然后用凉水冲冲头冲冲脚,倒头睡去……这夏天还正过得舒服着呢……
可是今天就在这儿,就在这西米市粮店的墙根底下,早早来排队买高价粮的人们却在不住地报怨咒骂这寒气逼人的鬼天气。他们有的或蹲或坐,有的站着,不过谁也不能保持这种姿式能达到五分钟以上。他们不停地变换姿式,蹲下站起来,站起来蹲下,不住地跺着脚呵着气来暖和身体。有时大家干脆就一起靠着墙根蹲下,相互贴着挤着来取暖暖……哄笑声嘲骂声此起彼伏。不过这也给这寒冷单调的夜色增添了一些气氛,帮助人们较少痛苦地熬过这漫漫长夜……队伍前一溜排着几盏马灯和石灰灯。有的人还打着手电筒,那光柱不时在队伍中、在人们的脸上晃来晃去,又引来了一阵阵新的骂声。有时几道光柱齐射夜空,交叉映照,互相取乐……有些上访告状和讨吃要饭的人也凑在这排队伍的灯火前,取暖度夜……
杨忠奎此时就在这排队买高价粮的队伍中。他每次来都带着一只小板凳。今天他坐在这小板凳上也不住地打战。他倒是披了件呢子上衣,腿上也套了条毛裤,就这他也仍然是冷得发抖。他没有敢穿年初被隔离前女儿给自己做的那件厚毛呢大衣……他不停地缩头缩肩掖衣服,双脚倒腾着跺地。不过他不敢站起来。他怕引起人们的注意,怕再引起人们的无端议论和猜测。他知道自己现在是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他佝偻着腰低着头,独自在那里默默地坐着……
到今天他回来已经有八九天了。这八九天里他每天都是早早地上班去打扫办公室,擦桌子打水。下班后他又是最迟一个离开办公室,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踽踽独行。回到家以后,他除了给别人家提水以外,那就哪也不去了。
他怎么还要给别人家提水呢?
原来就在开宣判大会放他们回家的那一天,岳大鹏代表群专小组还宣布了一条措施,那就是让他们三个人每人都要给自己院子里那些出去开会学习的红总站干部的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担水拉煤买粮打煤糕啦等等……这也算是一个在机关外对他们实行监督改造的办法吧。岳大鹏还特别警告他们三人,你们时时刻刻都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所以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你们要主动地去帮助人家。如果谁要是阳奉阴违或者说是偷奸耍滑不好好干,那就要再一次对他实行专政,不过下一次可就没有上一回这么好受咧……
回来后杨忠奎每天都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这一条纪律。他是个胆小心细的人。他生怕哪些事情做不到,会被别人检举揭发,会被再一次专政。他顾不得自己的脸面和体力了,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做……可是这些人家又往往觉得难为情而不用他做。人家很礼貌很客气地谢绝了他……他有时是很尴尬地呆立在那儿的!他怔怔地看着人家掺土和泥打煤糕,而且还是很长时间地呆立在哪儿……他很悲哀……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不过他不敢什么也不干,他还是抄起水桶来给人家提水了。有人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不要这么认真;俺们比你还年轻,还能让你干?!你要注意身体,俺们还害怕把你闪着了……你不用害怕,有啥事俺们替你去说……但他仍然不敢怠慢,不敢存有丝毫的侥幸。就这样,他今天这一家,明天那一家的……提水。提水。弯着腰,身子大摇摆地提水……直到有一天,轮到那个他虽然一直想去可是又不敢去,却又不得不去的人家了……他知道这一门自己是躲不过去的。
……昨天白天。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武兰的家门口,他犹豫了。他这还是第一次来到周武兰的家。这也可以说是他四十多年前从周家大院逃走以后又再一次站到了有周武兰在里面生活的家门口前。不过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今天竟然会是以这样一种身份这样一种面目站在了周家的门口……他没敢敲门。
“……家里……有人没哪……”这声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大概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听得见吧。
他连叫了几声……这时那屋里面才有了动静。
一个小花脑袋从白色单门帘后面探出来……一双吃惊的目光毫不掩饰地迎了过来。
“杨大伯,你……你……干啥……”话还没有说完,这个小花脑袋马上便消失了。
不一会儿,屋里一阵xixisusu过后,白门帘被大挑开了。
“……老杨……你……你啥时候回来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周武兰出现了。她先是一怔,霎时间脸色由红而白,紧接着又由白而红……他俩都怔在了那里……这毕竟是他们俩几十年来第一次真正地见面哪……还是周武兰先说话了。
她看见了地上的水桶。
“……你,这是……”
“我,来给你家……提水……”
“提水?!咋地让你……提水……这是咋回事?”周武兰并不知道自己现在对外界是一无所知的。
“老邹不在……组织上要求,给你们做点事情……”说话声仍然干涩低哑。
这时小花脑袋在周武兰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周武兰笑了,不过她笑得很尴尬。
“噢……,小奇刚才走的时候,刚把两个瓮填满。水还满的了……不用。小奇刚走。”周武兰尽量把话说得平缓些,说得热情些。她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快,快进来坐。好不容易才到我家来一次。来,来,不要光站在外面说……来,进来说吧。”
杨忠奎挺了挺腰,他看了一眼周武兰。这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周武兰……她更白了……脸皮打皱了……还是那么漂亮……他等自己的内心稍稍平静下来以后,才试着蹭蹭脚走进了屋里。他是从兰子身边走进屋里的,他闻到了一种香味。等进了屋以后这种香气更浓了。他觉着很好闻。几十年了,他又一次闻到了这种香味。他觉着身上有了一股热力。
周武兰让他坐在沙发上,他没敢坐。他只是呆呆地站着环顾着屋子的四周……他看见那个小花脑袋给他递过来一杯水,他也没有接。他有点僵硬。他觉着兰子就在他身边站着。兰子好像在说话……她说了很多,可是他一句也没有听清楚。他似乎也想说话,他觉得自己好像是憋了许久才要想说出这句话来。
“听说……你为我的事,操心来……”他觉着这也许就是兰子最想听到的话吧。这也就是自己此时最想要表达的意思了。
……周武兰还在说话……不过,他还是不清楚兰子在说什么。
杨忠奎本不想说什么话。他想走,他怕被人看见……可是他还得说,他不敢不说。
“我今天黑夜去,去西米市排队买高价粮……你们要是买,把粮本给我,我去给……”杨忠奎是在清了清嗓子后才说出这番话的。
“不,不用了。我们够吃……还能用你去买!你家要是不够吃,就把我家本上的拿去买了吧……要不,等小奇回来了,今天黑夜让他去替你排队去。”
这回杨忠奎听清了。他麻木僵硬的神情立刻清醒了过来。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呆下去了。尽管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自己朝思暮想盼得不就是这一刻吗?他有多少话要说呀……可是不行,他怕再受连累,再吃专政改造之苦……他把自己提来的水倒进瓮边的一只空桶后,就急匆匆地走出了周家。周武兰在他身后说的话,他还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
杨忠奎此时就这么在这寒冷的秋天后半夜里坐着想着……周武兰的身影不时在他的眼前晃动……她老了……不俏皮了……还是个美人坯子……还是那么招人……几十年了,他对女人的渴求从来没有中断过,对性欲的强烈要求也从来没有泯灭过。解放以前,他还能嫖娼宿妓玩玩大姑娘……那时他确实很风光,人生也很得意。正待他克尽职守,平步青云,并打算找回青春梦想接出周武兰再度人生的时候,没想到天翻地覆,国民党崩溃了,共产党掌管了江山,主宰了一切……他的前途事业突然间发生了断裂,他的人生命运一下子跌到了万劫不复的人间低谷。他的一切都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逃而彻底葬送了。他身边的一切,包括女人也就都随之烟消云散了……他烦恼,痛苦,甚至绝望过……你想想,他当时才刚刚四十出头呀!这正是人生的最佳年段,是一个人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岁月。有多少人就是在这个年龄宏图大展实现人生理想达到生平事业的顶峰从而名垂青史的!而且一个男人最风光最成熟最吸引女人的年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呀!可是他却正好和别人的命运掉了个个……他没有了政治地位,没有了人生前途,没有了名誉和尊严,甚至连生命前途都很难由自己掌握。因为他此时已经沦为了共产党的敌人,沦为了社会、民众的敌人。他是监狱外的战俘,是随时都可以借口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他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掌握,整天都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他哪里还有女人可以陪伴或供他来消遣呀,而且又有哪一个女人愿意和他这个等于是一个死魂灵的社会异类来交往呢!因此他陷入了一种到死也无法摆脱掉的困扰和绝望。他欲活如行尸走肉无人生之趣,欲死又牵子挂女难遂其愿……他生活在别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挣扎中。
他没有了别的欲望。他谨小慎微,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地生活。他从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多走一步路。他下班以后就把自己定在家里,从不出去乘凉说话。他现在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克华身上,可是他又对克华在外面在学校在小孩子们中间受到的歧视和污辱无能为力。他为自己走错人生道路而痛苦难言,他也深深地为克华将来的前途命运而担忧。他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路,可是儿子的路,咋样走他又法预料……他有时长时间呆呆地看着克华,心里暗暗长吁短叹……
可他一切都绝望了,还有做为一个人的最基本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