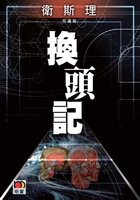二人说了这些话,却是谁也识不得谁是何来头。一时之间,二人似是均找不出合适的话题,谁也未开口说话。如此的沉默良久,终听一人讪讪地道:“足下是友非敌,还个在下早已识得了,只是……”看时,却是袁延翰干裂的嘴唇在启动。
“朋友若有不便启齿之处,不说也罢。”黄衣汉子见他说话迟疑,朗声一笑,截住了他的话头。
袁延翰原想说“只是兹事体大,”被他截口打断话头,心中顿觉尴尬。他见黄衣汉子方才还是戚容满面,转眼之间,便变得眉开眼笑的,心中不觉暗暗称奇。他微微一笑,道:“足下错解哀延翰之意了!”当下将庐州之事向他说了,又说了自己落水之因。
黄衣汉子听得袁延翰之言,不禁失声道:“哎啊,袁统领自庐州闯出已近二日时光,此时,只怕庐城已然落于唐军之手了!”他瞧了瞧袁延翰的面色,急促道:“袁兄内伤非轻,快,坐下来,在下为袁兄疗伤!”
“多谢足下美意!只是运功疗伤须费数时之功,在下心急如焚,还能稳得下心神、凝得住真气么?”袁延翰推开他搀扶自己的手,口中发出焦灼声。
“袁兄还能挺得住么?”
“朋友,区区肌肤骨肉之苦,在下料来还能承受得住!”
“好,既然袁兄如此说话,在下眼下便送袁兄去池州!”黄衣汉子语气坚定。
“朋友好爽快的性情!只是在下与朋友萍水相逢,便劳动朋友大驾,实觉不好意思!”
“袁兄怎的如此客气了!我辈之人,原当如此!”黄衣汉子朗笑一阵,敛了笑容,面上又出现一丝痛苦之色,黯然道:“袁兄,其实,在下与义军诸人、尤是黄浩统领亦是有些瓜葛的,只是……唉,不说也罢!若非情不得已,在下一人去池州传讯便是了,亦不用再劳累袁兄了。”
袁延翰见他神色黯然,识得他心中定然有极为不快之事,却也不好去问,只是轻笑一声,劝慰道:“朋友,谁个未有几件不顺心之事?还请朋友看开些,释怀为是。”
“袁兄,在下一时想起了些往事,心中不觉有些感伤,便说得多了些,倒惹袁兄见笑了。”黄衣汉子似是觉出自己有些失态,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又高声道:“袁兄,咱们走!”“走”字未落,一把拉过袁延翰,不由分说,背负于背,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黄衣人负了袁延翰,奔行如飞,霎时便来到江岸。他放他的身子于地,于一隐蔽之处,推出一叶小舟来。他搀袁延翰上船,扶他坐稳,操起篙来,口中道声:“走!”竹篙在水中轻轻一撑,见得小船似离弦之箭,顺了江水,向下直射而去。
顺水行舟,原是用撑篙不着的,但黄衣汉子心急如焚,是以便也用上竹篙了。
黄衣汉子一篙一篙地撑来,似是借此发泄胸中的闷气。小船在风头浪尖上飞行,却似风筝飘荡在气流湍急的高空之中,摇摆不定。数次,小舟险险儿便要撞上礁石,却被黄衣汉子轻轻一点,避了开去。黄衣汉子身子立于船头之上,任小船颠上簸下,晃来荡去,竟是稳如泰山,纹丝不动。看来便是天崩地裂、雷霆万钧,他亦是不会动上一动的。
袁延翰乃绝顶高手,又厮杀疆场数十年,此等惊险,对他来说,自是算不得什么,但他见得黄衣汉子如此神态安详、举止自如,心中亦不禁暗暗赞叹。
轻舟如飞,三百里之地,数时便至。
袁延翰功力高强,虽是身子坐于颠簸剧烈的飞舟之上,却也能运功调息。如此的一路行来,体力虽未全复,内伤却愈大半。
船至池州,靠岸,黄衣汉子送袁延翰下船。他拱了拱手,笑道:“袁兄请自便,在下便要返回了。”
袁延翰与黄衣汉子虽是相识不久,但见他如此坚毅勇敢,且又如此古道热肠,心中却是钦佩至极,早将他视为同胞弟兄,如今将要与他分手,当真便觉难分难舍。此时,心中虽有千言万语,一时却又无从说起,且又找不到适宜的言辞。愣了许久,方上前一步,抓住他的手,涩声道:“老弟便不进去坐会了么?”
黄衣汉子见他面露惋惜之色,识得他心中恋恋不舍,却也有些怅然,但终于苦笑道:“袁兄,在下进去有诸多不便之处,便不去打忧了吧?袁兄见得黄统领及诸首领,便说有一故人问候。”口中说话,身子便欲跃上船去。
却听袁延翰依依地道:“老弟今日离去,不识何时再得相会?”道时,真情溢于言表。
见得黄衣汉子神色一黯,低下头去,旋又抬起头来,爽朗地笑道:“袁兄,二座山碰不到一块儿,两个大活人还遇不到一起么?咱们日后自会有相见之期的!”道罢,跃身上船,手中篙使劲一撑,小舟艰难地逆流而上。
黄浩听袁延翰道罢庐州之事,顿足道:“是我误了庐州义军众将士的性命的!”眼中不觉流出泪来。
“唉,浩弟休要自责,俊哥亦是有不容推卸之责的!”却见一人上前一步,扯了黄浩的手,柔声劝慰道。
“俊哥,此事不关你事,都怨浩儿太麻痹了,竟让杨行密等钻了空子!”黄浩叹了口气,又嘶声道:“俊哥,浩儿若能像昔日一般,隔三差五便派人去庐州联络一次,也不会给唐军留下可乘之机了。”
“这却怪浩弟不得,谁会料得杨行密、钱鏐、高季兴这三条疯狗,前时还咬得难分难解,皮破毛落,转眼间便会突然合为一窝子,共同用兵,来攻打义军呢?”“俊哥”苦笑一阵,又道:“俊哥来池州之时,浩弟不正欲遣人去庐州么,只是听俊哥报庐州平安无事,才打消了此念头的么?如此说来,俊哥却要负主要责任了。”
袁延翰见黄浩与“俊哥”争着承担责任,又见黄浩捶胸顿足地追悔不已,心中但觉不忍,却又有些着急。听得他轻咳一声,语声平静地道:“黄统领、王统领,此时非争议此事之时,还是请尽快想一万全之策,速去救庐州的为是!”
“俊哥”、“王统领”自是被陈夹说的为“庐州主将”的“白衣秀士”王俊了。
黄浩闻得袁延翰之言,心中陡然醒悟,俊面一红,讪讪的道:“袁统领所言极是,咱们眼下便去庐州。”他转过身子,对了一人躬身道:“五叔,池州乃义军根基之地,它的安危关系到义军的存亡与发展,这防守池州的重担,便要落到您老与八叔肩上了。”
“浩儿放心去吧,有五叔在此,池州防务自会安置得妥妥当当的!”一黄衣汉子大声道。
黄浩点了点头,大声道:“吴五叔、七叔、袁统领、俊哥,随我去校场点兵,咱们去救庐州。”率先出得门来,四人紧随其后。五人点齐兵马,一路的疾奔庐州而来。
众人心急如焚,一路的催促兵马紧行。如此的紧趱,看看离庐州已然不远了。黄浩五人心中却是愈行愈紧张。
正行间,忽闻前面隐隐地传来厮杀之声。黄浩心中一喜,识得庐州的义军尚有人在,不由心神大振,口中发出一声长啸之声,大呼道:“弟兄们,快走!”催动駃騠马,率先向前冲来。
义军将士奔至庐州城下,果见几队人马斗得正炽。
黄浩拍马如飞,直冲而上,注目瞧时,心中不禁大吃一惊,但见前面的厮斗者,乃是几队唐朝军马,并无一个义军将士。他又向了城上瞧将过去,却见城头之上,高高地飘扬着“浪荡军”的大旗;城墙上,立了众多义军将士,正以手指了城下的唐兵,指手画脚地不识说些什么;被炸塌了的城墙也以沙袋补好。
高季兴拉马一旋,退出圈外,乘陈夹、冯权二人倾力架住杨行密与钱鏐二人之兵之机,手中双环一抖,分向二人背心击来。
正自危急,忽听一声暴喝之声传了过来,便见由城墙之上,凌空纵下一个蒙面人来,离得老远,便双手一伸,以掌心将陈夹、冯权二人吸了过来,又一手一个提了,挟于肋下,长啸一声,身子一跃,由城墙豁口处直飞出去。
杨行密三人直惊得目瞪口呆,怔怔地坐于马背之上,竟忘了追赶。半晌,方回过神来。便听杨行密大喝一声:“贼子大胆!”双腿用力一夹马肚,战马咆哮一声,由豁口处跃出城来。钱鏐、高季兴紧随其后。
蒙面人虽是功力了得,但他身挟二人,自是行动不便,杨行密三人坐骑又均是万里挑一的神驹,是以不多时,便被三人追至背后。便在此时,忽听二声断喝声传将过来,见得斜刺里又冲出二个蒙面人来,阻住杨行密三人的去路。
高季兴见二蒙面人阻路,口中发出一阵阴笑之声:“嘿嘿,不要命了么,敢拦高某之路!”手中双环左右一分,拍马抢前一步,居高临下,对了二人当头击下。
听得二蒙面人口中各自发出一声冷笑之声:“好大胆的狂徒,竟敢尔尔!”见得招式袭来,身子不退反进,灵巧避过钢环,欺进高季兴面前,飘忽几剑,反将他迫得连退几步。
高季兴暗道一声“邪门”,勒住马,以双环护住身子,口中大呼道:“杨帅、钱兄,风紧,并肩子!”
杨行密怒吼道:“小小毛贼,焉敢欺人太甚!”拍马向前,手中大刀挥舞,向了二蒙面人招呼过来。钱鏐亦步亦趋。
几声冷笑,轻轻数剑,二蒙面人便将身子密密地护了,任杨行密三人如何进攻,竟是近身不得。
杨行密三人均是老得掉了毛的老狐狸了,早已瞧出二蒙面人的功力倒也并非十分高强,招式却是诡异至极,三人试遍各种功力,竭尽全力,却是伤二人半根毫毛不得,不由各个心中暗叫“怪哉”。如此再斗一时,三人竟不识如何下手了。杨行密乃一凶猛强悍的纠纠武夫,直急得他口中“哇呀呀”地暴叫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