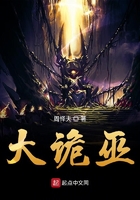九寨沟可以是藏人传说中的男神达戈与女神沃洛色莫的恋情所造。开天劈地的造山运动和几乎等同于静止的生物喀斯特沉积活动是达戈战胜魔鬼获得爱情的全过程。海子是沃洛色莫失手打碎的宝镜。花草树木则是两个热恋的年轻人遗落的体毛。大熊猫、獐子、蓝马鸡是东方密林之神亚拉伊觉送给的贺礼。一个人傍晚路过芦苇海,没准就会遇见沃洛色莫。她在已经枯黄的稻子一样的芦苇背后。她的头发也像芦苇——在夏日的晨风里飞扬的青翠的芦苇。她的肩胛骨,她的后颈窝,她的在摇曳的芦苇里时隐时现的后腰。
九寨沟,想象里的冲动要远比亲眼看见的多而强烈。一个完美主义者是不适宜去九寨沟的。尤其是一个热爱旅行的完美主义者。完美真的只能在想象里,就像传说中神的爱情。只有想象里的九寨沟才是那面不慎被打碎的宝镜的碎片,才是你一个人的九寨沟。然而,我这个完美主义者却去了三次九寨沟。三次,想象力几乎下降为零。而今九寨沟能让我想到的,仅仅是与九寨沟无关的杨炼早年那首《诺日朗》和容宗尔甲唱遍大江南北的那支《神奇的九寨》。它们已经与想象无关。
因了九寨沟,无论岷山有怎样的雄壮,它也是女性的了。无论海拔5588米的雪包顶如何张扬岷山的雄性,也抵消不了九寨沟赋予它的雌性。在我看来,九寨沟的水包含了女性全部的色素;水量足以暗示女性全部的经血和体液;而水姿,则是女性娴静、泼洒、奔流多种气质的外化。娴静是主流,泼洒仅仅在海子间的衔接处,而真的激情飞扬也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瀑布,且必须是在降水丰沛的年份和季节。比如珍珠滩瀑布和诺日朗瀑布。海子一个接一个,其间有神秘纤柔的灌木丛过度。微风拂过水面,逐生涟漪,尽显女人的小心情、小情感,小感觉。有风力超出微风的,水面便有涟漪竖立,细浪凸现,像我们看见的贝克汉姆时髦的发型之一种。但海面之下深沉含蓄,有积淀。海子间的灌木丛非常类似女性私密处的前沿。时而幽暗,时而透爽,隐秘之处幽泉暗涌。所以要说,九寨沟是岷山最为性感的地带。芦苇海,树正群海,长海,五彩池,五花海,熊猫海,箭竹海,珍珠滩……多么像处子的花蕊——各式的处子各样的花蕊。尤其树正群海,怎么想怎么像,怎么看怎么像。
在正午的烈日下看长海,长海什么都不是。她太明确了,像一个毫无遮拦的女人体,丧失了可供我们臆想的元素。雨雾里的长海一定非常的美,它的边际和水面都会因了不确定而让我们幻想。有限的轮廓隐埋在水雾里,给予我们无限的错觉。美总是在错觉里存在。我想象雨滴打在长海的肌肤上,它的肌肤生出一个个小窝儿,而风又随即将窝儿抚平。雨滴变成雪花,水雾变成积雪,肌肤轻度冰冻,皑皑的雪从湖边一直铺向山峰。倘若只是深秋,雪一点不厚,冰也很薄,整天,我们都能在空气里感觉到雪融的气息,甚至听见声音,闻见气味。残秋一点点显露,装点着长海。那样的时候,我们想起的便是老来依旧风姿绰约的女人。
五彩池最似沃洛色莫打碎的宝镜的碎片。只是那碎片也是由水做的,水之碎水,所以落在丛林依然圆满。我认定五彩池的水里溶了若干沃洛色莫的眼泪。她打碎的是达戈赠予她的宝镜,便等于是打碎了她自己的心。一个人在清晨路过五彩池,很可能还会看见沃洛色莫低泣的侧影。她的肩胛骨和锁骨凸出得厉害。她已经有些憔悴了。接过达戈递过的宝镜的时候,她的身子还是非常丰腴的。
我是在太阳升起许久才路过五彩池的,所以我没有看见沃洛色莫,也没有看见有她流下的眼泪;我只看见赶集一样的人边走边举着相机对着五彩池卡嚓卡嚓,而五彩池的水线在急剧下降。
我三次见到的诺日朗都不是妙龄的诺日朗,甚至都不是一年之中、一季之中和一天之中状态最佳的诺日朗。我可能已经永远错过了诺日朗。诺日朗是一个身躯,但不是达·芬奇笔下那种完美的身躯,而酷似米洛的维纳斯的残缺的身躯。一道长过百米的裂口和水的集团堕落成全了诺日朗。在别人眼里,诺日朗或许是堕落的地质和堕落的水,但在我看来,则是一种气象,一种恰恰是残缺给予的完美的气象。从远山到台地,从裸崖到远远近近的灌木丛,从任意一笔翠绿或一抹霜红到飞溅带给你肌肤上的一滴不宜察觉的水珠,都是构成这完美气象的不可或缺的元素。自然少不了朝晖斜阳、落雨飘雪、大雁横空,以及小鸟依人。
不只我错过了妙龄的诺日朗,现代人都错过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诺日朗也是沃洛色莫,不曾错过的惟有达戈。我相信那时的诺日朗连生物喀斯特都是柔软的,就别说水、灌木和空气了。且无以名状的丰盈。即使是在早春也是自满的。朴拙的性感到深秋也不衰。每到夏天便要疯狂。绿染了水,染了空气,一直染到天空的蓝。就是没有一点风的时候,诺日朗也不是静止的,冷杉云杉在跳舞,台地上下的灌木也在跳舞。它们像是要被欲望从内里折断。每一个水滴、每一片叶子的脸都胀得通红。这些毫无意义的美,这些没有等待的疯狂,这些逝去时间的永恒的孤独,对于现代人的我们而言不过是一种诗性的悲伤的追思。
我见过三次诺日朗。诺日朗的美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在九寨沟这美人窝里,诺日朗更像是个大众情人。我知道早年的杨炼之所以钟情这位大众情人,全得于对她的误读。
……
栈道崩塌了,峭壁无路可走,石孔的日晷是黑的
而古代女巫的天空再次裸露七朵莲花之谜
哦,光,神圣的红釉,火的崇拜火的舞蹈
……
杨炼不过一相情愿地借用了诺日朗。
剑岩下的原始森林空寂得密不透风,空气里有制造过十八般兵器的作坊遗址的紧张。它的前世该是男神达戈,是他让沃洛色莫受孕,生养了那一串串灵灵透透的海子姑娘。而今它仅仅保留着一个百岁老父坦荡慈祥的落寞。
草海是一个单凭名字便足以挽留我的赤脚女子。她的脚板很大,腿有些微的弯曲,而且敷着泥,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走过很多山路的牧羊女。下午路过草海,我看见一些倦容和一些清纯在交融,在山风吹开的她的藏式裙袍底下,在她桦树一般的肌肤上。细碎的阳光在她的肚皮和小腿上翻卷,而她却是一无所知,自个儿沉醉在一个没有白马王子的简朴的梦里。我很留心山边那一绺鹅黄的草带,包括草带间撑开的零星的野花;从那些尚未被统一的颜色和气息里,我看见了牧羊女桀骜不训的童年。与她的那些发育良好、见多识广的姊妹比起,她还显得很单薄,但正是那种单薄为我的想象提供了别样的可能。“草海,草海,草海……”我每唤一次你的名字,你就会在我的意识里探出一次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