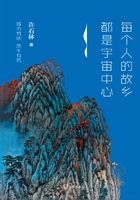过去多是在冬春季节去白马寨,看见的也多是荒芜和冰雪。肌肤记住的是凛冽,眼睛记住的是鼻孔呼出的白烟,耳朵记住的是寒风的叫唤。夜里开门出去小解,看见的夜空和星星也都是冰蓝的,像冰做的。上午即使是碧空朗日,墙脚的老冰老雪也都不融化,北风不间断地吹着落光了叶子的杨柳树,让人不能呼吸。
这一次仲夏去白马寨,感觉完全不同。与春秋两季的感觉也不同。青是铺天盖地的,繁茂的植物像火一样蔓延。像火一样,但又是绿色的;像火一样,但又是寂静的。车在火溪河、羊峒河河谷跑,没有人相信车轮下的路会是连接着外面的世界,没有人相信从一个喧嚣、堕落的时代还可以过渡到这样一个纯洁、宁静的境地。我宁愿相信那些灌木丛的鸟、冷溪里的鱼从未去到过外面,从未知道有外面;去过了,知道了,便是一种污染,一种不洁。
一路上看着青山冷溪,想着“火溪河”、“羊峒河”、“夺补河”这些名字的由来,感觉时间真是神奇,不仅孵化出了我们,还孵化出了我们的文明。白马人怎么叫“火溪”,怎么叫“羊峒”,又是怎么叫“夺补”?或许仅仅是一种发音,完全与今天汉语的词义无关,但在发音的背后又一定是意会了他们对这几条溪河的理解与审美,意会了他们与之的关系。
海拔三千多米的黄土梁是平武与九寨沟的界山,但却不是白马人与藏人或者汉人的分界,黄土梁下面的三方都住着白马人:九寨沟勿角的白马人、甘肃文县铁楼的白马人和平武白马的白马人。他们原本是一家人,后来翻过这座山梁,到了羊峒河河谷定居。羊峒河河谷的下壳子和上壳子,就是从文县过来的白马人搭建的寨子。几百年过去了,他们依旧保持着绿叶与根的情意,互通婚姻。
火溪河与涪江交汇的河口海拔不到一千米,河口对面的野猪山直到民国时候都还是白马人的寨子。进入火溪河河谷,白马人寨子越来越多,余家山、争岩窝、木皮、官坝、新益、河口,海拔也不断上升,尤其是从木座寨子到焦里岩一段,海拔陡增了六、七百米。如果说木座寨子以下还是山地气候的话,那么白马已经是高原气候了。我们从果木开花的时间、灌木发芽的时间,可以探寻到气候的差异。五月,火溪河口已经是初夏的景子,而白马寨子的春意才开始变得浓郁。从羊峒河畔七月的翠绿当中,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点。
黄土梁的气候和植被是典型的高原了。下车走进草地,看见的,听见的,闻到的,都是没人烟的那种。呼吸到的,肌肤感觉到的,都是接近天空的东西。七月,大杜鹃已经开过了,只有小杜鹃还零零星星地挂着花。洁白的花,不曾染上人烟,呈现出某种精神的圣神。远近的绿也是,青山的青也是,保存着史前的单纯与原始。因为是阴天,能见度有限,稍远的山峰和天际都被云雾罩着,无法像晴朗的时候看见雪山——巍峨的雪山,从阿坝一直绵延至陇南。
我特别关照脚下的小花,它们杂生在草丛里、牛粪里,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花茎,各种各样的花瓣,各种各样的颜色,自然也不曾染过人间烟火。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是神赐给大地的,赐给我的。我把相机调到微距,尽可能地拍下它们的细微处,希望能洞悉到神的工夫。我的心跳加快,呼吸加快,不完全是因为高山反应,也有审美的兴奋、想象的兴奋。
从黄土梁下来,路过下壳子,我叫停了车想去看看。下壳子早已没有人居住了,留着一个空寨子,一个废的寨子。冬天和初春时节,空寨子懒懒的地躺在羊峒河右岸的山坳里,静得能听见阳光的声音。现在是七月,它被淹没在绿色当中,半露出屋檐和木楼,隔河看去,屋檐与木楼都是绿的。我知道那些木楼站立的真相——内部已完全腐朽、坍塌,站立不过是它们尚能保留的最后的姿势。六、七年前去的时候,人刚刚搬走,寨子还是完好的,院落、木楼、土墙、板壁、木梯……一切都还是完好的,就像有人居住;走在长满蒲公英和野菊的小路上,还留着白马人的脚印,空气中还弥散着白马人特有的体味。路坎上那几棵叫不出名字的带刺的灌木,看上去就像我们习惯了的修剪过的桑树。随便推开一扇门,走进去,还能闻到烟火的味道。白马孩子用木炭或者粉笔写在板壁上的笨拙的歪歪倒倒的汉字都还很清晰。后来再去,看见了些许的破败和颓废,看见了瓦砾、垃圾和丢弃的衣裳、草鞋和碗筷。还有荒芜。它在蔓延。从寨子的内部向外蔓延。我们楼上楼下、没完没了地拍照,拍我们发现的每一件东西,拍他们原来的、现今丢弃的生活。一边拍一边去想象他们的过去,他们祖祖辈辈有过的每一天,自从在此定居后的每一天,每一个个体的每一天,每一个个体的时时刻刻——那可是有别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别于我们的文明。首先是有别于我们的血液,有别于我们的语言、地理、食物和思维方式。每一次想象都让我感动,感叹,忧伤。冬天和初春时节,羊峒河的河水不大,但流淌的声音还是能听见。羊峒河见证了我们想象的一切,但却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有两次走藤桥过羊峒河,走草径去下壳子。冬日暖洋洋,我们走一走坐一坐,有时也躺一趟。我想象自己就是一个下壳子人,一个白马人。我注意到草径上一块半陷在土里的石头,它光溜溜的,不再有一点点的棱角。我蹲下去抚摸这石头,想象那些脚——从时间里汇拢的密密麻麻的脚,穿草鞋裹棕的脚,甚至光脚——与石头的摩擦。我试图挖出那块石头抱回去,等什么时候有白马人博物馆了捐出去放在玻璃柜里,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去想象。但它太过于大了,埋得太深了,我无力挖出来。地震后再去,木楼已经崩塌了很多,很多都变成了废墟。寨子里互通的小路长满了野草和灌木,板壁朽了,土墙坍塌,用原木砍成的楼梯被丢弃在垃圾堆中。我捡回了一个碓窝,一个七十年代产的洋瓷碗,以及一张手绣的明信片。
九寨沟环线公路从下壳子脚下羊峒河左岸经过,不时有汽车跑过,打扰了下壳子和羊峒河的宁静,但这打扰是有限的,废弃的下壳子的宁静显得依旧深邃,与高远的天空和野草洋芋苗的知觉相伴;羊峒河从黄土梁一路流淌下来,潜入深涧,隐藏在茂密的灌木丛,不失早先的宁静与野性。
从羊峒河出来,我们的车左拐进了夺补河河谷。夺补河是火溪河的上游段,有大窝凼和竹根岔两条支流,都发源于王朗雪山,在进入白马寨之前要流经大片原始森林。进寨门的第一个寨子不大,就十几户人家,坐落在公路上的坡坡上。汉人叫罗通坝,白马人自己叫加。加过去就是我非常熟悉的焦西岗。比罗通坝的地盘要大,住户要多。虽然也坐落在坡坡上,但看上去要有气势的多。每次有外面的朋友进来,我都带他到焦西岗,住在阿波珠家里。阿波珠是我初中和师范的同班同学,有个大院子,有一间干净、温暖的火房;还有一手好厨艺,一副好脾气。他喝酒,他劝客人喝酒,喝高了,便开始唱酒歌,那歌声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都描写过:低沉、深沉、悲怆,完全是生命本身蒸腾出的。这次我没打算去他家,没跟他联系,车从寨子下面过,我摇开车门去看通往他家的那条水泥路,去看路上的苹果树和叫不出名字的灌木,感觉真是熟悉、亲切。也感觉神秘,或许他就在家里,与我只隔着几十米的距离。这些年,我有不少时间我都是在焦西岗度过的。冬天居多,冰天雪地,我们在寨子里走,在大风里走。也有秋天,苹果熟的时候,枫叶红的时候,早晨起来走到苹果树下,踮起脚还不行,干脆跳起来摘苹果。
从焦西岗过去,便是现存最大的白马寨子厄里加。远处山坡上是老寨子老民居,河畔是新寨子,即是住家也是旅游接待点。路边地里的莲花白已经收过一拨,新栽种的还是秧秧。厄里加东边坡上有一片迷人的洋芋地,洋芋苗长得很茂盛,正开着花,有三、四个穿裹裹裙的人在地里除草。一大片洋芋地,满地的洋芋花,三四个穿裹裹裙的白马人转身过来……除此,四下都是安安静静的。
我们的车悠然地穿过寨子,看见一栋栋的木楼,一家家院子,一块块的水泥地,却很难得看见人。那种空寂和安静是悠美的,洁净的,有种打扫完毕等着过年的气氛。我们没有停车,没有下车,偶尔有略显肥胖的白马女人从院子跑出来招呼,问我们吃不吃饭、住不住。我们对她们笑,朝她们招手。我注意到,冬天荒芜的河滩绿草茵茵,冬天荒芜的后山也是葱绿一片。
我没有建议再往里走。再往里走就是华能公司修建的水牛寨水库了,看到我会很难受。水库拦腰切断了夺补河,把水引进了隧道,下面厄里加、焦西岗、罗通坝、王坝楚几个寨子再也没有夺补河流过。在厄里加河畔踩水的情景,在焦西岗河畔看水的情景,都只剩下回忆。早先从厄里加上去,一直都是沿河谷而行,经过稿史脑、水牛寨、扒西寨、刀切寨,然后到祥树寨,三十里河谷的世外桃源的美是属于白马人的,也是属于人类的遗产,而今一个水库淹没了这一切。记得河谷里有好几个坝子,好几处草地,有两处有好几个足球场大,一条来自雪山的野性之河流过,对岸是大片灌木丛。
这当然不是白马人自己的选择。我保存着一些当年移民拆迁的照片——大小领导出马座谈的照片,开大会小会的照片,拆房子的照片。失去家园的白马人会有怎样的感受与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