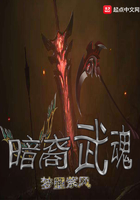沐国恩心想:那顺着东四北大街往南扎就是了,估计也就是三四公里。这算什么兜风呢?西尔维亚似乎看透了沐国恩的心思,冲他挤挤眼:“教授住城里,我住八宝儿山,远着呢!”北京周末不限行,天气又好,街上车水马龙,车开得走走停停。不过四个人都很享受火辣辣的阳光和路人的目光。沐国恩想起上个月在瑞士游山玩水的时候,敞篷车并不少见,只有六七十年代的经典跑车才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还是北京好,拉风的成本低多了。
在东四十条胡同口儿,西尔维亚开口了:“就这儿吧!胡同儿忒窄了。”沐国恩回望她一眼,感谢她的体谅,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开了进去,直到挂着六个大红灯笼的垂花门门口儿。垂花门本是四合院儿里内宅与外宅的分界线,这里成了宾馆的大门,颇有点儿内衣外穿的味道,符合时代潮流,正对沐国恩的胃口。待教授夫妇下车进门后,沐国恩不禁问道:“法国老头儿老太太,干吗非住进胡同里呢?”
“这就是巴黎教授的范儿,”西尔维亚说“巴黎教授”这几个词儿的时候改用法语,故意拖长腔,“我去过老两口在拉丁区的寓所:墙上挂中国字画儿,书架里摆满了线装书。对他们来说,来北京不住四合院儿就跟写法语不加重音符号儿一样大逆不道。
不瞒您说,我原本图方便,也订了这个酒店的客房。下飞机打车过来,司机在胡同口儿就想把我们撂下,我们当然不干。也难怪,胡同儿确实有点儿窄。酒店挺可爱,客房全套儿中式家具,就是小了点儿,他们住的套间才30平方米。再有就是这条胡同儿是单行线,打车进出不方便。”
沐国恩原本以为西尔维亚有点儿矜持,没想到却是个自来熟,英语说起来就跟母语一样流利。“于是您就搬到八宝山去了?”
她又笑了:“逗你玩儿呢!我住励骏酒店,离王府井不远。不过现在我不想回去,能不能兜兜风啊?”“呃……那就先去天安门向毛主席致敬吧!”不一会儿就到了金鱼胡同儿东口,励骏酒店就矗立在东南角儿,华丽的窗饰和膨胀的穹顶带着鲜明的异域风情,如同从法国大都市连根拔起,运到北京,空降下来的一样,与近在咫尺的厉家菜馆儿那气派的王府大门虽然风格迥异,奢靡的气息倒是相通的。励骏和外观简约的丽晶酒店一南一北,像一对门神一样把住金宝街的西端。金宝街长仅仅700米,云集了多个豪华车专卖店,洋溢着蒙特卡洛式的纸醉金迷。
他们一直向南,右拐上了长安街,不约而同地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行注目礼之后,对视而笑。“鸟蛋最近有什么好节目吗?”西尔维亚指着国家大剧院问。沐国恩说:“前两天有《图兰朵》,我去年看过,布景非常壮观。7月初原本安排了俄国女高音安娜·涅特列布科的独唱音乐会,因为庆祝建党90周年推迟了一个月。7月底打电话问国家大剧院,人家说8月2日上演的还是红歌儿会,独唱音乐会取消了。”西尔维亚叹道:
“太可惜了!安娜可是我的偶像啊!当初推迟一个月建党就好了!”“推迟一个月?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中国人民当时水深火热,眼巴巴地盼着他拯救众生,推迟一天建党都等不及啊!”
“哦,抱歉!不过那时候儿水深火热的不只你们中国:贝尼托·墨索里尼1921年成立国家法西斯党,第二年就上台了。”
沐国恩看了她一眼,脱口而出:“就知道你是意大利人。”“哈,马后炮!我都说墨索里尼了。”“是有点儿马后炮。不过维斯康蒂好像是个意大利导演吧,是你的什么亲戚吗?”“呃,他不但是导演,还是共产党员,外加同性恋。不过跟名人攀亲挺没劲的。
我们去哪儿?”她的面颊和胳膊都晒成了咖啡色,开始冒汗。
沐国恩没接她的话茬儿,问道:“安娜是你的偶像,你也会唱歌剧吗?”
“嗯,问题就在这儿。两个安娜都是我的偶像:小提琴手安娜-苏菲·穆特和女高音安娜·涅特列布科。声乐和器乐两样都难以割舍,也都没学出样儿来。到23岁才知道自己虽然有激情肯努力,但是缺乏天赋,于是改学艺术管理了。”“艺术管理?
就是安排、推介艺术团体的演出吗?”“差不多吧!”西尔维亚的神色忽然落寞起来。路过戒备森严的新华门,她似乎被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绿剪边黄琉璃瓦和朱漆门吸引,看着门外八字墙上镶嵌的两条红地金边白字大标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开口道:“里面一定很漂亮。”
沐国恩说:“的确如此。”“你进去过?”“不错,去过三次,第一次还坐汽艇在中南海兜风呢!”看到她满脸的不相信,沐国恩极为受用:“不但进得去,还不要钱呢!平头儿百姓,没有黄马褂儿,照样儿平趟大内!”沐国恩还真不是吹牛。他上初中时就去过两次,一次在春天去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和内容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还有一次是数九寒天去参观流水音、毛主席故居、怀仁堂和瀛台。湖面结了冰,一个男同学踩裂了冰面掉进水里,把他拉出来的时候,他的棉裤和大衣在刺骨的寒风中立刻上了冻。而大片的草地却是绿油油的——地下肯定有暖气。当时沐国恩一家三口儿挤在筒子楼十平方米的斗室里,靠烧蜂窝煤取暖,有过一次煤气中毒的死里逃生。如今头一次看到这种为绿地保温的做法,觉得既新奇又有档次。
第一次进中南海无疑才是最难忘的。那是1981年,沐国恩正在芳草地小学上三年级。芳小当时是北京唯一接收外国人就读的小学,有点儿国际学校的味道,其实中外小朋友分别在不同的教学楼上课。除了新年联欢交换礼物之外(他本人曾用一块义利威化饼换来一支铅笔,觉得亏了),中外学生平时并无什么交流。
大批西方管理和专业人员以及缺乏管理或者专业背景的人员来中国淘金是很久以后的事儿。改革开放之初,外国生源主要来自驻京外交官子女,在芳小似乎还是以亚非拉孩子居多。在这些外国孩子里,沐国恩当时唯独觉得着裙装的朝鲜女孩儿有几分姿色,但她们都很矜持,从不正眼儿看他。
这京城独一家的国际小学享受的待遇自然与众不同:离六一尚早,小伙伴儿们就纷纷议论儿童节会参观连成年人也很难有机会去的地方:人大会堂、建外国际俱乐部、中南海。沐国恩去年已经去过人大会堂了,这回一心想去中南海。谁知天不遂人愿,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于5月29日与世长辞。国丧期间,娱乐自然告停,六一节便在对宋主席的默哀中度过,芳小的孩子们遗憾不已。好在国恩浩荡,暑假期间安排了娱乐活动,算是给他们补过儿童节。于是在8月份一个凉爽的上午,沐国恩与幸运的同学们终于有机会参观向往已久的中南海。泛舟湖上,清风拂面,垂柳依依,妙不可言。而且那次令别人艳羡的一日游没有让他花一分钱:接他们往返的车辆都是学校安排的。
“现在可就没机会了。”沐国恩唏嘘不已。两人一时无话,继续前行。西长安街一如北京的其他大街,充斥着二三十年来新建的办公大楼和购物中心,三味书屋的屋瓦、民族文化宫的白墙、广电总局的尖顶、首都博物馆外墙上的青铜塔楼点缀其间。在北京,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建筑比肩而立,对比鲜明,如同百多年来左右中国的各种政治思潮一样势不两立。想到这里,沐国恩说道:“欧洲城市的建筑风格似乎比这儿更协调,古典式、文艺复兴,要么就是新古典或者折中风格。不过北京这种针锋相对的建筑格局也有它的好处。”“怎么讲?”西尔维亚笑问。“不会让游客腻味呗。小胡同儿、大皇宫、老宅门儿、新商场,明清宫殿园林,近代西洋楼,斯大林式建筑群,开放后出现的玻璃幕墙高层建筑,各投所好,各取所需。”他把车开进三里河儿路的辅路,在银杏树荫下缓缓停下,去路边商店里买了两瓶儿冰镇的康师傅冰糖雪梨,递给她一瓶儿:“歇会儿,不妨躺在车里日光浴。”
西尔维亚耸耸肩:“没带防晒霜。”从小挎包里掏出黄色外壳的“爱疯”手机,戴上橘红色镰刀形耳机。沐国恩指着汽车音响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她心领神会,随即把手机馈线插入音响,节奏鲜明的欢快旋律顿时飘溢出来。原来是吉卜赛国王组合用西班牙语翻唱的老歌儿《飞翔》。音乐比冷饮还要提神儿,几乎令人手舞足蹈。这首歌儿诞生于中国砸锅打铁“大跃进”
的1958年,是欧洲电视歌曲大赛中意大利的参赛歌曲,最终取得第三,并在翌年的首届格莱美大奖中被评为最佳唱片和最佳单曲。歌词把情人的双眼比作星空,写得相当浪漫。
“真想听听您歌剧唱得如何啊!”沐国恩喝光了饮料,悠悠儿问道。西尔维亚郑重其事地清清嗓子,两手相握,摆好造型,却说:“哟,没伴奏啊!”沐国恩笑了:“欺负我外行是吧!晚上带你去基辅餐厅,见识见识乌克兰的歌手。”“嗯,听说过。”“不过为了艺术可得做出点儿牺牲:那馆子的俄国菜也就那么回事儿。”如果说北京展览馆院儿里富丽堂皇的老莫代表了苏联50年代的辉煌,屈尊栖身在西三环外逼仄胡同儿里的基辅餐厅可算是苏联解体的佐证,在那儿花百八十块钱就可以请所谓“乌克兰功勋歌唱家”在顾客面前引吭高歌。“为什么不去莫斯科餐厅?”
西尔维亚问道。沐国恩说:“我觉得莫斯科餐厅的建筑比烹饪水平高得多。开放前莫斯科在北京算是首屈一指的西餐厅,如今嘛,最受欢迎的西餐肯定轮不到俄国菜,地道的西餐饭馆儿恐怕都在东边儿吧。我去基辅餐厅是为了听歌儿,去老莫儿则是为了怀旧,而且是替父母怀旧。当时全国崇尚苏联,比现在崇尚西方更盲目更狂热。”“你替父母怀旧,怎么讲?”“我爸当年请我妈在莫斯科餐厅开过洋荤。”沐国恩想象着当年老爷子如何跟妈妈套瓷,不觉笑了。
基辅餐厅门脸儿虽然不体面,人气却一直很旺,或许就是因为表演吸引人吧。沐国恩照例点唱了雄壮的《苏联国歌》和父母最喜欢的情歌《遥远的地方》以及几首意大利歌曲。乌克兰的男高音看见与沐国恩同来的西尔维亚,显得有点儿人来疯,唱《我的太阳》和《说你爱我,玛丽欧》比以往更加卖力。沐国恩正觉得意犹未尽,却见西尔维亚频频看表,便问缘故。她说:“和女儿约好在9点半视频通话。”沐国恩这才注意到她左手戴的婚戒。
夜色中的长安街灯火通明,热闹不亚于白天。沐国恩贫了一下午,送她回酒店的路上却无话可说了,道别时才问起他作为志愿者的工作安排:“哪天需要我接送?”“周一早上十点在阅微庄碰头儿吧。我自己过去,甭接我了。”“行。哦,出门儿上街,戴耳机听音乐时当心小偷……”“当然,多谢!在罗马就是在听歌儿的时候被人偷过iP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