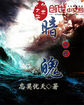众人无不伤心落泪。
小钢炮哭着对春水说:“春水,就让她回家看一眼吧……”
春水抹了一把泪水,上前搀扶着花倩倩走出了船舱。众人急忙出舱尾随,缓步向岸边走去。码头的坡上坡下,跪满了寿州人。从下往上看,一排排,一溜溜,层层高去,如同一座人山。开始是哽咽声,听到花小姐那揪心的哭声,便开始了号啕。偌大的下码头,笼罩在一片哭涛声中。
这时候,突然有人跑来告急说:“黄满贯要以亲家身份前来收拾残局,马上就要到花府了!”这消息如同炸雷,一下把众人炸蒙了。哭声悄然低落,码头上相继静了下来。人们都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春水,像望着一位能解救众生之苦的菩萨。这始料不及的消息,也惊得春水不知所措。许久,他才使自己冷静下来,说道:“先让倩倩小姐回避一下,我们几个去看看!”说完,让人搀扶着花小姐重返舱房,随后就领着几位头面人物上了码头,直奔花府而去。
四
花家庭院逐年外扩,已很气派。大门朝南,青狮把门,面对颍河边的大马道。后门朝北,出门便是大街。砖铺的甬道直通大厅,路两旁皆是花圃。迎春、探春、牡丹、吊金钟散发着幽香。大厅盖得很讲究,筒瓦兽脊,巍巍峨峨。雕花门窗,双双对开。明柱直立,雕梁画栋。厅内方砖铺地,芦苇棚顶。外墙似切,内墙似雪。大厅外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月亮门。后院是三进深。东西厢房,均是出厦走廊。门前各栽数株桂花树,双排对立,遥遥相看。这中间有个小花园,玫瑰、芭蕉、棕榈……多为南国树种。曲径通幽处,正中是六角门。进得门来,是一个小小方院。花草异木,满院皆是。柳垂金丝,桃吐艳红。山石之后,是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许多豆子大小的小青杏。靠后处一幢小阁楼。这阁楼式样考究,通一个“木”字——木梯木门木走廊。走廊的扶手、栏杆皆是柿木,雕花别致,做工精细。相间处的方形或菱形木雕,更为绝妙,多是历史掌故或戏剧故事。诸如《状元及北》、《沣矶访贤》、《昆仑寿星》之类应有尽有。或山或水,清秀精美;或人或兽,栩栩如生。尤其《鹊梅登枝》,更为佳绝,人见那浮雕上,枯枝纵横,红梅朵朵,有的含苞,有的绽开,隐隐还有似浸染过烛光的红色交映。枝头几只喜鹊,神态各异,生动欲出,再看片片鹊翎,雕刻得羽绒折叠,细若发丝……绝对出自江南雕林高手之手!走廊里花盆比比皆是,兰花、墨菊、仙人掌……花儿有开有谢,叶儿有黄有绿。品种不一,雅而不俗。楼下五间,台阶高出三尺有余,须拾级而上。楼上五间,别有洞天;竹帘掩门,香气袭人——这就是花小姐的闺房。
当初的时候,花小姐在镇西山陕会馆里读书。花庭芳而立之年得娇女,自然视为掌上明珠。颍河镇素有五里长街之称,小小幼女会跑伤腿的。花庭芳托船老大在蚌埠买回了黄包车,派专人拉倩倩学堂就读。
每天拉花小姐上学的,就是常春水。
春水比倩倩年长五岁,他就是当年第一个在颍河镇落户的寿州人的后代。春水的父亲常秉光是码头上的“号子头儿”,自然也是码头工的首领。码头上的重大商务,花庭芳多请他参与交涉。当然,花家对常家也照顾得好一些。比如春水拉倩倩上学堂,就是别家孩子捞不到的美差。
每天早饭吃过,倩倩坐上黄包车,由小春水拉着穿街过巷到镇西。小倩倩方满七岁,赶到上坡,见到春水那吃力的样子,便学大人赶牲口一般“吁吁喔喔”地叫了几声。谁知这一下竟惹怒了小春水,他扭脸喝道:“你再叫我就把你掀下去!”倩倩以为他开玩笑,不服地说:“你敢?”小春水二话没说,一放车把,把倩倩摔了个倒栽葱。倩倩头上撞起了大包,哪里会依?哭闹着回府禀告爹爹。
倩倩哭着头前走,春水怒气未消地拉车随后跟。回到花府,倩倩向父亲哭诉了挨摔的经过,颇使花庭芳恼火,他呵斥春水道:“你这孩子,我好心待你,为何不识好歹?”
“她为何把我当牲口?”春水理直气壮地说。
“有这等事?”花老板问女儿说。
倩倩揉了揉眼说:“我和他闹着玩嘛!”
这时候,赶巧秉光来向花老板说事,一见倩倩头上的包,便知出了岔子,什么话没说,拉着春水就打。花庭芳急忙拦住。常秉光余怒未消地命令春水说:“跪下!给小姐赔不是!”
春水昂首硬腿,把脸一扭,犟道:“不怪我!”
“跪下!”常秉光呵斥道。
没想春水突然大叫一声:“我不干了!”说完,扭身即走。
常秉光上前一把拽过春水,正欲猛打,被花庭芳拦下。花庭芳望着倔犟的小春水,转怒为喜道:“好小子,像个寿州人!老常,若不是倩倩许了黄家,怕我要和你成为儿女亲家哩!”说着,拉过倩倩说,“今儿个惹事的是你,向你春水哥道个不是!”常秉光哪里肯依,忙命春水拉过了黄包车……
到了学堂,倩倩入学,春水无人玩耍,甚觉无聊,便倚在门口偷瞧。谁知他越听越入迷,竟也用小棍在手上地上写写画画。放学了,他又商量着借来倩倩的书,趁饭时重读一遍。日子久了,他比倩倩还透。每每遇难题,倩倩均是求他。有一次,课上到中间,老学究突然来了兴致,出了一个上联:“柳絮蕴奇梦”,要求学生对出。全堂学生目瞪口呆,有几个举手答对,老先生均摇头缄口。小春水耐不住,脱口说道:“桃花藏仙境。”老学究一听大喜,抬头望去,见是花家小姐的拉车的,更是惊奇,走上前问道:“你认字?”
倩倩禁不住心里高兴,说道:“他比我学得还好!”
老学究随意出了几个题,春水对答如流。先生见春水天资聪明,大喜,便开恩给了他个后排位,并送给了他一本书,让其当个免费旁听生。
倩倩在山陕会馆里读了近七年书,春水也跟着读了近七年书。后来倩倩随舅父去了汉口,春水便上了码头。老学究几次寻找春水爹商量让春水继续学业,常秉光都苦笑回道:“唉!我怎能供得起呢?”
春水上码头的第二年,老父被盐包砸伤,染疾而死。在花庭芳的推荐下,常春水接了父亲的班——当了“号子头儿”。
船老板的势力再大,进了港要听码头工的“号子”,这是多年来约定俗成的老规矩了,所以客商和船老大若想早装早卸,均得巴结“号子头儿”。
“号子头儿”不但有权威,也需有极高的威信,否则,众人不服。威信之说,无外乎那么几条,一是心地正,二是活路上是把好手,三是善于交涉应酬、多为工人说话……如此而已。
常春水二十岁上码头,正是血气方刚年岁,骨子虽嫩,心眼却扎实。他深知自己当头儿是父亲和花老板的面子,自己若打天下,使码头工心服口服,必得显露几手方达目的。开始的时候,他不多言语,双目老在活路上瞅巧儿。等身子骨练硬了,他处处不让人,披单一披,麻利又爽快。加之他有眼力,沿跳板上大垛,无人不服。尤其木材摽筏的技术活,后生中非他没别人了!他嗓门也亮,喊号子极有韵路,格外耐听。每每商船要拢岸,他便站在高头,手举着洋铁皮卷成的小广播筒喊号子:“郭家商船拢岸——靠上头——西边一码脚——”
春水还住在他上辈佃下的老宅里,紧靠码头,两间破房。院落不大,残墙只剩半人高。父亲死后,他更无心修缮,任其败下去。他母亲早死,父亲领着他和姐姐度日月。后来姐姐嫁给了李豁子的船工,随船下了淮河。早晚路过这里一趟,走娘家像讨个火似的。有一次因一件小事春水和姐夫闹了气,便不常来往了。父亲死时,姐姐来哭祭一回,从此更不见回娘家了。春水并不感觉这么过有什么。因为他有学问,工余小憩或过年过节,众人听他讲《三国》、说《水浒》,几个后生听入了迷,干脆来与春水一同住了。
春水说起故事来滔滔不绝,平常却极少言语。他把一切都藏在心底,从不向人透露半分。书本丰富了他的知识,使他变得老成又有心计。为得到寿州人的爱戴,他总是吃苦在前,乐于助人。由于码头弄得井井有条,花庭芳对他也放心。尽管花老板信任他,但他从不像他父亲那样大事小事都往花府跑,只是看准时机去一趟,三言两语禀报完毕,可谓干净利索。
这样一来,春水的两间破草房就成了码头工聚众议事的“忠义堂”。
花家发生滔天大祸以后,下码头停工一天,全体寿州人如同塌了天,哭天号地,无不伤心落泪。望着几具七窍流血的尸首,常春水双目通红。老板一命归阴,“号子头儿”自然成了当家人。他当即召集了刘二楼、小钢炮等几位头面人物,提出三条建议:一是派专人护守庭院,该密封的房屋一定要密封;二是向花小姐电报告急,因为她是眼下唯一的花家主人,一些事离不开她点头;三是告知官府前来验尸并捉拿凶犯……
“干脆,就直告黄家!”小钢炮满面怒火地说。
“这样怕不妥!”春水扫了众人一眼,分析说,“拿不出证据的乱告为诬告!再说,捉拿不到春嫂,怕这案子也就成了悬案!眼下最当紧的是捉凶犯,保码头!黄家灭花家,目的已众所周知:是想娶过花小姐,暗度陈仓,把花字码头变为黄家码头!若花小姐答应黄家婚事,我等怎么办?若花小姐不答应婚事,黄家逼婚或告官,我等又该怎么办?”
一连串审时度势的分析,顿使众人口服心服,但也感到压抑,大有末日来临的预兆!问题的紧迫和严重很明了:若码头改花姓黄,这偌大的花家庭院再不是寿州人的出入之地了,寿州人的“五五”正提就要变成“三七”倒提,生活无着不说,挨打受气是定了的!眼下明知是黄家的阴谋,可抓不住人家的把柄能奈何呢!再说,黄家家大业大势大,谁能惹得起呢?
几个人不由你看我,我望你,均缄口了。
好一时,刘二楼才叹气道:“唉!这都是花掌柜自个儿种下的恶果呀!”
“当初他不听咱劝说,还担心是咱想怎么着呢!哼,不亏他!”小钢炮一股懊悔怨恨,说出了大伙儿不愿在这种时候说出的话。
高半截看了春水一眼,胆怯地劝小钢炮说:“事……事情到了这一步,也不必抱怨了!”
“是呀!”常春水沉思着,顿了一会儿,又分析道:“眼下非得破罐子破摔不可了!先告急花小姐回府是第一步,若她答应婚事,我们几百口子寿州人就跪地不起,使其心软下来!这一条并不难,因为我了解花小姐,她压根就不喜欢黄音那小子!难的是下一步,若花小姐不答应婚事,黄家就要告官逼婚!若捉拿不到春嫂,挖不出后台,这大理全在黄家那方,咱用什么办法能保住花小姐呢?保不住小姐,这码头只好做嫁妆了!”
“罢工!外边到处罢工,咱们也罢他个小舅子一回!”小钢炮激动得满口喷沫,恶狠狠地嚷。“罢工是怎个罢法?咱谁也没见过,怕闹不成哩!”刘二楼像预感到了什么,面目阴沉地说,“不管用什么法,咱寿州人一滴血一滴汗挣来的花家家业,决不可轻易让人!”
“那咱们寿州人就应该精诚团结,一斗到底!”春水庄重严肃地看了看众人说:“罢工可以,但我们一家是斗不了黄家的!若能争得上、中码头的哥儿们帮帮忙,用此要挟黄家退婚是目前的上策!当然,若花小姐能支持我们,这事情就会好办一些!”
……尽管常春水料事周密,但黄满贯在这个时候登门确是他始料不及的!一路上,他不免心事重重,面目沉郁,猜测着黄满贯来花府的目的以及如何应酬……忽听一声高喝,黄满贯已在众人簇拥之下到了花府大门前,正与常春水他们迎面而至。
黄满贯花甲之岁,身穿长袍马褂,头戴茶色金丝边礼帽。方方大脸,浓眉亮眼。由于上了岁数,大眼睛开始松陷,厚厚的泪囊成了三角袋。端正的鼻梁直冲鼻宇,透出一股威严之气。他手托黄铜烟袋,缓步走了过来。
常春水急忙抢前一步,拦住黄满贯,双膝扎地,先叩了头。除去怒目的小钢炮外,刘二楼和高半截也相继跪倒在地,向黄老爷请了安。黄满贯大度地瞥一眼一旁立站的小钢炮,上前搀起众人,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面目阴得能拧出水。许久许久,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摆了一下手。
常春水等人头前带路,过大厅来到东厢房,四具尸首用单子蒙了,全放在这儿。黄满贯挨个儿掀开看了,目光里透出悲哀,然后掏出绫绢擦了一下双目,立在花庭芳尸体前头深深地鞠躬,惋惜万分地说:“花兄,怪我回晚了……”好一时,才缓缓地转了身问春水道:“报官了吗?”
“我们报过了!”小钢炮火火地望着黄满贯说。
黄满贯不瞧小钢炮,仍盯着常春水。
“他们已验过尸,实属砒霜毒死!”春水回答说,“可不知为什么,他们一直未派人捉拿凶犯!”“这种大案,还推什么?再推几日,凶犯逃之夭夭,看他们如何了事!”黄满贯颇显气恼,说完话好一时,面部凶气未退。
“我明天就准备再次催他们!”常春水苦恼地说,“时局太乱,他们并不把这看成大案!”
“屁话!军阀混战,百姓遭殃,这还不够吗?”黄满贯气咻咻地说,“几条人命不为大案,成何体统?”
“我等定加急火催!”
“万不得已,可以拿上我的帖子!”黄满贯突然又盯着春水问道:“听说倩倩回来了?”
黄满贯突然杀来这一枪,颇使常春水等人不知所措。刘二楼和高半截面面相觑,脸上不由掠过惊恐之色。常春水窘了片刻,随机应变道:“是呀,可她刚到家就哭背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