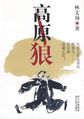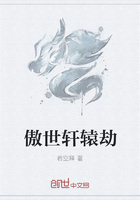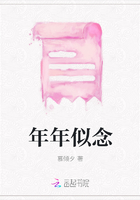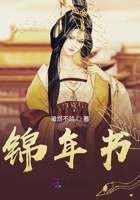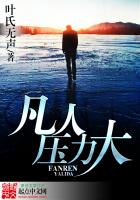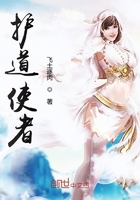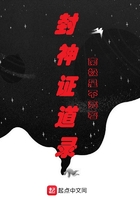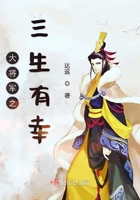颍河镇距寿州老远,可镇子里却多有寿州人,多得组成了一条街。
寿州出了个孙状元,
淹三年,旱三年,
淹淹旱旱二十年,
富豪人家卖田地,
穷苦人家卖儿男!
……
据传皖地不宜出官,出官就是遭晦。先前出曹操,六十年不停地动刀枪,亳县遭殃,孟德举家皆死于非命。后来冒出了个朱元璋,除去马娘娘享上了荣华富贵外,大多凤阳人却多年不得安生。再后来,就是这位凑热闹的孙状元,像是把“地气”一下拔尽了,更是苦煞了寿州人。连年闹不出粮食,家有万贯搁不得颗粒不收,日不进分文。人们为糊口而背井离乡,往南、往北、往东、往西,华夏虽大,但到处都有寿州人。
颍河镇,属河南地界,背靠颍河,前临汴京通往皖地界首、蚌埠的土官道,号称水旱码头。各家商船、骡马客商,南蛮子北侉子,山西、陕西的老商贾,都云集到这儿做买卖。三里长街,从头至尾飘荡着生意幌子。商店药号,烟馆粮坊,六行经营,八道交易……全了。
颍河街有一座关帝阁。从关帝阁往南走,是一条小街,又破又短,直通颍河,由于街短偏东,竟被本地人和外埠的生意人冷落了。早先的时候,来了两户讨饭的寿州佬,夜里宿在关帝阁,白日沿街乞讨。由于这地方能糊饱肚子,他们在河沿处搭了窝棚,安下了家。后来又来了几户皖南同乡,亦学他们的样子住了下来。本地人原以为他们是暂住,谁知他们竟慢慢扎下了根。再后来,又从寿州过来了一位有钱人,看中了这条短街,便连同河坡一起买了下来。
民国十几年的时候,这些寿州人的后代繁衍生息,寿州街亦越发名副其实了。
也就是在这个当儿,寿州街发生了一桩稀奇古怪的大惨案……
一
这一日,早集刚散的时候,从颍河南岸摇过一叶小舟。舟上站着一位少女,十八九岁,留着齐耳短发。刘海儿剪得俏齐,似乎盖了眼帘。月白色大襟上衣,紧身细腰,镶着淡蓝色的边。琵琶扣一下扣到领口处,突出了白皙的脖颈。下身的裙子刚过膝盖,长筒丝袜是淡淡的米黄色,幽幽地闪着光。带襻的新式皮鞋跟部老高,立在船头禁不住朝前倾身,胸围显得格外高耸,后腰朝里凹,臀部自然出现俊美的弧线。近了,方见女子长相不俗,一派大家闺秀的气质。鸭蛋形的脸盘,杏儿似的眼睛。迎风甜笑,玉齿微露,酒靥初现,像朵似开未开的花骨朵。
河水浪拍驳岸,哗哗作响。春风送来对岸柳林桃林李林醉人的芳香,令人心爽。一个浪头打来,小船颠了一下,只见女子腰一闪,风摆柳般晃了几晃,更见婀娜。等船拢岸,她手提皮箱倏地跳起,如春燕点水着了地,朝老艄公分寸恰当地回眸一笑,正欲前行,却被一人拦了路。
“花小姐回来了?”那人双手一拱,施礼问道。
“嗯……”花小姐下意识地用绫绢半掩桃口,薄面略略含嗔,羞怯怯地盯着那汉子。
这人瘦高,上下一溜子,活脱一条带鱼。那脸瘦长,那眼小精,一笑面部堆沟沟。他见花小姐生疑,忙说道:“你不认识我了?”说着,那长脸顿起恭维,“哎呀,真乃贵人多忘事——再仔细瞧瞧?”
“噢——”花小姐终于轻轻嘘了一口气,叠了手帕,面部溢出笑意和惊讶,“我记起了!你是葵花杆——对不?”
“对对对……哎呀呀,花小姐能记起我来,可真是活增我的阳寿哟!”
“你还在码头?”
“那可不!”
“春水呢?”
“他在那儿——”葵花杆顺手一指,把花小姐的目光带到了下游的远处。
拉纤号子隐约传来:
哎嗨子!嗨——喂喂!
哎!打摆好日喂,嗨喂喂!
天上小黄河哟,
小河九道湾哪!
头道窄来二道宽,
三道湾里老龙潭
,四道湾里能行船哪……
遥望颍河,如一条巨龙,莽莽苍苍,翻滚奔流而下。蓝的水,青的树,好一幅动人的水墨丹青!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满目堆青叠翠之中,点缀着一簇簇红的、黄的、白的、紫的花。
浓郁的幽香飘袭而来,熏得人醉。涌金叠银的河面,百舸争流,帆影相叠。偌大的河湾里,商船济济,桅杆林立。起锚声、抛锚声,拉纤号子、出航号子、挑担号子、上垛号子,此起彼落。“喂哟来,喂哟吼”的打篷号子刚刚传来,雪白的大帆就涨满了风,像一把巨大的切面刀屹立在空中……好繁闹的码头!
“啊——”花小姐禁不住扬开双臂,激动地说,“光阴荏苒,转瞬六年!可爱的故乡,我回来了——”
“屁!这儿可不是咱们的故乡!别忘了,咱们是寿州人!”葵花杆望着花小姐说,“就是寿州人让俺来这儿等你哩!”
“嗯?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花小姐稍有不悦地睁大疑问的眼睛。
“花小姐要回的消息早已传遍了颍河镇,连毛孩子都晓得哩!”
“是吗?”花小姐又掩不住地兴奋,甜甜地笑了笑。
花小姐十三岁随舅父去汉口上洋学,没想今年年初舅父病故。她正要求父亲供她读完大学,不料父亲电报告急,非让她速回故里不可。她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便匆匆告别了年迈的舅母,急急搭上了往北的火车……
想起父亲的电报,花小姐禁不住有点犯急,对葵花杆说:“这样吧,等我回家给爸爸说一声,然后就去码头!”说着,拎起皮箱就要上岸。
葵花杆一听小姐要回家,面部掠过一丝惊慌,急忙拦住花小姐,讪笑道:“嘿嘿,花小姐,你不是想见见春水吗?”
花小姐双颊泛起红润,嗔笑道:“你这人,真是!”
“从下码头回府,既见春水又见乡亲,可算一举双得哩!”
花小姐犯愁地迟疑片刻,终于朝葵花杆点了点头。葵花杆受宠若惊,急忙接过皮箱,领花小姐顺河滩往东走去。
二
“花小姐回来了——”
葵花杆的喊声刚落,人们便一传十、十传百地相互小声传告,偌大的下码头顿时静了下来,几十条船上的号子声亦戛然而止。码头工,密密麻麻的挑夫、担夫以及外地运货的车夫和拾捡物什的老妪、少妇、娃娃们,都相继关注地转了身,齐刷刷而又木然然地望着几年未见的花小姐。
花小姐先是吃了一惊,以为众人犯了什么邪,他们为何敛声屏气,只顾呆呆地痴望自己。一会儿,她恢复了正常,双目透出惊喜和亲切,深情地向寿州老乡望去,还甜甜地报之一笑。接着,她腰一闪,体态轻盈地上了麻石铺的码头场地,向大伙儿招着手,落落大方,潇洒之至。
这时候,只见从一家大商船上走下几条壮汉,为首的是一位年轻后生。那后生身高出众,方面大耳,眉目清秀,嘴角透出一股刚毅之气。只见他缓步上前,双手一拱,彬彬有礼道:“花小姐,请!”
花小姐定睛一瞧,不由怔了。好一时,她才轻声试探道:“你是……”
“我是常春水,花小姐!”
“春水哥——”花小姐一下跳将起来,不顾众目睽睽,竟紧紧拉住春水的双手,一上一下地猛晃,口中连连怨道,“什么花小姐,我是你的倩妹子嘛!俺给爹爹写信,每回都提到你哩!”春水略显尴尬,黝黑的脸上荡起了红潮,结巴道:“倩……倩、倩倩小姐,请!”
花小姐笑弯了腰,用手帕擦了擦激动的泪水,随春水他们上了一条大商船。
这家商船又高又长,舱深六尺有余,皆是尺把粗的沙杉垒排而成。花小姐随众人下了一个大舱内,舱里很干净,散发着杉木和桐油的清香。这可能是船老大的卧室,很讲究,也很简单,仅一床一桌一凳而已。竹床靠窗铺了。单桌隔“山板”处放了。桌子上除去一把宜兴茶壶和一支黄得锃亮的水烟袋外,还放一本用黄表细纸缉成的“偏开门”账本,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花小姐正看得入神,突然听得春水说:“倩……倩妹子,坐!”
听到“倩妹子”三字,花小姐禁不住面颊掠过一丝红晕。她大方地坐在一张竹凳上,见众人显得拘束,便笑道:“都坐呀!”
众人各寻其位,有的坐在床沿,有的蹲在入口处。春水拉开窗口木板,朝外望了一眼,又急速地合上了。人们神色木然,就那么坐着,默默地抽烟,暗暗地叹气,气氛沉闷得令人发急。常春水端坐桌前,见众人缄口不语,便问花小姐:“倩妹子,这几位你还认得吧?”
“除了这个葵花杆,大都是认得脸叫不出名字!”倩倩望着众人歉意地笑道。
葵花杆耐不住地朝前探了一下身,手指一位身材短小的人说:“他叫高半截,小名臭娃!”
高半截坐在床头,听到介绍自己,倏地弓下了腰,双手如搓绳,末了,方敢做贼似的瞥了花小姐一眼。
蹲在出口处的老汉未等葵花杆发话,便瓮声瓮气道:“姑娘,我叫刘二楼!俺爹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咱两家还有个偏亲哩!论辈分,你该喊我声表叔哩……”老汉说着,竟流出了泪水,慌乱中急促地用手抹了一把。
“光哭顶屁用!”坐在春水旁边的胖汉子早已耐不住,忽地站起,说,“姑娘,俺叫常苦生,绰号小钢炮,爱叫甚叫甚!春水兄弟,快把实情给小姐说了吧!”
花小姐不知发生了何事,双目里充满疑问地望着常春水。
春水望了众人一眼,咽了口唾沫,像是先压抑一下感情,顿了一下,才低沉地说:“倩妹子,催你回府的电报是我等拍的!”
“什么?!”花小姐像预感到出了什么事,紧张得似坐非坐了。“是这样!”春水又动了一下喉结,忙扭了脸,用手抹了一把眼睛,才回首沉沉地说,“大前天晚上,不知是谁……”
“哎呀,干脆直说嘛!”小钢炮性急如火,站起来抢过春水的话茬说道,“黄家想急着娶你霸占码头,收买了给你家做饭的春嫂,用砒霜毒死了你全家!”
“春嫂?她?!”花小姐瞪圆了杏眼。
小钢炮一捶大腿:“跑了。找到现在还没下落。”
“天啊——”花小姐如炸雷击顶,天旋地转面色苍白,一下子昏倒了……
三
众人一见花小姐昏倒,都不由慌了手脚。刘二楼懂得是背了气,急忙放了手中的烟袋,掐着小姐的“人中”,连呼带叫,方使花小姐缓缓醒来。
花小姐恍如隔世,微睁双目傻呆呆望着舱顶,好一时才“哇”地一下放出了悲声……
花小姐叫花倩倩,就是当初从寿州来的那位有钱人的后代。花家上辈买下那条短街之后,正赶上林则徐虎门销烟,草烟逐渐兴开,花倩倩的爷爷便在颍河镇办起了第一个烟厂,雇的大多是寿州人。这些寿州人多年与本地人争斗,早形成了一种抱团思想。花老先生也极注意拢众人之心,常劝诫众乡亲说:“寿州人实乃应与烟厂共存,富则皆富,穷则皆穷!”众人掂轻掂重,自然信他。由于此种“集团主义”作盾,花字烟厂日见红火,连汴京城里的生意人都前来订货了。
颍河镇有一老门大户,姓黄。据传先人曾在京都做过四品官,门楼自然高大。镇里的几大号生意以及酒馆、粮行、中码头、上码头大都是黄家的。年轻少掌柜黄满贯执事以后,更是雄心勃勃。他见花家烟厂生意兴隆,便也办了个烟厂。为挤垮花家,黄家烟厂出的头批货先低于花家两成。生意人大多为见利忘义之辈,他们便蜂拥到黄家门里。花老先生为再次打开销路,不但提高了烟质,而且把烟价降到了黄家以下。黄满贯见花家果然中计,不由窃喜,连连朝下猛降。花老先生生性刚硬,不甘示弱,亦咬牙猛跌。黄满贯见大功告成,便派人化装成客商,一下跟花家签了合同,全包了。没到一年工夫,花家赔光了多年积累,烟厂自然倒闭。
花老先生怎经得起这般气磨?一病身亡了。三百多口子寿州人皆都披孝送殡,丧事摆了整整一道街。
这些寿州人,大多是没田没地者。烟厂倒闭,吃穿无着。会手艺的又开始沦落街头,不会手艺的只得跑码头掏苦力混饭吃。
花老先生归西之后,他的独生子花庭芳掌管余产。这庭芳年轻气盛,扬言要孤注一掷,筹办一座超过上码头和中码头的下码头。人争一口气,神争一炉香。四处逃散的寿州人纷纷回到颍河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硬是帮少掌柜建起了一座大码头。寿州人全成了码头工。花庭芳不负乡亲一片苦心,头三个月不提分文。再后来,也只要了个全河道的最低提成:五五平分。比起黄家码头的三七倒提,可算是天上地下了。
寿州人齐心协力,干活干净利索,取运货小心轻放,很招船主和客商们的青睐。花庭芳薄利广收,极受寿州人爱戴。黄家码头的码头工经常寻衅闹事,而花家码头却置之不理,惨淡经营,吞吐量日益增多。不到十年工夫,花家又跃为镇上的富户。
花家虽家大业大,怎奈人丁不旺。花庭芳的结发妻连生几胎,但只成了一个女儿——花倩倩。花老板为续烟火,东庙烧香,西庙拜佛。三十八岁那年,他又娶了一房妻妾,果然在不惑之年得子,喜得他大贺了一场。为缓和与黄家的矛盾,花庭芳曾托人攀亲黄家,把花倩倩许配给了黄满贯的三公子黄音。这一下,大招寿州人的反对,皆说花老板深仇未报,如今又引狼入室,丢尽了寿州人的脸面!尽管故乡父老如此反对,但花庭芳在这事上却寸步不让。他曾多次开导,声称寿州人目光短浅,并说自己上了年纪,幼子尚小,寿州人若想在颍河镇上立于不败之地,靠不住黄家乃是最大的失策!
可做梦未曾想到,花老板竟自食恶果!每每想到这些,常春水就有一股无名火,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一切都为时已晚。他犯愁地望了望痛哭不已的花倩倩,无奈地对众人说:“事到如今,只好让她先歇一歇了!”说着正欲搀倩倩躺床上,谁知她竟如疯了一般,猛地挣脱春水,高喊着要回府看父看母看弟弟。刘二楼急忙架住她劝道:“闺女,怕你顶不住哟!”说完,也不由老泪纵横。
“松开我!”花小姐已披头散发,脸色如纸一般白,双目似喷火,凄厉地哭喊,“天啊!我可怎么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