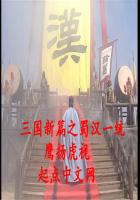次日在冀州府中的议事堂,冀州军中大小一干人等均在厅中落座,公孙度官拜马兵昭信校尉,也在中间寻得位置坐下了。过了不多时,只见太守韩馥和参事刘子惠,后面跟着冀州军马统领潘凤,三人一起由厅后屏风转过而入。待这三人坐好,韩馥说道:“黄巾贼横行多年,虽然贼首已被剿多年,但依然有散匪在我冀州附近扰掠,各位可有什么良策?”
“大人,所谓兵来将挡,这帮贼子相扰我城邦,只要有所发现,我便带兵将其击溃便罢。”潘凤说道。
刘子惠起身对韩馥一拜,说道:“韩大人,我冀州近日多次被黄巾贼的散兵游勇所扰,潘将军虽几次出击将其击退,但这贼子待我军撤后,又继续骚扰附近路往客商,导致我冀州城外三十里处无人敢过,我通过探子来报,说此贼人一伙在附近山中有安营扎寨,我想我们应寻得机会将其一举击溃,方可一劳永逸啊。”
韩馥说:“探子如何报之,你与我详细说来。”
“前不久有贼人在冀州附近被潘将军击溃,我方擒获了几名口舌,经过拷问得知他们在虎头崖的山中搭建营地,已经经营多时。”刘子惠说道。
“哦,已经经营多时了,我等怎地也不知晓。”韩馥一惊。
“得知此事后我已派出探子,昨日探子来报说在虎头崖一处有贼子数千人,依旧是黄巾匪的打扮,均是头戴巾带,那营房壁障也是搭建许久,不知在此谋划什么。”刘子惠说道。
“张角匪首死后黄巾贼已经大乱,其弟张梁引领残匪在广宗被皇甫嵩亲自斩杀,之后群贼无首,凡是没被朝廷通缉的都回故地重新务农为生了,其余的是十几人一伙以抢掠为生,什么时候能聚得起数千人,那探子不是为了邀功,胡诌乱报罢?”潘凤问道。
“此人乃我心腹,回报绝对不会有误。”刘子惠转过身对着潘凤说道“这虎头崖虽然离我冀州不近,但若骑快马也就是两天的路程,我等不可不防啊。”
听完刘子惠说,韩馥缩紧眉头,默默思考不做声。
这时潘凤向前一步举手拜道:“主公莫要担忧,某愿带本部兵马前去剿贼。”
刘子惠忙说:“潘将军不可造次,近日我冀州城外多次被黄巾残党扰乱,往来客商均不敢入城皆绕路而走,若将军引兵出城去虎头崖搦战,那冀州危矣。”
“子惠所言极是,潘将军乃冀州之重,不可擅自而为。”韩馥说道。
“我冀州乃此地一方重镇,大人帐下又是有良将无数,我从那探子得报虎头崖处残匪不过区区千人尔,想必也未立稳,今日大人可派一勇将,配以城中精兵,必能旗开得胜。”刘子惠又对韩馥说道。
“恩,子惠想的周全。”韩馥说罢站起对着议事堂下的众位将领说道:“今日召集各位至此便是为了此事,不知可有人愿出城清剿黄巾残党否。”
公孙度开始听着上面这三人一唱一和早已等的不耐烦,他既知昨日韩馥与他说过此事,便知是太守有意让他立功提拔,待韩馥刚一说出此话便急不可待前身一步答道:“大人,末将公孙度新到冀州便拜昭信校尉,未有寸功不敢居高,愿带人前往将黄巾余党一举击溃以卫我冀州之牢,平百姓之安。”
“好。”韩馥听后大喜“不知公孙小将此次前去需要多少人马?”
不等公孙度回答,站在议事堂厅下稍外的一人又朗声回道:“大人,末将钟快跟随大人多年,未得报效大人之机,今次愿往虎头崖剿灭贼子余党以慰大人之心。”
韩馥一见有多人愿意为此效命,不禁面露喜色,但又露不决之色,只得面授刘子惠说道:“这二将能为冀州之地效命此乃朝廷之福也,只是他二人均乃我爱戴之将,不知遣何人前去,不如让他二人一起领兵去罢。”
刘子惠说道:“大人,虎头崖此处匪患非深,又是残兵败党,何苦用我冀州出两元前去,不如你二人各报之可领多少兵丁前去。”
“大人,刘治中,末将只带三千精兵前往,定可将匪患剿除。”钟快说道。
“大人,小将公孙度只带两千人便可成此事。”公孙度抢着答道。
“大人,请听臣一言。”这时在帐内前台处一亮声幽幽传来,众人不禁全神望去,此人乃韩馥幕僚,姓田名丰字元皓。此人博学多才,在冀州一带广有威望,但性情刚正不阿,出语不顾他人颜面,在此许久不受韩馥待见。田丰一声之后向前踏出未等韩馥答话自己便径自说起来:“钟快乃冀州本地人士跟随大人多年,初为巡查使队深熟冀州城外山脉沟壑,且公孙度乃新进之将,虽有武艺在身不免不熟络于城中将士。所以臣以为可命钟快为前锋讨敌,虎头崖若真是如子惠所说乃黄巾余党,那见我大军临境必四散溃逃,可命公孙小将为后锋,于虎头崖必行之处将其余党尽数剿灭,此患可根除矣。”
韩馥听后颇为拿不定主意,便面色刘子惠。刘子惠见此景便说:“元皓所言极是,但虎头崖乃残党败军之流,不必大动干戈,臣以为只要派一队人马前去即可,公孙度虽是新来之将,但前几日以示武功,此官乃其所得之位,冀州城中军士哪有不服之礼。某以为可遣公孙度自行带兵前往即可,钟快留任城内听候调遣,若有其他事故再行处置不迟。”
“好,好,那就按刘治中的意思。”说罢韩馥站起身,拿出府台令箭说道:“公孙度听令!”
“末将在。”公孙度大喜,跪答道。
“吾授你为剿匪先锋官,都尉护军,授你两千精兵,你可自行前去调配,收拾妥当后明日便前去虎头崖将黄巾贼子剿灭。”韩馥说道。
“末将得令。”
刘子惠这时插话道:“虎头崖乃流贼尔,公孙护军前往后直接大举进攻将其击溃便罢了。”
“谢刘治中点拨,如无他事,末将这就是调配编制了。”
“好,你去吧,明日一早我等在冀州外为公孙护军祭酒。”韩馥说罢,公孙度便拿着令牌离开议事堂下去了。单见厅中无事,其余众将均鱼贯而出,只剩下韩馥,刘子惠,潘凤与刚才那献计的田丰未走。见他人已走田丰又对韩馥说道:“大人,此事交与公孙度颇为不妥,此人初来我处心计莫知,轻易交与兵权恐不易尔。且听得流民报知虎头崖众匪甚有计划,出动策防均不像普通流匪所为,大人还应遣人带兵前去策应不妙啊。”
“元皓你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刘子惠笑道“公孙度前来此处时候不多,正是想效命图功之时,且其父公孙延人在琢培收留流民耕种,已有数千人之势,若此人一心为我冀州谋事,那公孙延岂能不管不问。琢培处近几年不得匪患骚扰富裕盈余,若得知可保我冀州丰足矣。”
“子惠所言差矣,琢培流民为战乱所迫迁徙至此,已是大为不易,怎能将其再次投入这乱世之中呢。况且我冀州粮食富足,虽有流匪作乱但总能保得平安。现朝中有乱臣扰政,我等应以安民为主,广做控民心之策。待到时机成熟可为朝廷顺命保天,岂能乱百姓之生活呢。”田丰再劝道。
“元皓不必再说,我意已决,定要借此将琢培纳入掌中,你若无事便退下吧。”韩馥听后颇为不快,便下了逐客,田丰见此景只得悻悻离开。见此人走了,潘凤便说道:“元皓所言非虚,若照大人安排,这公孙度此次出兵多半不能取胜,我冀州虽富足,但周围诸郡不可不防,尤其渤海袁绍,虽为公所辖之将,但其祖上四世三公,眼下身为司隶校尉,但在渤海招兵买马日夜操练,不可不防。这次遣公孙度领两千精兵前往,若是胜了还好,倘若败了对我冀州也是一大损失啊。”
“潘将军言之有理,以某看公孙度此去必不能胜,但这虎头崖之匪也必为我所剿,事成之后虽伤我冀州两千人马,但获之必盛多矣。”
“哦?刘治中的意思是?”
“只需如此如此”刘子惠便对潘凤布置一番,韩馥在旁不住点头称妙。
公孙度得了将领,急忙赶回府馆,将今日之事与阳仪说了。阳仪听后细细琢磨,让公孙度先行去营房调配人马,并嘱咐虎头崖处多以险峰沟壑而名,此次前去不必选马兵,只得挑选步兵即可,另外攻打山崖营寨当以弓箭为首,另教公孙度多以擅弓箭之人为主进行挑选。阳仪自己留在屋内盘算计划出兵虎头崖之事。
公孙度从韩馥府中出来便往城外营盘去,在城门口忽见一人面善,细细一看原来是今日在议事堂中那位向韩馥提出不建议自己带兵的文人。公孙度自幼脾气火爆,要是换做从前必前去或是羞辱一番或是将其欧之。但这次他身为帐下军将,况且今日在厅堂上见此人与太守对话语气应该是地位甚高,想到此处便纵马向前追上此人做了一拜,可不晓得这个人的姓名,公孙度追了上去一拜却不知说什么怎么称呼,一时将竟愣在那里。那人听得身后有马蹄声便回身细望,一见原来是今日在堂上讨领的新投奔而来的将领。
公孙度见此人回头便说:“末将公孙度,字升济,正要前往营盘调配明日出战之兵,偶遇大先生特前来拜会。”
“公孙护军,你初来此处求功心切我也知道,但这次虎头崖的流匪非平凡之辈,今日我不愿举你为将是为冀州着想,既然太守选你出战那田某自要对你嘱咐几句。”
“谨听田先生教诲。”公孙度以为这人是要故意为难自己,心中不禁开始愤怒。
“冀州地形不知你可熟悉,”这人一问见公孙度没立即作答便接着自己说下去“这冀州之地看似乃平原之所,可据城外三十里后便是群山众峦,尤其以沟壑山涧居多。虎头崖地处凶险你这次去调配兵员务必以步兵为主,决不可带骑兵进山。另外这如真是山匪据寨那必是兵具不全,你只要多带弓箭前去不必着急攻寨,只围不攻,留条生路,那群匪必然溃散。你务必记好。”
此番言语一出,大大妙过刚才阳仪与公孙度所说,听的公孙度心中豁然开朗,连忙从马上滚落下鞍,重新对着这人深深一拜。说道:“公孙度虽年幼操练习武,但不善于兵法钻研,今日听得先生一席话深受启发,望先生再赐教一二。”
“公孙护军不必多礼,田某今日还有要客回见,现在时候已经不早,如有机会再于公孙护军相聚你我再谈不迟。”说罢便对着公孙度行礼一拜,接着自己转身骑马而去了。
公孙度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不敢强留,想到今日大事乃选兵征讨,便急急前去城外营房调兵,闲话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