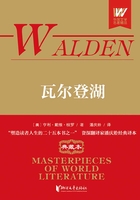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京官中,四品而掌印的,只有这么一个。做祭酒的,生活实在颇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在门口喝一声短道,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清朝时他们还有两桩特殊任务:一是每年十月初一,率领属官到午门去领来年的皇历;一是遇到日蚀、月蚀,穿了素服到礼部和太常寺去“救护”,但领皇历一年只一次,日蚀、月蚀,更是难得碰到的事。戴璐《藤阴杂记》说此官“清简恬静”,这几个字是下得很恰当的。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朝廷似乎也知道这种心理,所以,除了特殊例外,祭酒不上三年就会迁调。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
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国子监一没人打官司告状,二没有盐税河工可以承揽,没有什么外快。但是毕竟能够养住上上下下的堂官皂役的,赖有相当稳定的银子,这就是每年捐监的手续费。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须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
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按“千字文”数,有一个字算一个字,平均每年约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说,国子监还有许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厅的刷印匠,管给学生“做卷”——印制作文用的红格本子,这事包给了他,每月例领十三两银子。他父亲在时还会这宗手艺,到他时则根本没有学过,只是到大栅栏口买一刀毛边纸,拿到琉璃厂找铺子去印,成本共花三两,剩下十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烩鸭条才一吊四百钱一卖!至于那几位“堂皂”,就更不得了了!单是每科给应考的举子包“枪手”(这事值得专写一文),就是一笔大财。那时候,当差的都兴喝黄酒,街头巷尾都是黄酒馆,跟茶馆似的,就是专为当差的预备着的。所以,像国子监的差事也都是世袭。这是一宗产业,可以卖,也可以顶出去!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新中国成立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一九五七年
昆明的雨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左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
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
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段多放蒜,否则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
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至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儿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有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扳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阶石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间娇娇的。她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是像一球烧得炽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把儿兰”(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这种花叫做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它和兰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熙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看了着比丘尼装的陈圆圆的石像(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雨又下起来了。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瓷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我想念昆明的雨。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
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
香港多高楼,无大树。
中环一带,高楼林立,车如流水。楼多在五六十层以上。因为都很高,所以也显不出哪一座特别突出。建筑材料钢筋水泥已经少见了。飞机钢、合金铝、透亮的玻璃,纯黑的大理石。香港马路窄,无林荫树。寸土如金,无隙地可种树也。
这个城市,五光十色,只是缺少必要的、足够的绿。
半山有树。
山顶有树。
只是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些树,欣赏这些树。树被人忽略了。
海洋公园有树,都修剪得很整洁。这里有从世界各地移植来的植物。扶桑花皆如碗大,有深红、浅红、白色的,内地少见。但是游人极少在这些过于鲜明的花木之间流连。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乘坐“疯狂飞天车”、浪船、“八脚鱼”之类的富于刺激性的、使人眩晕的游乐玩意。
我对这些玩意全都不敢领教,只是吮吸着可口可乐,看看年轻人乘坐这些玩意的兴奋紧张的神情,听他们在危险的瞬间发出的惊呼。
我老了。
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我在香港极少逛街,张辛欣说我从北京到香港就是换一个地方坐着),想起北京的大树,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的柏树,北海的白皮松。
渡海到大屿岛梅窝参加内地和香港作家的交流营,住了两天。这是香港人度假的地方,很安静。海、沙滩、礁石。错错落落,不很高的建筑。上山的小道。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需要清闲。
古华看看大屿山,两次提出疑问:“为什么山上没有大树?”他说:“如果有十棵大松树,不要多,有十棵,就大不一样了!”山上是有树的。台湾相思树,枝叶都很美。只是大树确实是没有。
没有古华家乡的大松树,也没有北京的大柏树、白皮松。
“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是不成其为故国的。《金瓶梅》潘金莲有言:“南京的沈万山,北京的大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大树就有了名了。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
回北京,下了飞机,坐在“的士”里,与同车作家谈起香港的速度。司机在前面搭话:“北京将来也会有那样的速度的!”他的话不错。北京也是要高度现代化的,会有高速度的。现代化、高速度以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想起那些大树,我就觉得安心了。现代化之后的北京,还会是北京。
一九八六年二月
西南联大中文系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
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坐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
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