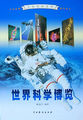骄阳热烈地洒向大地,池塘边堆满了干枯的荷叶,青蛙有气无力深一声浅一声地叫着,树上的知了倒是无休止地聒噪。院子里的青梅,莲藕已经接近成熟,柿子已经结出青绿色的果实。
梁佑坐在躺椅上闭目养神,不知觉的,之前遇见的人,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涌现在脑海。到头来,只化为一声哀叹。
梁佑忙招呼来张充,刘松,“兄弟们,我们是时候该走了。”
“可是大哥你的眼睛!”张充说道。
“不碍事,我眼睛虽然不太方便,但能大概看到人物的轮廓。”
梁佑向卞神医请辞:“佑等人连日叨扰,造成不便,敬请见谅!”
卞神医正在磨药,听到这里,停了下来,“先生真的决定了吗。”
“决定了,神医之恩,来日再报。”
“罢了,罢了,你的眼病可以医好,但是你的心病我却无可奈何,还是走吧。”卞神医说道。
梁佑走出了卞宅,轻轻的合上了门扉。
梁佑刚走,阿靓从门后出现,“师父,草药采好了。”
“阿靓,那位梁先生可是你的旧识?”卞神医问道。
“啊……那里啊……师父,我根本不认识他。”
“好吧,我也不管你的过去了,我就想说一点,在这乱世之中,好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就像这飘零的浮萍,随风摇曳,你要学会正视自己的过去,懂吗?”
“恩……,阿靓明白,阿靓能跟着师父已经是三生有幸,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唉,世上无情,而人自有情,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卞神医说道。
梁佑辞别了卞神医,会合了李岩,一路往太原赶来,这一天路过浮桥镇,梁佑的眼疾恶化,疼痛难忍。张充请了一位郎中给他瞧病,郎中摇了摇头,表示无可奈何。张充性急,拿出手枪对准郎中的太阳穴,“快点医治,否则一枪崩了你!”
刘松来制止他,“二哥先别这样,何必为难一个走江湖的郎中呢?”又对郎中说道:“你先给我大哥开点止疼药。”郎中刚才已经吓得半死,听到刘松这么一说,唯唯诺诺地点了点头。张充也把枪给收起来。
梁佑服用了止疼药,疼痛有所减轻,李岩辞别了梁佑回到了东城,梁佑出了镇子来到通向太原的官道。
“奇怪,怎么会这么安静呢?”
“怎么奇怪了大哥?”张充问道。
“三年前我路过此处时,在此借宿一宿,沿街店铺兴隆,半夜不息,街上人虽不算熙熙攘攘吧,但也是川流不息,怎么到了今天会这么安静?”梁佑说道。
“我们也不知,大概迁徙走了吧。”刘松说道。
时近中午,梁佑三人找到一家客栈吃饭,点完三菜一汤过后梁佑问店老板此地发生何事?
店老板拨弄着算盘,头也不抬地说道:“客官是从外地来的吧,我们这浮桥镇两年前便是这样,人越来越少,我这生意越来越难做咯。”
梁佑说道:“我看此处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我虽不太懂风水,但也能看出来此地是风水旺地,离太原也不过百里,怎么会没人居住呢?”
“唉,客官有所不知。”店老板停下手中的算盘,“三年前我们这里还好好的,百姓安居乐业,虽比不上太原的荣锦繁华,但也算得上是欣欣向荣,可是自从三年前阎锡山上任后,为了西北剿匪,穷兵黩武,大肆征兵,而且赋税加重,太原近郊士民携家带口逃到外地,再加上荒年干旱,就更加不妙咯!”
梁佑心想“我看阎百川有治国之才,辅佐他当了总督,不曾想却看走了眼,唉!”
“客官,我今日说的纯属市井小民的茶余之谈,你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讲哟!”店老板说道。
梁佑答应了他。酒足饭饱后张充买了辆马车,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赶到了太原。
到了太原,梁佑见天色已晚,“我们今日暂且找家客栈住上一晚,明日再去拜访百川兄。”二人表示赞同,一起住了店。
夜已经深了,安静的星空下时不时地传来蝉鸣,梁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干脆掌灯起来,抽一袋旱烟。他们从怀城逃出来已经三个月了,失去了家的他们就如孤坟上的野草,随风摇曳。丧家之痛,梁佑此时何曾不想打回去,可是他的家底尽丧,本想求助阎锡山可浮桥镇的事有让他重新考量,百川到底可不可靠?还有那个梦中姑娘,她为何要装作素不相识?大概只有时间能够解决这一切吧。
次日清晨,梁佑还没动身,阎锡山就亲自来他们下榻的客栈去迎接,刚一见面,阎锡山紧紧握住梁佑的手,“向佐来也不知会一声,要不是李中将派人提前告知,阎某人岂不要怠客咯!”
梁佑笑着作揖道:“百川兄哪里话,佑走投无路愧于打扰,岂敢过于劳烦您呐!”
阎锡山说道:“向佐这是哪里话,你我兄弟二人何分彼此,你的事我都听说了,自有为兄替你做主,快请到寒舍一聚,我们俩好好说说话。”
梁佑和阎锡山在一帮护卫的跟随下来到了阎府。进门的时候,梁佑差点被门槛绊倒,幸好张充眼疾手快,扶住了梁佑。梁佑说道:“百川兄的门槛太高,佑有点高攀不起啊。”
“贤弟这是哪里话,听说贤弟眼睛受伤了,多半是没看到这门槛,这样,我明天就把这门槛去了!”阎锡山拍了拍梁佑的背部。
这时,一声枪响,阎锡山左臂中弹,枪弹贯穿到梁佑体内,梁佑顿时倒了下去。“有刺客”还没等阎锡山发令,卫队就已经把刺客打成了筛子。
“向佐,向佐,快快,来人把梁兄弟送到医院!”张充和阎锡山扶着梁佑上了阎锡山的座驾美产吉普车里,刘松在后面跟着,走到刺客的尸体旁边时,狠狠地踹了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