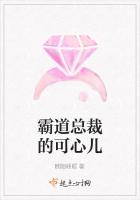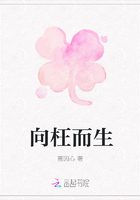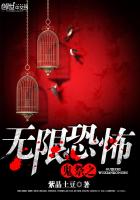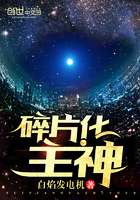一尘禅师从院墙厕所出来,低头疾行,忽闻有人招呼:“一尘禅师请留步。”抬头看时,仍是上午求见的那两位男女,便撤后一步,垂下眼睑,单手施礼,说:“阿弥陀佛,此乃后禅之地,请施主离开,恕小僧不与多陪,失礼失礼。”说完,在于垚和彭伊叶面前匆匆绕过。
于垚双手合十,对着一尘禅师的背影虔诚地说:“我们觉得你有不凡的气度和内涵,便慕名前往,今日一见,更加深了我们对您的探究之心,希望能与您进行一次不寻常的心灵沟通。”
一尘禅师停步顿了一下,没有转身,还是快步走进房门。
于垚看着关闭的房门,对彭伊叶小声说:“咱们就在这儿守着他,以表示咱们对他的真诚和尊敬。”
彭伊叶也小声地问:“你觉得他能出来见咱们吗?”
于垚回答:“不会,但他会知道的。其实他也渴望有心灵的沟通,但必须是对等的。”
“那咱们要站到什么时候?”彭伊叶照着于垚的样子,双手合十。
于垚闭上眼睛,说:“站到不让站为止。”
隐浮阁里,一尘禅师没有按惯例跏趺,而是站在屋中央拿着书翻看默读,时不时地从窗格向外看一眼伫立的于垚和彭伊叶。
夕阳西下,于垚和彭伊叶最后走出寺宇大门,僧人随即把大门从里面关上。此时平台上只有几位老人在散步聊天。
彭伊叶活动了几下疲惫的腰身,问于垚:“咱们现在怎么办,就这样无功而返吗?”
于垚看了看紧闭的大门,说:“等,咱们就在门前等他。我总觉得他会出来的。”
彭伊叶问:“怎讲?”
于垚说:“如果他认为咱们可谈,他会出来看一下。亦或不是如此,他也会在没人打扰的时候走出佛门,感受一下束缚之外的境地。”
彭伊叶赞许地看了于垚一眼,不自觉地拉起于垚的胳膊,说:“对,我们等他。现在你先陪我走一会儿,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
于垚笑着点点头:“好吧,借这净土之地,咱们也敞开心扉。”
天色彻底暗了下来,寺宇的大门悄然打开,一尘禅师走出来关上大门。他走下台阶,来到平台的边缘,深深地吸了几口清新的口气,便望着远天遐思。忽然,他觉得身后有人,便转回身,见仍是白天的那两位男女向他施礼,有些惊讶,连忙举手还礼,问:“阿弥陀佛,你们真没走呀?”
于垚回道:“我觉得咱们应该是心有灵犀,所以就又见面了。”
一尘禅师闭目静思一会儿,问:“施主既然是要与少僧心灵沟通,想必是意有所境,心有所载,少僧法号一尘,敢问施主如何解义?”
于垚看看彭伊叶,彭伊叶欲言又止,摇摇头,冲于垚小声说:“我怕说不准,砸了锅,还是你说,让人放心。”
于垚会心一笑,转向一尘禅师,说:“以我的本性,我欣赏这个法号,它普通简洁,却饱藏心智。从我不成熟的理解看,法号中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微不足道,有自谦之意;其二是一尘不染,高洁傲岸。而我觉得,能支配不寻常之举的思维,绝不甘于微不足道,所以,恕我直言,我倾向于其二。既然争不过沉浮,何不隐遁凡尘。表面看是藏锋谦逊,其实是咄咄傲骨,不屑与庸碌为伍。尊师之所以拒人于千里,是因为在平等之时被偏见世俗所拒绝,心中伤感,而在非凡之地,又被庸俗功利所利用,心中孤寂。我想,尊师也渴望心灵间的共鸣,只是没有觅到知音。”
彭伊叶忽闪着眼睛,脉脉地看着于垚,敬佩之意由心底涌出。
一尘禅师一动不动,仿佛没有听见于垚的说话,静了很久,他微睁双眼,平淡地说:“少僧固执度生,不指点迷津,更不预测未来,如有事相求,请免开贵口,望施主见谅。”
于垚:“我们此次前来不是相求,而是想得到认证,是为了使自己的内心如磐,更能经得住风侵雨蚀。”
一尘禅师:“认证的前提是认知的相同,世上之事,因人而异,对错之解,角度所见。想必你们并不是为了指点迷津的规劝,而是为了在心灵深处有一个宽慰自己的理由,使自己能够说服自己,不至于在未来之路上因荆棘多而铩羽折戟,因岔路多而半途而废。”
于垚:“大师看得很透,我们正是此意,就是想听听您对人生的中肯之见。”
一尘禅师:“我是放下了一切,皈依空寂,何谈人生,而你们是胸怀大志,负重前行,其任重道远。我心无旁骛,无所顾忌,什么话说起来轻松容易,而你们却要一步步去做,要在坎坷中踉跄前行。所以我,一个小小的僧徒,实在是不敢肆意地说什么。”
于垚:“尊师自谦了,其实您的话里已含有许多期许,那就是说的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踏实地做到。就像您,能够放下自己,向命运挑战,就是一种超然的境界,是无声的展示,是无字之书,只有真正理喻读懂的人才能从中得到感悟和收获。”
一尘禅师:“施主的话,有对的地方,也有过誉的嫌疑,但你是俗人,少僧骨子里也难泯普生之心,好在此地是在佛门之外,也就彼此心知吧。有什么见教,可说一二。”
于垚:“人们都说,命运不是天注定的,是可以改变的。我也这么认为,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的命运是沿着自己的心灵轨迹而运行的,这是否有悖于常理?”
一尘禅师:“这很正常,因为多数人是普通人,他们不求过程,只想结果。所以真理为大多数人所膜拜,所接受。而真正受益已于真理的人,是少之又少。当你所做的事情是多数人所做不到的时候,命运就与真理接轨了。”
于垚:“人们把少数人的做法叫另类,那这另类的实质是什么?”
一尘禅师欲言又止,反问于垚道:“你说呢?”
于垚看到一尘禅师目光的深邃,里面有希望和渴望。那就是希望能心灵相通;渴望能觅到知音。他与彭伊叶对视一下,略想了想,说:“奋发向上或是追求不一样的另类,就是超脱普通,放下自我,历练自己。”
一尘禅师赞许地点点头,说:“施主说得极是!只是不知施主能如何放下自我,历练自己?比如,面对形形色色之人,你要……”
在一尘禅师等待回答的余音中,于垚胸有成竹,坚定地回答:“我要抛开功利私欲,促善避恶,广安普众。”
一尘禅师:“面对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之人,你的策略是……”
于垚:“高山远眺,虚怀若谷。”
一尘禅师:“对方挑剔尖刻,你会……”
于垚:“不卑不亢,顺势宽容。”
一尘禅师:“面对嫉妒讳忌之心,你……”
于垚:“坦荡笑对。”
一尘禅师:“需要辩解表白时,你应该……”
于垚:“踏实实践,用行动说话。”
一尘禅师:“你有了冲动急躁的情绪,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或是认识上的偏差失误,带来伤害或损失。”
于垚:“认识到的错误不可再犯,豁达释然地勇于承担,抛开自尊地竭力挽回。”
一尘禅师:“逆级拾阶时……”
于垚:“要有把酒临风的气质。”
一尘禅师:“阿弥陀佛,施主大胆做吧,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包括救赎他人。”
于垚:“谢谢大师,按惯例,我们应该……”彭伊叶把已准备好的一个信封呈给一尘禅师。
一尘禅师双手合十,放到胸前:“出家人净空之心,慈悲为怀,立命无忧,衣食不愁,身外之物,就让它用在该用的地方吧。做好你们的事就是对我最好的答谢。”
于垚:“今天您让我对自己、对未来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谢谢您给我信心,给我启示。”
一尘禅师:“启示不敢当,信心在于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其实,人的一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或多或少都有曲折、离奇、辛酸、迷离、狂热、幸福、快感等感受,其路途也不排除是是非非、悲悲喜喜、甜甜苦苦、寻寻觅觅、磕磕绊绊、糊糊涂涂,最后的结局或是平平淡淡,或是起起落落,或是苦尽甘来,或是惆怅遗憾,或是功成名就,或是哀叹孙山,无论怎样,都不枉追寻的人生。”
于垚:“最后,我再问一句,别人以为你一时冲动,放弃了美好前程,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坚守自己?”
一尘禅师:“关于自己,我不好回答,不过我可以说,放弃和坚守都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放弃需要足够的勇气,而接下来的坚守就需要足够的定力了。我现在心闲身定,还很安逸,阿弥陀佛!”
于垚刚要回话,彭伊叶略前一步,双手合十,放置眉前,说:“小女听了你们的对话,心有感触,不知是否可讲?”
一尘禅师还礼,说:“这是佛门之外,没有什么拘礼,小姐有话可讲。”
彭伊叶:“一尘尊师,来之前我对您是未知的,只是充满好奇,在艰辛的等待和碰壁中,我对您也有了些许的烦躁和抱怨。而您与我同伴的几番交流,让我对您肃然起敬,也对我的同伴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你们是不同环境中的同类人,都有着远大的抱负,有睿智的头脑,有超常的隐忍之心,都是能够脱离低级趣味而成就大业的人。恕我冒犯,可能性格决定心灵的归宿,但我感觉,您放下自己虽是属于无奈,可绝不是被动地放弃逃避,而是主动地把自己放到一个超然的位置,在寻找、在呼唤、在践行自己的未了之愿,是要把自己的寄托托付给真正的天行健之君子。而我的同伴,在偶然中知道您,使我们在必然中相识,这也可说是一个机缘。在您和我的同伴身上,我有了许多新的发现。我们今天已经是不虚此行了,尤其是我本人会受益终生的。”说完,她深情地看了于垚一眼,一尘禅师闭目微微颌首。
于垚也回望了一眼彭伊叶,眼神里满是感激。
一尘禅师双手合十:“天色已晚,二位请回吧。”
于垚回礼,说:“我明白我应该怎样继续下去了,谢谢!希望还能与您相会交心。”
一尘禅师垂目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