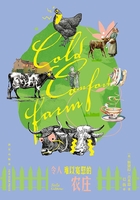活阎王气得眉毛倒竖,心火往上窜,浑身瑟瑟地抖动着,充血的小眼珠里射出一股凶狠的光。他熬了一夜了,专等儿子追人和要钱的消息,可是儿子至今连个影子也没有。吃过早饭,他坐不住了,便要到坎马寨兴师问罪。
唉,六百块钱,是他的血汗钱啊。活阎王一想到钱的失落,内心便激烈地阵痛,自然地便又联想到前天夜里的事。他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媳妇跑了,儿子能认不得?谎鬼,除非睡死了。听寨子里的风言风语,这事好像还与小孔明有瓜葛。想到这里,他的脚步慢了下来。
山那边吹过来一阵风,白生生的云就随之滚动,膨胀。猛然间,他下意识地踅转身,直往寨子里狂奔,那速度,那股劲头,简直不像个将近花甲的人。“小孔明,你给祖公滚出来!”活阎王满脸怒气,小眼珠滴溜溜地转动,上嘴唇稀疏的胡子一根根的翘得老高,手里提着根栗树棒子,站在小孔明家的门口大叫大骂:“祖公今日饶了你,就做你孙子!”
小孔明家的门虚掩着,里面静静的像没有人一样。几个小娃娃离得远远地睁着惊疑的眼睛往这边瞧。他听听房里没有回音,就把那栗树棒子敲在门坎上,又冲门里喊:“你别装聋卖瞎,是英雄好汉出来给祖公瞧瞧,何消做个乌龟,好事又怕事。鬼聪明,想恁个就蒙住祖公的眼睛?你再去投几年师……祖公的裤带也比你的年岁长,你算个卵子!”
活阎王一嚷,二十多户人家的大门里都走出两三个人来。他们先是在远处看,互相逗着耳朵悄悄地谈论,说一句朝这边望一眼,直到明白了是那件事,才慢慢靠拢来,说好话合稀泥,唠唠叨叨。但是活阎王还是不吃这一套。
众人无可奈何,走又走不开,一边洗耳恭听,一边把目光投向小孔明家的门里。
少顷,“吱嘎嘎”一阵刺耳的响声,小孔明家的门慢慢开了,走出来的是小孔明的嫫(小孔明不在家里,早避风去了)。她睁着一双半闭的惊疑的眼睛,莫明其妙地瞅着气势汹汹的活阎王,扶在门板上的手像按在钢琴上,指头不断地抖动。她双耳失去听觉,活阎王的话她还没听清,还不知道眼前发生的事。她只凭视觉看到活阎王的嘴在动,偶尔听到一句又听不到一句,断断续续。最后她终于弄清了活阎王在讲些什么,也是那半闭的惊疑的眼睛骤然间睁开,用手“砰砰”地敲着门板,双脚咚咚地跺着地,张口就骂:“这个没长眼睛的老乌龟。你儿子媳妇跑了,来怪我儿子,还好意思满口尿屎喷到我的门上。你嚼牙巴骨,骂你的本身自身。我问你,二十多年前你媳妇私奔了,去找野老公了,又怪哪个?你讨老太太捡你的脸。老杂毛!”
小孔明的嫫其貌不扬,竟是这般泼辣,几句话呛得活阎王脖子发直,脸色发乌。
看热闹的人们暗暗叫好:活阎王这块顽石总算碰到了铁锤。
他也暗暗叫苦:怎么骂小孔明会骂出个老妖精来。活阎王是寨子里说一不二的人物,可是对老妖精却有些畏惧。他是尝过辣子汤的。只因打死过她家两只下蛋的母鸡,她竟然从他家的厩里抱走了一头小猪。这样的女人,比母老虎还恶。好男不和女斗。活阎王看看骑虎难下,摸错了庙门,便狠狠骂了一句,如一头斗败的公牛睁着血红的眼睛转身就走。
活阎王自找苦吃,走了儿子媳妇,丢了六百块钱,挨了一顿骂,实在划不着。他像一个醉汉跌跌撞撞离去,拖在地上的栗树棒子碰在街心的石块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天擦黑的时候,他才转悠进家,但两手空空,那根栗树棒也于不见了。
家里很黑,除了耗子叽叽咕咕的叫声和在楼梯上跑动的声音外,什么也听不到。静,静得叫人窒息。他在楼梯脚的草墩上坐下,把头深深埋进两个膝盖之中,使劲把胸脯里的闷气往肚子里挤压,但是压不下去,气这东西只能往上浮。
他终于由骂小孔明转到了骂福寿:无义种!这个无义种!你还记不清你嫫的样子,祖公就一泡尿一泡屎,一口饭一口汤,又当嫫又当爹地把你拉扯大,省吃俭用供你读书,苦死累死积攒了六百块钱,你是恁个整嘎?老子哪点对不住你,尽去丢人摆底,叫我这老脸往哪搁。
他越想越气,越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就慢悠悠站起来,抬起哆哆嗦嗦的手从木柱的铁钉上取下一根棕索,拖着无力的脚,艰难地爬上了楼。楼上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他顺着板壁走,抖抖的手摸到窗子上,还摸到了一盒火柴。他站住了,随着“嚓”地一声响,一朵火苗从手中跳起,又一闪一闪地点燃了一盏用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楼上立刻有了些光亮,眼前的一切也模糊可辨了。
这个家,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家,每一样东西都能激起他的一番思绪。铺上的那床绣花被子,大补丁压小补丁。这是讨福寿嫫时就从山外换来的,年代长,被子给汗浸透了,太朽了,脚指甲壳挂一下裂开一个口子,补也补不住,但他舍不得丢,山里人的钱来得艰难。供柜的正中没有供奉“天地国亲师位”的神灵牌位,贴的倒是几十年前出了十一块钱从山外画来的一幅彩云姑娘下凡的图画。图画也旧了,被蛀书虫啃了很多洞,大大小小的,像一张篱笆处处透亮,彩云姑娘苹果一样的面容变成了十分丑陋的麻脸,连鼻子头也不在了……他看着,嘴唇不停地抖动,腿也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心里默默地说:“彩云姑娘——嘎玛寨的祖先,我没有把你供奉好。家里出了件伤风败俗的事,我甘愿得到报应。”
过了一会儿,他才怏怏地站起身,走到了大梁下,把棕索拴在大梁上,就将脖子往上伸……脖子刚伸上去,却又缩了回来,他双手放了棕索,三步两步走到供柜前,踮起脚尖,伸长手,从里面摸出一瓶酒,用牙齿咬开盖子就喝。他想,反正饿着肚子寻死划不着,死后还不是变成饿死鬼到处要饭。吃饱喝足去死,到了阴间就有酒喝,有饭吃啦。这一点,他比谁都聪明。
他伸长脖子咕咕地喝,喝得浑身燥热,眼睛发红,脸发紫,脑壳发胀。片刻,他突然手一扬,瓶子落到楼板上,又轱辘辘地滚向窗子那头。他嘿嘿地发着傻笑,一边结结巴巴地说:“彩云……姑娘……六百块……全完了……”一边歪歪倒倒地朝拴在大梁上的棕索走去。
棕索结成的活动扣在他的眼前晃动,整个楼房也在眼前晃动。他试图抓住棕索,但刚伸过手棕索又荡远了,扑了个空,脚也随之打了个趔趄,险些摔倒。棕索又荡过来了,好像擦在了脸上,他急忙又抬起了右手,狠狠一抓,虽然抓住了,身子却控制不住,沉沉地往下坠,软得像一坨烂泥。手也无力支撑了,五指一松,整个身子瘫在楼板上……
大脑里一片空白,像一张没有字迹的纸。他只是直勾勾地睁着眼,望着大楼左右上下旋转,望着彩云姑娘千疮百孔的画像旋转,望着套在大梁上的棕索旋转……
天老爷,这是咋个整?他像在彩云姑娘的凌霄宝殿,身体上下浮动,嘴里还喃喃地说:“福寿……我的儿子……你在哪里?”